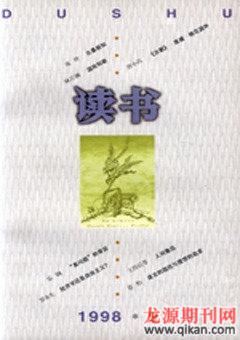“奇跡”背后的幽靈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還應該對創造“東南亞奇跡”的四個主要國家的政治軌跡進行比較考察,以估量每個國家在這場崩潰中可能的后果。這一考察以菲律賓為開端,再談到馬來西亞和泰國,以印度尼西亞為另一端。
在“奇跡”年代的大多數時間里,菲律賓看來是個可悲的例外:這個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美國的前殖民地,在其它國家高歌猛進時陷入了貧窮。但是在這場崩潰中,它的貨幣比泰國的銖,馬來西亞的林吉特,當然還有印度尼西亞的盾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并且這個國家甚至正在擺脫而不是落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控制,這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是,與馬科斯政權的特點,以及它在一九八六年二月崩潰的原因和時機有關。除了他是個文官政治家這個事實,馬科斯是“熱”冷戰時代“東南亞”典型的暴君。他在一九六五年首次當選總統,當時林登·約翰遜正開始把大量美軍派往越南。美國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特別是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巨大的克拉克空軍基地,是進行這場戰爭的中心。馬科斯為提供這些便利索要了高額租金,雇傭菲律賓軍隊去越南服役,對在菲律賓土地上貯存核武器保持快樂的沉默,并叫囂著支持美國的戰爭行為。反過來,也許也因為對尼克松最后兩次總統競選提供了大量個人財政資助,華盛頓對他在一九七二年建立盜賊式獨裁視而不見,直至他合法的總統任期結束。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八六年,馬科斯家族和他們的密友,完全依賴美國的不斷支持,系統地掠奪本不太強大的菲律賓經濟,在這個過程中既促成在南部穆斯林地區弱小的分離主義叛亂,也激發了一場傳播到國家各地的起義。但到八十年代初,“東南亞”冷戰的“熱”階段結束了,里根的白宮開始冷靜下來,認識到馬科斯的獨裁政權必須結束:它正在毀滅這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對美國也沒有什么好處。于是中央情報局積極參預了反對這個政權的民眾動員,正是美國軍隊的飛機最終突然把這對令人憎恨的夫婦從他們的宮殿帶到夏威夷的“豪華”監獄之中。科拉松·阿基諾(她的丈夫于一九八三年在從美國流亡后回國時被馬科斯的親信謀殺)接管了政權,立即恢復了大部分馬科斯之前的大地主式民主體制。當極右翼軍人試圖推翻她的政府時,華盛頓在反對他們的干預中起了決定作用。(最突出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一九八六年,正當“東亞奇跡”的高峰,菲律賓實際上破產了;但就在同時,正由于這個原因,它脫離了冷戰體系。一方面,阿基諾被迫接受了非管制、自由化和緊縮政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威(在她的繼任者菲德爾·拉莫斯治下仍在繼續),但是她懷著十足的正義譴責她可惡的前任。在另一方面,由于許多復雜的原因,包括皮納圖博火山爆發的火山灰埋沒了克拉克空軍基地,美國人開始分階段撤出在這個國家的軍事設施,這個過程在一九九一年結束了。隨著馬科斯的垮臺,共產黨起義勢頭大減,分裂為多個派別,漸漸瓦解了。政府最終與主要的穆斯林叛亂者團體達成了解決方案。現在的寡頭式但內有競爭的政權看來十分穩固,也沒有強有力的理由認為菲律賓不會以不大的步子顛簸前行,渡過九十年代。總而言之,菲律賓在這場崩潰中損失最小,是因為它在崩潰來臨之前很久就陷于破產,從未經歷過“泡沫經濟”,并從八十年代中期就有著一種“正常化”的半民主、半寡頭的冷戰后文官執政的政治體制。
比較起來,馬來西亞和泰國受到較重的打擊。馬來西亞在“熱”冷戰時代是以非正常的重要方式經過的。這個國家一九六三年才創建,當時白廳將馬來亞、新加坡、婆羅洲地區的沙撈越和沙巴匆匆地捏在了一起,新加坡后來在一九六五年獨立出去。馬來亞半島本身在殖民國粉碎了強有力的當地共產主義運動后才得到獨立(在一九五七年)。馬來西亞繼承了(后來改進了)殖民政權的嚴酷的反顛覆法律和無情的安全機構。部分是由于這個原因,部分是因為倫敦堅持(至少在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期間)保持它自身在“東南亞”的存在,華盛頓在馬來西亞的干預比在這個地區的其它部分要少。這個國家一直有著一個持久的專制性的政府,但它的持久性的基礎與冷戰無關,有關的只是馬來種族群(占百分之五十二)的集體意志,面對人口眾多的“中國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和較少(占百分之十)的“印度人”少數民族,壟斷實際的政治權力。這意味著總理必須是馬來人文官,這些總理沒有一個是被公開的暴亂趕下臺的。同時,馬來人領導者也足夠明智,允許“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受控制的和從容的政治參與。政府名義上總是由三個種族分明的黨派組成的聯盟,并總是有少數民族的內閣部長。馬來人企業家受到很多的優惠待遇,通常是在受保護的領域,但從未走到完全排斥發達和有活力的少數民族商人的極端。結果是一種不尋常的政治穩定,鼓勵了多年來外國的廣泛投資。從石油和天然氣得到的充足財源也為政府財政提供了穩定的基礎。雖然投機狂熱和對膨脹的大規模計劃在九十年代打擊了馬來西亞,腐敗迅速滋長,這個國家由于兩個特有的因素部分地避免了嚴重的瓦解。第一個是與富有的與其只有一條跨越柔佛海峽的短堤道相連的新加坡特有的競爭—共生關系,這個絕大多數是“中國人”的被李光耀控制了四十年的城市國家,總是對被夾在兩個伊斯蘭教講馬來語的,有著反華的暴亂歷史的國家之間的位置很敏感,因而有一切理由幫助吉隆坡,而它的財富使它有這樣做的條件,至少在這一點達到了目的。第二個原因是很奇怪的,就是這個馬來人領導層自身的小城鎮的狹隘觀念,它感覺到需要公開強調伊斯蘭教的價值,人們甚至可以說它面對老大哥印度尼西亞有著自卑情結。
馬來西亞在未來較長的時間里面臨的主要困難,將是它教育體制的落后,還有許多馬來人當中那種吃現成的心理,他們整整一代人一直是政府慷慨賜予的特權受益者,這一模式讓人想到像科威特這樣的地方。在近期內,這個持久的政府以什么方式對經濟危機作出回應,是加緊專制的控制,還是允許更多的民主參與并承擔真正的公共責任,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相反,泰國從“東南亞”冷戰的“熱”階段的開始,對美國人而言就是一個前線國家。早在一九三二年,一個軍人—文官集團就推翻了專制君主政權;從三十年代末期起,軍人的政治地位在披汶頒堪元帥領導下開始上升,并將泰國作為日本人的同盟國帶入了太平洋戰爭。由于日本的失敗暫時失去信譽后,軍人通過一九四七年的政變重新掌權,立刻與華盛頓結成同盟。這個時期的特點是“野蠻的比爾”多諾萬(Donovon)被艾森豪威爾派到曼谷當大使。美國的控制在強人沙立·他那叻和他的副手們的政權統治下(一九五八——一九七三年)進一步加強。在越南戰爭的高潮期,幾乎有五萬名美國軍人駐在泰國土地上,這個國家遍布軍事基地,這些基地被用于從陸地、空中和海上進攻印度支那。同時,美國把大量的金錢投入泰國,用于軍事設施、農村發展和教育,而日本在六十年代末也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投資參與者。
由此導致的社會變化,在七十年代中期產生了為數巨大的新中產階級和(一九六五年之后)共產黨的起義,與日益增長的反對與美國結盟的力量結合在一起,造成了未曾預見到的前所未有的一九七三年十月的群眾總動員,在國王拉瑪九世慎重的協助下,奪走了獨裁者們的權力。一部自由憲法頒布了,泰國歷史上最公平的選舉舉行了,到一九七六年三月,美國撤出了在泰國的軍事存在,與北京建立了誠摯的關系。在同一年,共產黨在印度支那的勝利引發的國內劇烈的兩極分化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血腥政變時達到高峰,此后數千理想主義和激進化的學生們逃到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中。
在那時,一個極右翼軍人政權極有可能得到鞏固。但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時冷戰在亞洲已迅速冷卻下來。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極端分子被將軍江薩·差瑪南領導的另一場政變推翻,他對地下組織的學生進行大赦,對外采取了發展與北京和河內良好關系的方針。江薩靈活的政策由于中—柬—越一九七八——七九年的三角戰爭而幸運地進一步發展,在這場戰爭中忠于北京的泰國共產黨喪失了它在印度支那的安全后方,還喪失了新近招募的和有強烈民族主義的學生支持者。到一九八○年,這個黨與其它的左派都退居不重要的地位。
因而從八十年代開始,現已得到中國、日本和美國支持的泰國基本上走出了冷戰階段。雖然這十年間大多數時期由一位將軍擔任總理,他的內閣也是松散結合的保守政黨的聯合體。經濟“奇跡”為空前規模的賄選提供了基礎,大商人和地方顯貴的政治力量通過買通軍隊和官僚而穩步增長。軍隊在一九九一年又一次短期奪取了政權,不是以傳統的“紅色恐怖”的理由,而是基于文官政治家的腐敗,但在一九九二年“血腥的五月”中被巨大的中產階級動員起來趕下了臺。
這個插曲產生的一個有價值的后果,是一場要求根本憲政制度改革的運動:減少腐敗的官僚階層的集中的權力,制止賄選,加強政黨紀律和增加公共負責體制。泰國銖在一九九七年七月的崩潰,使那些最有力量對抗這些改革的群體失去信譽。新憲法在大多數方面是進步的,近來已經頒布。崩潰本身沒有引起政治動亂,甚至大規模的示威,只導致一個腐敗的文官內閣垮臺,被另一個稍微廉潔些的政府取代。并且,得益于“中國人”長期以來成功地整合進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之中,到目前還一直沒有人尋找種族主義的替罪羊。泰國的政治精英通過屈從于國際風暴的壓力,已成功地堅持了一個半世紀,不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的順從有什么大驚小怪。由于這些要求,它可能、也許馬上,會遭到失業率上升和物價陡漲的報應。因為上面列舉的理由,看來奇跡將不會在泰國重現,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個國家的冷戰后政治秩序足夠靈活,根基足夠穩固,能保證在不太遙遠的將來緩慢地恢復過來。
然而印度尼西亞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印度尼西亞經濟在一九六四—六五年實際上已經崩潰了,這是過度膨脹、腐敗的軍方操縱的巨大國有化領域和蘇加諾絕對專制的政策造成的后果。這次崩潰是造成發生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和一九六六年一月間對合法的、非武裝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及其同盟大規模屠殺的心理氣氛的關鍵因素,它付出了犧牲五十萬人的代價,還有不經審訊卻常進行拷問的監禁,使另外幾十萬人被關了許多年。此后不久就推翻了激進的民族主義的總統蘇加諾這個令華盛頓頭痛的怪物。正在美國軍隊陷入印度支那的泥潭,而蘇聯的軍事力量迅速增長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集團之外最大的共產黨的可怕毀滅,使得這場大屠殺的指揮者蘇哈托將軍贏得了美國的迅速支持。在一九六六年春天,印度尼西亞的第一個“熱”冷戰政權就在恐怖之后建立起來了。
在其早期,這個獨裁政權完全滿足了美國的希望,并因此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一群新古典派,在美國受訓練的經濟學家管理著經濟,結束了過度膨脹,把許多國有公司私有化,或歸還給它們原先的外國所有者,并鼓勵外國投資制造業和投資開采這個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又與美國達成了秘密協定,允許美國核潛艇潛過印度尼西亞的水域而不浮出海面,以躲避蘇聯衛星的追蹤。作為回報,華盛頓組織了跨政府援助印度尼西亞集團(IGGI),一個由美國、日本和主要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組成的國際財團,在超過二十五年的時間里給這個國家的“發展”預算注入了大量的和穩定的資金。這些政策,它們的效果在新近由石油致富的印度尼西亞得到極大增強,這個國家受益于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一九七三年大幅度提高油價。這是蘇哈托政權得以鞏固和印度尼西亞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奇跡的兩個關鍵性的基礎。華盛頓極為滿意,以致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之后,當蘇哈托決定入侵和占領東帝汶這個前葡萄牙小小的殖民地時,福特和卡特政府無視這個侵略事實,達到侵略目的所用的武器百分之九十是美國的,這大大地違反了兩國一九五八年雙邊武器協議。美國還在國際制裁中維護雅加達,并秘密提供殺傷性的在越南戰爭中使用的OV—10對地攻擊直升機,它如此有效地摧毀了東帝汶人的抵抗和東帝汶的農村環境與社會。(超過二十萬東帝汶人,即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間非自然死亡。)
隨著時光流逝,蘇哈托政權以必將產生長遠后果的方式,逐漸改變了它的內部特性。在早些年中,他是將軍統治集團中的第一人,他的權力基本上來自軍隊,他的權威基于恐懼和由美國安排的經濟穩定受歡迎的效果。在那些日子里,有名的富人是軍隊的高級軍官,最臭名昭著的是伊布雷·蘇托沃將軍,長期是國家石油公司帕塔米那(Pertamina)的首腦,他的管理使這一組織在一九七五年歐佩克(OPEC)處于成功的高峰時破產。然而長期以來,蘇哈托將他的戰友甩到一邊,建立起個人獨裁,今天雅加達說笑話的人稱之為“我們的泰坦尼克號”,其意義是雙重的。
一方面,蘇哈托完善了一種選舉制度和一個以巨大的官僚制為基礎的國家政黨,以確保他完全控制立法和人民協商會議(它選擇總統和確定國家政策的總綱),他頗為狡猾地建立和資助了兩個名義上的反對黨,一個是熱誠的穆斯林,另一個是基督教徒和其他害怕這類穆斯林的人。利用這些機制和國內外各種來源的無限的資金,可以演出無窮的“自由選舉”,也使他自己長期一直被任命為總統而無人反對。
另一方面,他開始利用印度尼西亞的很不被喜歡的少數民族“中國人”確保他對這個國家國內財富的控制。在這個政權的早期,蘇哈托斷絕了與“紅色中國”的外交關系,封閉了“中文”學校與報紙,強迫“中國人”將他們的名字改為穆斯林或爪哇語發音的名字,并立法將這些人們的官方名稱寫為“支那”(tjina/cina)(以China為根據)。他后來認識到對“中國人”政治—文化的鎮壓和強迫聚居可以服務于其它目的。一方面,“中國人”以一種從未有過的方式完全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權力之外。同時,這些“中國人少數民族”被鼓勵集中在商業領域,他們中間一小撮精英被提拔到他個人保護之下的超級大亨階層中。在這種“分而治之”體制中,人們可以說“中國人”有經濟的而不是政治的權力,而當地的印度尼西亞人(對于蘇哈托而言這些人中可能出現對手或繼承人)可以有政治地位,但沒有集中的獨立的財富來源。
這些“宮廷大亨們”也是建立蘇哈托家庭巨大到難以置信的財富的代理人,他們使馬科斯家族在鼎盛時期的掠奪相形見絀。這些超級大亨階層靠政治手段重新壟斷經濟的關鍵部門,特別是銀行業、進口業和自然資源的開發。蘇哈托的“皇家子女”和其他親戚在大亨們的公司里得到大批股份,從大亨擁有的銀行無限制地借貸,并附帶壟斷特定的出口品(例如丁香)和進口品(例如塑料)。這種榜樣在“奇跡”年代上行下效,因而印度尼西亞通常與尼日利亞和中國一道被列為世界上最腐敗的三個國家之一;因而這個在一九六○年曾與南朝鮮處于同樣發展水平上的國家,在三十年后完全被后者超過了。
時間的逝去必然也產生它的社會和政治后果。蘇哈托作為國家首腦的時間比世界上所有非君主制領袖都長,除了菲德爾·卡斯特羅,還有差不多長的多哥的納辛貝·埃亞德馬(GnassingbeEyadema)。多年來他能依賴對一九六五—六六年“大屠宰”的記憶保持印度尼西亞公眾在政治上的沉默。但是今天,只有四五十歲以上的人才有這種記憶,大多數印度尼西亞人都要年輕得多。這個政權仍然舉起“潛伏”的幽靈或“復發的”共產主義來證明它鎮壓的合理性,但是這種僵硬的冷戰式的花言巧語說服不了任何人。現在領導軍隊的將軍們在大屠殺發生時還是沒長胡子的軍校學員,比他們的總統整整年輕一代人。在九十年代開始,一代新的、龐大得多的工廠工人中,其中許多人是婦女,產生了越來越大膽的爆發力,通過罷工和其它形式的抵抗,破壞著這個政權對勞動者的總體控制。新中產階級是從這個奇跡中誕生的,他們最初的感激已轉變為對資本主義亞洲這個最后的冷戰政權的貪婪和壓迫的失望和厭惡,是因為他們已看到,在其它地方壓迫都已令人愉快地減少了。
印度尼西亞盾災難性的崩潰,要比任何其它過度膨脹的地區性通貨所遭受的崩潰嚴重得多,這意味著每個人,不論印度尼西亞人還是外國人,都認識到,印度尼西亞現代史上第二次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有密不可分的聯系。盡管經濟破產,“發展之父”蘇哈托的政治機器還確保他一致再度當選為總統,還有他的門徒,在德國受訓的航空工程師哈比比當選副總統。他的女兒“圖蒂”被任命為社會事務部長,還有他寵信的“中國人”大亨為貿易部長,而他的女婿是軍隊精華——戰略部隊(StrategicCommand)的司令。多年來對兩個黨派和幾十個社會組織的壓制和操縱,看來削弱了它們進行那種使南朝鮮、菲律賓和泰國從冷戰政治體制中解放出來的,有目標的社會運動的能力。結果是民眾到現在為止,對崩潰的苦難的反應主要是騷亂,反對和搶掠那些“中國人”的財產。這種騷亂的后果只能使經濟進一步癱瘓。
蘇哈托完全明白,他在世界上各大國眼中已經被看成是一個大問題,而不再是一個有用的盟友。他知道在大屠殺時代還是一個學生的克林頓,會愿意他下臺。但是他在他的泰坦尼克號下沉時還要賴著不走。他太老,太狹隘,太驕傲,不能打好行李走人。新秩序是由他建立,為他服務的,沒有他就不能存在下去。但是有他也在劫難逃。還沒有人對在他之后可能會出現什么情況有清晰的見解,但這種日益增長的不確定性,只是加深了對一個長期遭到破壞的國家的未來和可能蔓延的動亂與失序的普遍恐懼。不管它在何時何地起伏發展,蘇加諾都會搓著他那魔爪般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