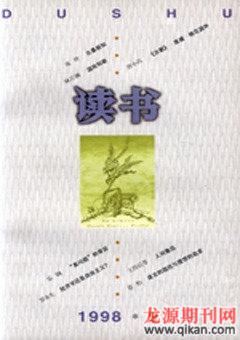留學生的故事
梁科慶
許多個他和許多個她的經歷,組成了《留學美國》。學生出國升學的第一關是“托福”。近年各大學對“托福”分數的要求不斷提高,學生為應付考試,都要努力操練。我當年亦曾參加有關的課程,同樣遇上可笑的經歷。本書作者錢寧曾在的一班是由一位邊漫游,一邊教英文,卻從未聽說過“托福”的美國小伙子授課;而我所讀的一班更荒謬,授課的所謂“外籍教師”,是一個巴基斯坦人,不僅發音不純正,更糟的是,他每次上課前一刻,才從教務處領到講義,這些講義其實是一本頗暢銷的“托福”練習的影印本,那本練習我早就做得滾瓜爛熟,所以不時發現既無備課,又無答案本的老師解錯題。我曾因此事向香港的消費者委員會和教育署投訴,但直至我登上加航客機前,仍未有下文。
香港學生選擇留學主要由于移民或失意于本地的公開試,九七之后,隨著移民熱潮減退,以及大學學額增加,留學人數漸趨減少。在內地,情況并不一樣,社會“沒有給年輕一代留下太多的發展空間”,于是出國是“無數中國青年平凡、無聊、黯淡生活中的一線亮光”,留學便成為出國的手段。
由于留學的動機不同,香港學生和內地學生在異鄉過著不一樣的校園生活。香港學生大多以盡快完成學業為目標,不惜Overload(增選科目)、修讀SummerCourses(暑期課程),務求把課程縮短半年、甚至一年,早日回港與家人團聚和工作。相反,內地學生則千方百計延遲畢業,以保持學生身份,藉此留在外國。轉校、轉專業是方法之一,錢寧慨嘆:“讀書的學生,為了獎學金,常常從一個大學轉到另一個大學;訪問學者,為了在美國呆下去,不得不一年換一個地方。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無奈,這種動蕩不安、前途未定的生活總使異國生活所特有的飄浮無根的感覺更加深重。
“打工”才是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在錢寧的采訪個案中,不少碩士生、博士生、學者一面在高等學府里做專業研究,一面在學府外做低下的工作,例如洗碗碟、送外賣、抬死人、收垃圾、帶孩子等。
香港學生就幸福得多了,不僅不需為經濟操心,而且,在紐約、費城、溫哥華、多倫多等富裕城市,開名貴轎車上學的,大不乏人。
留學的動機不同,畢業后的去留抉擇亦迥異。記得初到加拿大時,一位來自上海的工程碩士生問我“你還回去嗎”,香港學生大都跟我一樣,覺得這問題沒什么大不了,畢業后,有興趣的話,把履歷寄給大公司碰碰運氣,運氣不好,便返港找工作。然而,我這位朋友的答案是“一定不能回去”,因為她出國前向親友借了一大筆學費和生活費,若回國內工作,一輩子也無法還清債項。我剛讀到一份香港浸會大學的中國薪酬調查報告,其中助理工程師和貨車司機二項,最令人詫異,在上海開貨車的司機年薪可高達三萬元人民幣,而在上海工作的助理工程師最高薪的,只得二萬四千多元人民幣;若縱觀全國,貨車司機年薪可達四萬二千六百二十元人民幣,助理工程師最高的年薪亦不超過四萬元人民幣。所以,她選擇“留”是可理解的。我認同錢寧所說:“留學生最終留在海外生活,顯然不僅僅是因為西方國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為發達社會的‘物質的誘惑。”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顯然不應該是一種罪過。
追求“美國夢”——家庭、孩子、汽車、狗和穩定的工作,不單是美國人的目標,也是留學生的目標。
留在美國,并取得綠卡的,是否等于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答案乃“不是”。錢寧透過他的訪問,歸納出一個叫人難以置信的現象——“海外生活實際上是很易培養一個人的愛國情操的,其效果往往遠勝于國內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的確,在海外,就連平素“政治冷感”的香港學生也對祖國特別關注。然而,這種愛國情操,至少包含兩個條件:
(一)祖國越抽象越容易愛,一旦具體了,愛起來就困難了。
(二)祖國越遙遠越容易愛,一旦近了,愛起來就不那么容易了。
這種虛擬的愛,歸根究底,似乎與國內的青年爭相出國同出一氣。
錢寧在《留學美國》的開端和結尾都提及留學先驅容閎,他說:“從個人角度來說,容閎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個悲劇。他帶著夢想回國,并為這些夢想的實現百折不撓地奮斗了一生,最后卻看著自己所有的夢想一個個的破滅。”容閎堅信留學教育是中國復興的真正希望,可惜,終他一生,亦無法目睹這夢想的實現;到今天,無數留學生的情感在歸留之間糾纏不清,更是容閎當年所料不及的。
(《留學美國》,錢寧著,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1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