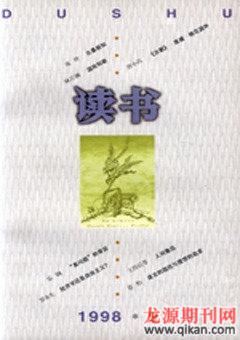也談布萊希特與梅蘭芳
梁 展
早在一九二五年,布萊希特就曾觀看過由當時柏林大導演馬克斯·賴恩哈特(Max Reinhardt)執導,Klabund編劇,取材于我國元曲李行道同名戲的《灰闌記》。而一九三五年的蘇聯之行才促使他真正接觸到京劇藝術和梅蘭芳的表演風格。這段藝術因緣應歸功于當時的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和先鋒藝術家特萊杰亞考夫,他們當時都是特萊杰亞考夫的座上賓。梅劇團三月十二日抵達莫斯科之時,受到蘇聯官方和各界群眾的熱烈歡迎。在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專為梅蘭芳舉行的招待午餐上,蘇聯的大牌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欽科、梅耶荷德、特萊杰亞考夫和著名電影導演愛森斯坦都在座。緊接著,三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梅蘭芳劇團在莫斯科大劇院首次表演。演出之前,先有專人用英、法、俄、德數種語言向觀眾介紹劇情,演出盛況空前。而布萊希特也恰在這時由流亡地丹麥到了莫斯科,推行他和皮斯卡托的“無產階級戲劇”。在這一年三月的一封致妻子威格爾的信中,布萊希特說到達莫斯科的當天,“在蘇聯作家協會進了午餐。我已經看到數場戲劇和電影。相當混亂。梅蘭芳,偉大的中國演員也在這兒。”
梅劇團自列寧格勒演出歸來后的四月十三日是“告別紀念”,地點破例選在莫斯科大劇院,場面異常隆重,就連高爾基也都到場了。布萊希特觀看了梅蘭芳、王少亭合演的《打漁殺家》,這出戲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月十四日,他再次觀看了梅蘭芳臺下“身著黑色禮服”的表演動作示范,并參加了由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召集的梅蘭芳戲劇討論會,還應主持人丹欽科之邀,首次談到了對中國戲劇的看法。
這份發言記錄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斯拉夫語教授拉爾斯·布萊堡教授整理、保存下來,它已經由梅紹武先生翻譯并于一九八八年發表。根據這份資料,我基本上可以得出兩點不同于以往的看法。
其一是:布萊希特對中國戲劇的偏重形式的看法本身,是受到了特萊杰亞考夫的影響。作為蘇聯先鋒藝術家的特萊杰亞考夫是位著名的東方專家,曾在北京大學做過教員,漢名鐵捷克。魯迅曾在書信中提到過他和他的劇作《怒吼吧!中國》。早在一九三○年,特萊杰亞考夫在首次訪問柏林時,布萊希特就結識了他。一九三一年,特萊杰亞考夫再次來到柏林時,他的“操作文學(operativerLiteratur)”或“事實的文學(Literatur desFaktes)”的藝術觀念對“布萊希特圈”的藝術家們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后來,布萊希特還曾經為《怒吼吧!中國》所表現出的有違世俗的藝術方式做過熱情的辯護。兩人間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在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那次莫斯科討論會上,他(特氏)最先發言指出中國戲劇是封建道德的宣傳工具,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忠誠和謙恭,但他馬上話鋒一轉,說了下面一段話:
……中國戲劇是一種宣傳鼓動性的戲劇,這種戲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有意識地使其中意味深長的成份直扣觀眾的心弦。它并不直接反映,它要求觀眾在視覺和聽覺上予以加工分析。
布萊希特在后來的發言中,肯定了特萊杰亞考夫的把中國戲劇看作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的看法,但他并沒有注意到這位藝術家或東方專家對中國戲劇內容所做的批評,而是看重了特萊杰亞考夫所說的宣傳鼓動功能和“不直接反映”而要求觀眾“加工分析”的形式特征。不管特萊杰亞考夫的觀點對否,布萊希特對這位東方專家的意見是不加懷疑的。另外,通過對一九三五年布萊希特的發言與《布萊希特全集》中所收的《論中國戲劇》的對比,可以發現兩者內容十分一致。后者實際上是一些短評匯集,其內容最先出現在倫敦一九三六年冬出版的《今日生活與文學》上作者發表的《對中國表演藝術的一些評論》中。本雅明就是參考了上文作了《什么是史詩劇?》。這說明西方學者所看到的布萊希特對中國戲劇的表述是脫離了一九三五年莫斯科討論會這一重要歷史情境的,他們沒有看到布萊希特背后特萊杰亞考夫的影子,然而就是這個特萊杰亞考夫的影子造成了布萊希特對中國戲劇很有旨趣的“誤讀”。
其二是:布萊希特不是在觀看梅蘭芳表演之后,才使用“陌生化或間離效果”這個術語,而是在此之前就試運用它了;不是布萊希特從梅蘭芳那里借過了“陌生化”表演方式,而是他已經在用“陌生化”理論來解釋梅蘭芳的表演藝術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英國戲劇學者魏勒特根據布萊希特一九三六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的一行邊注(即:“一九三五年梅蘭芳一行人在莫斯科進行表演,這篇文章即緣此而作。”)就斷定“陌生化或間離效果”產生于一九三五年對梅蘭芳表演的觀看之后。但萊因霍爾德·格林(Reinhold Grimm)教授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里,把這一術語的根源追溯到了一九三○年,即布萊希特創作《例外和常規》一劇中對于與陌生化(Verfremdung)詞義相近的“befremdend”、“befremdlich”兩詞的使用那里了(Brechts Drame,stuttgart,1984.S.24.)。讓我們再回到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那次討論會上,布萊希特有一段話是這么說的:
我在上次訪問莫斯科期間,曾經有機會同特萊杰亞考夫同志以及他那些文學評論界朋友交談。我開始認識到蘇聯學者已經展開一種新的觀點,這種觀點可以給運用到那種應該取代陳腐的亞里斯多德概念的現代美學里去。這個觀點,恕我的俄語發音不準確,是“Ostranenie”。在德國新戲劇里,我們試用“陌生化”或“間離化”這個術語,同時這也多多少少改變了蘇聯學者那個概念的內涵。
正如格林(Grimm)教授等一些西方布萊希特專家所指出的那樣,“陌生化”概念之來源是與三十年代盛行的俄國形式主義思想及其“尖銳化或陌生化(Ostranenie)”的手法緊密相關的。布萊希特的上述談話印證了這個觀點。它說明,早在一九三三年布萊希特的第一次蘇聯之行之時,“陌生化”的概念就在他的思想中孕育成熟,因此,所謂一九三六年才產生此概念的說法站不住腳了。與“Ostranenie”不同的是,布萊希特的“陌生化或間離效果”為前者加上了意識形態因素,從而使它由一個純藝術形式手段上升為一個藝術—社會學概念。在這個創造中,特萊杰亞考夫是中介和橋梁。上文引述的,特萊杰亞考夫關于中國戲劇“有意識地使其中意味深長的成份直扣觀眾的心弦”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形式主義代表人物什克羅夫斯基(
事實上,二十年代初期,布萊希特深受皮斯卡托“政治戲劇(DaspolitischeTheater)”的影響,后者在一種“歷史化”的場景中展現出某種統一的、批判性的立場(Haltung),這給劇作家以深刻的啟發,并使他漸漸地對亞里斯多德式的,建立在“幻覺(Illusion)”、“共鳴(Einfühlung)”、“凈化(Katharsis)”等藝術機制(Organon)之上的傳統戲劇發生不滿,進而在皮斯卡托之后提出“史詩劇或敘述體戲劇(dasepischeTheater)”對抗傳統的、以動作模仿為指歸的“動作戲劇(dramatischeTheater)”。在《馬哈哥尼城的興衰》(AufstiegundFallderStadtMahagonny)一劇的評注里,他要求“敘述體戲劇”不是“體現事件”而是“敘述事件”;不要將“觀眾卷入行動,消耗其主動性”,而要“使觀眾成為觀察者、喚起其主動性”。從而對演員的表演性質及其與觀眾的關系提出新的看法。一九二六年以來,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產生了“教育劇(Lehrstueck)”的理論構想。“教育劇”,在布萊希特看來,是一種戲劇實驗,一種對世界的概念式把握,它原則上不需要觀眾,演員既是劇中人,又是教育者,還是觀眾(Ibid,S.1024.)。基于上述觀念,布萊希特把這種“史詩劇或敘述體戲劇”的諸因素,“歷史化”、“立場”、“角色間隔”等等都投射到了梅蘭芳的表演中。
在布萊希特看來,中國演員“觀察自身(Sich-Selber-Zusehen)”的表演使他與觀眾間不存在所謂“第四堵墻”,從而有效地避免了觀眾的“共鳴”,在一九三五年的那次討論會上,他還認為這種表演方法給觀眾留下了批判性思考的空間;梅蘭芳“男扮女妝”只是將女性留給男性的印象表現出來,不至于使我們把演員誤認為人物,起到了角色間隔作用。更讓人感到驚奇的是,布萊希特竟然從《打漁殺家》中那個“蕭桂英”搖櫓的經典場景里“看”出了更多地符合自身旨趣的內容:
但這搖櫓的動作好像是歷史的,為許多歌曲所傳頌,每個人都熟知這不平凡的駕船動作。這盡人所知的姑娘的每一個動作皆可入畫,而河流的每一次拐彎都是一次冒險,人們認識到,就是這所遇到的小河彎曲也是熟悉的。觀眾的這種情感是由藝術家的立場喚起的:正是這一立場使這搖櫓聞名起來。
由演員的外部表演向著他的內在化的、歷史的、批判性的“立場”推進,布萊希特顯然是在用“史詩劇”的眼光來看待梅蘭芳的表演了。而按照梅蘭芳自己對同一場面的解釋來看,“蕭桂英搖櫓”經過了藝術的改造,出于“美”的立場,表演者沒有把生活不加改變地搬上舞臺。在京劇中,表演者的眼睛的“自我觀察”,旨在引導觀眾,它沒有造成“出離自身而存在(Ausser-Sich-Sein)”的效果,反而使觀眾真正投入到了劇情當中。
按照梅蘭芳的真實表演意圖所表現出的內容必然不符合布萊希特“史詩劇”的標準和要求。因此,當布萊希特一九三七年在《中國表演藝術中的陌生化效果》中,再度思考中國戲劇時,清醒地批判了它的非科學的表現方式:“中國的演員從魔術的符咒里取得他的陌生化效果”,“演員只表現神秘,而不向觀眾揭示謎底”,京劇“對人類激情的表現是程式化的”,其“社會概念是刻板的、錯誤的”。這種從形式回溯到內容的分析方法,使布萊希特沒有停止在對中國戲劇的簡單認同上,而是達到了批判的深度,思想家布萊希特的價值恰恰體現在這里。在此,我對于國內一些學者,只頌揚他對中國戲劇認同的一面,而不提批判一面的做法,深感不能贊同。
俱往矣。但這段藝術因緣永遠令人深思。你盡可以說,布萊希特對于中國戲劇的表述是薩伊德(Said)所說的“西方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對東方的解釋”造成的“東方不是東方”的現象,或者是“西方中心論”,進而指責其為“文化霸權”;也可以說是布魯姆(H.Bloom)的“誤讀”,但人或藝術是一個不會衰竭的生命系統,它自身需要一個不斷衍進的生長點。在此意義上,我愿反薩伊德“理論旅行”之意而用之,因為我把“旅行”看作是一種理論的生長過程,對此,布萊希特由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到自己的“陌生化”概念,再到梅蘭芳的“陌生化”的探索歷程最具說服力,只是理論在這一“旅行”之中,需要經過不斷的批判而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