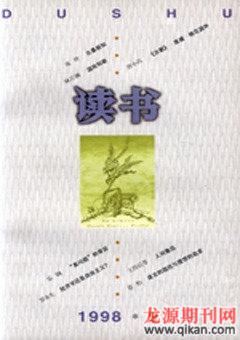關于亞當·斯密的兩部書
紫 雪
《讀書》一九九八年第六期樊綱的《“不道德”的經濟學》批評“人們經常援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例子,說他寫了《國富論》之后又寫了一本《道德情操論》,……并由此推論經濟學家應該講道德。”令人吃驚的是:作者將一七七六年《國富論》與一七五九年《道德情操論》先后顛倒,并作為“經濟學不要講道德”的論據。
按說兩本書寫作的先后并無太不得了,可在這里,它關系“經濟學鼻祖”的根基經典,涉及“道德”與“經濟”的先后根由,所以不能不加以討論。
亞當·斯密一七五一至一七六三年在格拉斯哥大學先后任邏輯學和道德哲學(包括倫理學)教授,在倫理學講義的基礎上,一七五九年二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頗得好評,多次再版;《國富論》則于一七七六年三月九日出版,標志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斯密也被尊為“經濟學之父”。《道德情操論》雖“名氣”不及《國富論》,但凡講斯密大抵要談此書。不僅由于博學的斯密一生主要專著即此兩書,而且兩書的關系亦為研究者注重。埃里克·羅爾(Eric Roll)在其名著《經濟思想史》中講斯密《國富論》“構成該書基礎的社會哲學是當時廣泛承認的,他的老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就是這種社會哲學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約翰·雷(JohnRae)的《亞當·斯密傳》被公認是有關斯密“最詳盡、最優秀的傳記”,其中記述哈奇森對斯密的影響包括道德情操與經濟學說。熊彼特(J.A.Schumpeter)在《經濟分析史》第一卷中介紹當時道德哲學“主要由自然神學、自然倫理學、自然法學以及政策學(或‘治安學)構成,而政策學又分為經濟學和財政學(‘稅收)。A·斯密的老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的就是該意義上的道德哲學,A·斯密也是如此。《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都是從一較大的有系統的整體上分割出來的部分。”這說明了兩書的關聯。斯密本人在《道德情操論》初版時就說還要寫一專著來完成系統研究,到一七九○年(逝世前)第六版說在《國富論》中“我已部分履行了自己的諾言,至少履行了論述國民收入和軍備的諾言。”此版最重要的是新增一章“論道德情操的墮落”。法學家塞繆爾·羅米利(SamuelRomilly)曾評價斯密本人“總認為《道德情操論》是一部遠比《國富論》杰出的著作。”詹姆斯·博納(JamesBonar)編制斯密藏書目錄,政治經濟學和歷史類書共占不過五分之一。馬克·布勞格(Mark Blaug)等主編的較權威的專業工具書《世界重要經濟學家辭典》中就將斯密首先界定為倫理學家——這些很能說明一些問題。
另外,作者主張經濟學不講道德,卻又說“經濟學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實證地考察、分析,現實中,人們是否是自私的、甚至是一有機會就會損人利己的……。”還用了“好的經濟學分析”等價值評判語,這些不正是倫理學要做的?說經濟學以“性本惡”為前提,而設計經濟政策與制度來“防范欺詐、防范惡行”等等,“制惡”不就是倫理學的意義或法學的功能嗎?(不能否認手段或途徑的不同)經濟學不僅內涵牽涉繁博,而且外延顯呈動態,概念如經濟哲學、經濟觀念,學科像文化經濟學、倫理經濟學等等,不好籠統而論,更何況講“效益”就很難離開“公平”。尤其在“經濟人”之局限越發顯現的時代,“不講道德”傾向的“經濟學”越來越受到質疑批判。如K.E.博爾丁(Boulding)主張經濟學的重建,一九六九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作為一種道德科學的經濟學》;J.M.布坎南(Buchanan)進行倫理準則與期望價值等方面的研究,一九七八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市場、州和道德范圍》,這些都是著名經濟學家。
總之,“務正業”確實要大力提倡。不過,即便主張經濟學不講道德,但“理直氣壯”地宣稱經濟學家就是“不講道德”,總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