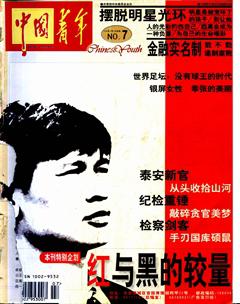用汗水證明自己
張茜
等我明白眼淚流得再多也沒用的時候,我長大了。那年我21歲。
雖然我生在農村,家里的條件并不好,但我是家中的幺女,從小嬌生慣養,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并如愿以償地走進了師范學校的大門,圓了我們兄妹幾個都不曾圓過的求學夢,我成了一個“公家人”。
轉眼間,3年的學習生活結束了。師范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一個只有20來戶人家的山村小學任教。學校建在山村惟一的一片開闊地上,離村莊還有二三百米的路程,孤零零地站在一片風聲里,像個寂寞的島嶼。當我在牛車的搖晃中走過20多里的山路趕到那個小山村時,已經沒有勇氣走進那簡樸的校舍了,惟有眼淚一串接一串地滾落下來。
迎接我的是一位剛剛辦了退休手續的老教師,他已經超期服役好幾年了。他用一種注滿滄桑的口氣勸我道:“既然已經來了,哭有什么用,時間長了,你就習慣了。”
晚上,我一個人躲在那漆黑的小屋里,連燈也不敢點,我用桌子凳子將門緊緊地堵住,聽著遠遠近近的狼嗥,流著淚度過了第一個不眠之夜。
第二天,我見到了我的學生,十四五個孩子,一至四年級的都有,是山區典型的復式班。孩子們眼巴巴地看著我,那臉上的表情甚至比我還要“復雜”。大概他們太害怕失學了,有一個大膽的孩子竟然拉著我的手問:“老師,你還走嗎?”我無言以對,還沒有“開張”,我就對著我的學生流淚了。
孩子們的功課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那位老教師大概是在退休前剛轉正的民辦教師,能夠每月掙著幾十元守著十幾個孩子已經很不容易了,山村與外界又相對封閉,孩子們所學的知識自然要大打折扣。想到我已經沒有退路了,在這個山區小縣,除了這群孩子外,目前不會有人再“收留”我。痛痛快快地流過淚水之后,我平靜了,我寫信告訴遠方的父母:“這里一切還好,你們不要為女兒擔心。”其實,我知道,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
我開始向挫折與壓力挑戰。從來沒有上過鍋臺的我很快就學會了做飯,盡管我吃了整整一個月的夾生面;我學會了流著汗帶領孩子們重建校園,自制了雙杠、單杠和乒乓球臺,并和孩子們一起上山搞小秋收,從而使這小山溝里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紅旗,孩子們第一灰穿上了整潔的校服。村里的大媽大嬸們無不時刻關心著我這個遠方來的倔丫頭,從生活上給了我很多關心和照顧。我在這里慢慢地扎下了根。
我在告別了淚水之后用汗水證明:我還行!
不久,經同學介紹,我在縣城認識了一個小伙子。當他知道了我的一些想法后,竟然辭去了在縣工商局的工作,自愿來到我所在的山區小鎮做了團委書記。他說:“你是對的,也許,這樣能夠使你和孩子們的心貼得更近些。”結婚后,我們沒有購置什么家具、電器,這在山村里還用不著,我們倆用所有的積蓄買了一輛摩托車,這樣,我和丈夫幾乎每天可以“鵲橋會”了。我教的孩子一個接一個地飛出了山村,飛進了他們夢想的校園。我本人也多次被評為“優秀教師”,還被破格聘為“一級教師”,這在與我同時畢業的同學中是不多見的,
至今,那位老教師的話依然回響在我的耳邊,作為一個剛從學校走向社會的女孩子,不可能總是希望社會來適應自己,更多的時候,是我們在適應社會。困難的日子,遭受挫折和生活打擊的時候,流點眼淚是正常的,微不足道的。假如我們在流過眼淚之后記得用汗水證明自己,腳下的路千萬條,我們一定能找到一條屬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作者通聯:043003山西省侯馬市中條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