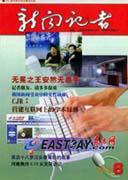輿論監督“步步高”
蔡銘澤
今年4月12日,羊城晚報發表著名專欄評論作家微音的文章《為市人大高歌一曲<步步高>》。文章指出,在廣州市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人大代表對市府各有關職能部門的質詢多達8次,可謂盛況空前,聽者開心,閱者高興。這說明:廣州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又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人大代表的監督作用也由此逐步強化起來。筆者注意到,今年以來不僅人大代表的監督作用在不斷強化,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作用也在不斷強化。我們真應該為廣州乃至全國輿論監督的進步高歌一曲“步步高”。
為新聞輿論監督唱“贊歌”,并非作者囿于一己私見,而是有充分事實根據的。綜觀今年1—4月各報的輿論監督,我們以為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輿論監督的密度明顯加大。輿論監督是新聞媒介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賦予新聞媒介的神圣權利,也是新聞媒介生存競爭和發展的重要手段。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民主法制建設的不斷進步,輿論監督在國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新聞媒介無一不花大力氣開展輿論監督工作。從數量上來看,各報尤其是各級黨報輿論監督的報道明顯增多了。以人民日報為例,1—3月該報共發表有關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34篇,每個月達到11篇以上。這在該報的歷史上是不多見的,更何況1、2月份還有元旦和春節兩個重大的喜慶節日。新千年喜慶剛過,廣州的南方日報立即駛上了輿論監督的“快車道”。1月3日,該報率先刊登《非常師生,非常家長》長篇報道。報道涉及幼兒過早接受教育問題,批評了部分“翻過跟斗過來的”家長至今還抱著“棍棒之下出英才”的想法。文章認為,“大人的憂患意識過早地感染了孩子,使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改變了天性,變得早熟,有的甚至造成心靈的創傷。”由此引起了全社會包括中央領導人對教育問題的重視。據統計,僅1月份,南方日報即發表有關輿論監督方面的報道57篇。其中,1月10日即有24篇,這一天的第二版更是圖文并茂,聲勢強勁。
第二,輿論監督的頻率明顯加快。一般人認為,輿論監督是一種揭露性報道,是要經過有關部門“批準”的,如此一來輿論監督的時效性必然大受影響。但從近年來特別是今年以來輿論監督的實踐看,這種認識顯然失當。毫無疑問,為了保證輿論監督的準確性和權威性,重大的批評性或揭露性報道必須經過上級有關部門的批準。例如,近來有關“湛江走私案”、“廈門走私案”、“胡長清受賄案”和“成克杰受賄案”的報道均是如此。但是,這絲毫不影響新聞媒介開展輿論監督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事實上,今年以來人民日報和南方日報所發表的輿論監督稿件(主要是批評性報道)除極少數大案要案是統發稿外,其余均是自行采集的。以南方日報為例,2月份該報發表的32篇輿論監督稿件有28篇是自行采集的“本報訊”,只有4篇是采用新華社的通稿,“本報訊”約占88%。由于充分發揮了新聞媒介的主動性,輿論監督的時效性大大加快,日報一般是次日見報,晚報大多是當日見報。不僅如此,各報在整體增加輿論監督密度的基礎上,還注意推出自己的“拳頭產品”,使輿論監督不斷形成新的“熱點”和“亮點”。1月25日,廣東省九屆人大三次會議剛一開幕,一件大新聞即和新聞工作者不期而遇:佛山市人大代表就四會電鍍城環境污染問題質詢省環保局。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和廣州日報立即主動展開全程跟蹤報道,掀起了今年以來輿論監督的第一個熱潮。當天,南方日報立即以《四會南江電鍍城排放氰化物一案今見分曉》為題加以報道。第二天,該報又在頭版中心版位以橫排通欄標題和三幅照片推出了組合報道。據報道,質詢會“火藥味”濃,王局長表態誠懇,但未獲通過。報道還特別以新聞背景的形式介紹了代表質詢的三條理由:第一,環保評估報告未出臺、未經批準就搞建設是違規的;第二,跨區域影響的有污染建設項目沒有征得另一方同意;第三,電鍍城選址不對。應該說,這些報道是客觀、實事求是和兩面俱呈的,但又是明顯傾向于支持人大代表的質詢。對于南方新聞媒介這次成功而精彩的輿論監督,人民日報也立即介入,并在2月23日出版的第56期《民主和法制》周刊的《監督廣角》專欄中以《沉甸甸的質詢案》為題予以及時總結。文章說:“就人大會議上的‘質詢本身而言,似乎并沒有構成特別的‘新聞意義。……此次質詢最引人注目的焦點在于,省環保局負責人的答復,代表表決為‘不滿意,出乎意料。人大代表對答復表示不滿意,甚至意見比較尖銳和激烈,這在人大會議的歷史上是罕見的。這反映了人大代表忠實履行職責的自覺意識,不再像以前那樣‘只要政府說的都是對的,‘代表代表,開完會就了。”事實上,人民日報的《民主和法制》周刊本身就是輿論監督不斷進步的一個標志。該刊從1999年初開辦以來越辦越好,真正做到了及時反映和總結全國新聞媒介輿論監督的動態和經驗。
第三,輿論監督的范圍明顯拓寬,內容更加實際。對輿論監督的界定,新聞界歷來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從新聞事業的戰斗性出發,認為輿論監督是新聞事業對革命隊伍內部錯誤思想和行為所展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按照這種觀點,新聞事業的戰斗性體現為新聞批評,新聞批評演變為輿論監督。但這樣容易將輿論監督限制于一個狹小的范圍內,而且容易使其蛻變為純粹的斗爭工具。另一種是從新聞事業的“環境監測”功能出發,認為新聞媒介對全社會負有監測和督促的職責,大凡對政府及其官員的監督、對公民個人品行高下的評判以及對社會風氣良否的引導均可納入輿論監督的范疇。而這樣又容易使輿論監督的范圍失之過寬,并且有可能誤導新聞工作者產生“無冕之王”的虛妄心理。因此,這兩種觀點都不利于輿論監督的健康發展。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公民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檢舉的權利(請參見本刊今年第4期闞敬俠的文章《論我國的輿論監督法律制度》)。根據這一規定,輿論監督的定義應該是:新聞工作者代表公民行使監督權,在了解情況的基礎上,表達輿論、影響公共決策的一種社會現象。隨著這種觀點為新聞界普遍接受,輿論監督的主體、對象和方法也隨之進一步明確,使之更加貼近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繼1月底廣東省人大質詢案之后,3月底全國新聞媒介再次掀起輿論監督的高潮。和上一輪高潮相比,這一輪輿論監督高潮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它所涉及的話題都是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直接相關的。先是3月24日中國青年報等以顯著的版位報道了“姚麗事件”,積極為因“沒有挺身而出”與打劫銀行的歹徒進行殊死搏斗而被“雙開除”的大慶市建行營業員姚麗鳴不平。接著,為配合廣州市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召開,羊城晚報集中報道一系列與廣大市民密切相關的事件:“自來水提價”問題(3月20日),“指定燃氣具”壟斷經營問題(3月24日),“個體中巴整頓”問題(3月27日)和“日放粉塵數噸,危害居民卅萬”的廣州水泥廠遷移問題(3月28日),等等。這些問題既為老百姓密切關注,自然也為人大代表積極主張。因此在廣州市人大會議期間,人大代表先后就這些問題向市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提出了尖銳的詢問。其中,人大代表提出的關于“白云山風景區亂建豪宅”(4月6日)和“緩建廣州歌劇院”(4月8日)的詢問案,反響尤為強烈。正如羊城晚報4月11日報道會議閉幕的消息時所指出的,這次人代會“因執著于民生問題而深得民心”,“人大關注的正是百姓關心的”。這些新聞讓廣大市民眼前一亮:現在的人大大不一樣了,民主氣氛很濃,政府官員再也難當“太平官”了。這正是輿論監督的威力所在。
輿論監督歷來被認為是一件難事,有人形容輿論監督“稿件采訪難”、“謝絕人情難”、“擺脫糾纏難”、“應付官司難”。上述輿論監督的進步正是克服了這些“難點”而取得的,它有著深厚的社會背景。從根本上說,這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不斷進步的必然結果。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輿論監督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為新聞界開展輿論監督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指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同健全法制緊密結合,實行依法治國。”所謂依法治國,就是人民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輿論監督。1998年7月,朱镕基總理為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題詞,勉勵新聞工作者積極開展輿論監督,做“民眾喉舌,政府鑒鏡,改革尖兵”。為推進反腐敗斗爭的深入發展,尉健行同志最近強調指出:“要重視和善于發揮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要選擇典型的違紀違法案件進行深入報道,營造反腐敗的輿論氛圍。”這樣,就極大地鼓舞了新聞界開展輿論監督的勇氣。
其次,全社會特別是人民代表民主法制意識不斷加強,為輿論監督的進步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和發展,作為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我國人民的政治文化素質特別是民主法制意識得到了全面提升,因此,人民代表當家作主意識便有了歷史性的進步。以廣東省人大代表為例,類似質詢省環保局的事并不是第一次。例如,1994年11月有21名人大代表就省國土廳拒不執行《城鎮房地產權登記條例》提出質詢;1995年2月江門代表就325國道擴建問題對交通廳的質詢。在今年3—4月召開的廣州市第十一屆第三次人代會上,代表們共提出8件詢問案。這些充分反映了人大代表民主和法制意識空前覺醒,他們忠于職守和參政議政的能力日益增強。這正是輿論監督得以迅速進步的源泉所在。
再次,各級政府特別是各級人民法院為輿論監督的順利展開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今年1月底,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央新聞單位座談會上明確表示,“人民法院支持輿論監督”。他說,“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人民法院與新聞媒體的任務和目標是一致的,希望新聞單位和人民法院相互了解、理解、諒解,互相支持,互相合作,共同促進司法公正和社會進步。”為此,他還提出了保護新聞媒介進行正當的輿論監督的六條具體的司法保護措施。為了切實鼓勵和保護輿論監督,各級地方黨政部門也先后制定了一些關于輿論監督的辦法。1999年6月,珠海市委和市府首先出臺了《珠海市新聞輿論監督辦法(試行)》。受這個文件的鼓舞,珠海市新聞工作者展開了一系列重大的輿論監督報道,他們自豪地把1999年稱為珠海市新聞界的“輿論監督年”。最近,安徽省政府法制局發出通知,要求縣級以上政府鼓勵和支持新聞單位對行政機關違法、違紀行為進行監督曝光,并建立和健全新聞曝光案件追查制度。這些辦法和通知雖然還不具備法規的性質,但其權威性是不容忽視的,它表明我國新聞輿論監督正在步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軌道。
最后,新聞界自覺遵守法律法規,依法開展輿論監督的水平迅速提高。依法開展輿論監督是避免新聞官司的關鍵,以前在這方面新聞界是有過深刻教訓的。據專家披露,從1983年1月我國第一起新聞官司(《二十年“瘋女”之謎》)到1994年的180起新聞官司中,絕大部分是新聞界敗訴。之所以如此,新聞法制建設滯后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與新聞界不懂法、不守法也有密切關系。近年來,新聞界普遍吸取了教訓,注意自覺遵守法律法規,依法維護輿論監督的權威。這樣,新聞界在開展輿論監督時就有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例如,在輿論監督的對象上,注意嚴格區分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和一般法人和公民,對前者大膽實施輿論監督,對后者則審慎從事,盡量避免新聞侵權;在新聞真實性問題上,十分注意事實的真實和準確,不道聽途說和主觀臆斷;在報道方法上,注意使用客觀報道和平衡報道的手法,對人對事盡量兩面俱呈,避免片面性;在思維方式上,注意摒棄單向思維方式,代之以全方位、多層次和往復式思維方式,克服過去那種非此即彼、非好即壞的弊端,在主持社會正義的同時,力求留有余地。隨著輿論監督水平和藝術的提高,新聞界也積極依靠法律維護自身的權利,并且在一些“新聞官司”中勝訴:1月6日,華東方面首先傳出無錫日報社訴中國足協并獲賠3萬元和被告賠禮道歉的消息(最近雙方調解成功);1月19日,廣州的南方都市報社也在一起侵害名譽權案中勝訴;4月3日,山東電視臺記者孫震博訴海陽市人民政府侵犯名譽權案勝訴,獲賠精神損失和其他損失費16000余元。這3起“新聞官司”分別代表了新聞界和公民、法人及政府三種不同的新聞法律關系,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它說明我們的國家已經進入民主和法制的新時代,新聞界也步入了依法開展輿論監督的正確軌道。
當然,就此斷言我國的輿論監督已經全線告捷,恐怕還為時過早,因為輿論監督在不少地方至今還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們沿著這條路堅定地走下去,那么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輿論監督在新時代必將大有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