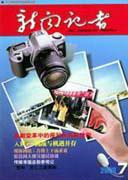充分表現(xiàn)西部大開發(fā)之“新”
蘇繼賞
黨中央國務(wù)院提出西部大開發(fā)的戰(zhàn)略方針,有的專家撰文說,這等于“再造一個中國”。這句話概括了開發(fā)西部的全部重要意義。這對西部人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在今后漫長的年月中,西部新聞媒體都要牢牢把握這個母題;對報紙來說,這是一個嶄新的課題。
從五十年代起,歷史上曾有過多次開發(fā)西部的舉動,每次都轟轟烈烈,每次都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但這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從地區(qū)上說,過去的西部僅指西北五省,現(xiàn)在則包括十個省市。最近,連內(nèi)蒙古和廣西也自愿加入大西部的行列。從前是在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靠國家投資建設(shè)項目,現(xiàn)在雖然還需要國家投資,但主要靠吸引區(qū)內(nèi)外、國內(nèi)外和社會方方面面的資金。過去一提開發(fā),就意味著辦工廠,開荒地,現(xiàn)在則是首先抓基礎(chǔ)建設(shè),把西部變成有吸引力的市場。過去,在開發(fā)中,常常忽略了生存,有時甚至是以犧牲生態(tài)為代價的;現(xiàn)在的開發(fā)是把保護生態(tài)放在首位。西部是資源型省份,過去講開發(fā),一般指的是開發(fā)礦藏,現(xiàn)在則是要按市場需要,市場需要什么就上什么,自然也要把高科技放在重要位置……這種不同還可舉出許許多多。這些不同就是事物的“新”。這些還僅僅是表現(xiàn)在物質(zhì)和制度層面上的“新”,至于思想觀念領(lǐng)域的“新”就更多,能否表現(xiàn)出西部大開發(fā)的“新”,就成了考察新聞媒體質(zhì)量好壞的一個重要標志。我們深切感受到開發(fā)西部對報紙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機遇。如果我們能抓住這個母題把報紙的質(zhì)量努力促上去,贏得讀者的親善,報紙就有前途;否則,報紙的生存都會發(fā)生問題。為此,《新疆經(jīng)濟報》編委會特地作出《深化報紙改革,提高報紙質(zhì)量,迎接西部大開發(fā)的決定》,發(fā)動全體編輯、記者學(xué)習(xí)、討論。
我們的報紙既是機關(guān)報,又有商品的屬性,也要遵循市場經(jīng)濟的規(guī)律參與競爭。報紙的競爭也是新聞產(chǎn)品質(zhì)量的競爭。新聞產(chǎn)品的質(zhì)量指的是思想和文化含量。提高報紙質(zhì)量就是要提高報紙的思想文化含量。在西部大開發(fā)中,社會生活會有大量新人、新事物出現(xiàn),按照舊的思想經(jīng)濟,很難完全理解這些新事物。解疑釋惑就成了讀者的普遍要求。報紙不僅擔(dān)負著服務(wù)、娛樂、消遣功能,而且還擔(dān)負著認識(也即教育)功能,過去大報忽略了娛樂功能,當晚報體現(xiàn)了這個功能時,一下子就把讀者爭取過去。大報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也想走晚報的路,這是不對的。大報要照顧到娛樂功能,但千萬不能丟掉認識功能。面對社會生活中出現(xiàn)的大量新事物,報紙有責(zé)任向讀者解釋清楚這些新事物“是什么”。在感性層次上解釋還不夠,還需要在理性層次上解釋清楚,從這個意義上講,現(xiàn)在是需要思想、需要理論的時代。報紙承擔(dān)著重要的啟蒙任務(wù),西部大開發(fā)的形勢要求報紙必須提高新聞稿件的思想深度,提高稿件的思想文化含量。發(fā)表在報紙上的重要稿件,一定要使讀者看了心有所得,思想上有所啟發(fā)。由于我們多年的提倡,在我們《新疆經(jīng)濟報》上出現(xiàn)過許多這樣的新聞。許多從事實際工作的人,他們做了事,創(chuàng)造了經(jīng)驗,但并不知道其意義何在。借著記者的稿件,他們的認識有了提高,弄清楚了意義所在,因此非常歡迎這樣的稿件。所以我們提出,必須寫好一版頭題新聞。頭題新聞應(yīng)是政治性新聞或者是意義新聞。事物既有感性層面的表象,也有理性層面的義理。表象和義理的合一,才是事物的全部和整體,意義新聞和政論性新聞就是要體現(xiàn)這樣的合一。
新聞姓“新”,報紙的基本特征是“新”,如果“新”被淡化了,被漠視了,報紙就會被讀者拋棄。同樣,對西部大開發(fā),如果抓不住它的“新”,就可能產(chǎn)生錯誤導(dǎo)向,引導(dǎo)到計劃經(jīng)濟的老路上去,這是牽涉到輿論導(dǎo)向的大問題。
八年前我們提出新聞業(yè)務(wù)改革時,就把求新放在重要位置。八年下來,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總不能盡如人意。新聞工作是思想勞動分量很重的職業(yè)。出于新聞記者之手的有些稿件只是傳播信息的報道,還不太費腦筋;有許多稿件則是要寫成新聞作品的,那就要觀察、要捕捉、要思考、要提煉主題、要選擇恰當?shù)慕Y(jié)構(gòu)形式,要精心遣詞造句,每個環(huán)節(jié)上都要動腦子。只要仔細閱讀獲得普利策獎的新聞作品,就會發(fā)現(xiàn)它們都不是簡單的報道,而是精心構(gòu)造的新聞作品。多年來,因為我們的記者不研究新聞寫作技巧,不重視新聞寫作技巧,新聞只是材料的簡單整合,在內(nèi)容上,或是對采訪對象談話的如實記錄,或是實際工作的流水紀實,或是對一個事物運作過程的輪廓勾勒。沒有記者的認識,沒有記者的見地,沒有記者的思考,一句話,記者沒有動腦子,連粗加工都不到位,讀起來索然乏味。
再看看新聞的形式,事物的內(nèi)容和形式本來是統(tǒng)一的,互為存在的條件,彼此之間,應(yīng)沒有高低上下輕重之分,但在我們的認識上,常常重內(nèi)容輕形式。新聞記者不研究與新聞內(nèi)容相符合的形式,照說,有什么樣的內(nèi)容就應(yīng)有什么樣的形式,新聞的內(nèi)容是多姿多色的,形式也應(yīng)該是多變的。新疆有一位學(xué)者說得好,新聞無常法,無法之法是為新聞法。而我們的記者恰恰不重視新聞的形式,不管什么內(nèi)容都往一種模式中套。這同樣是不動腦子。新聞稿件本應(yīng)分為新聞報道和新聞作品的。但我們的記者卻無視新聞作品形式的存在,篇篇都寫成信息報道,篇篇都是一種形式,就是讀者戲稱的“豆腐塊”,“豆腐塊”產(chǎn)生并不要緊,方寸之內(nèi),同樣能寫出好的新聞作品。但仔細剖析我們記者筆下的“豆腐塊”的結(jié)構(gòu),只是由導(dǎo)語+三段式(背景、展開、結(jié)果)組成的一個固定框架。不論什么內(nèi)容都往這個框架中套,這樣就減少甚至喪失了新鮮感。在我們報紙上,套用模式似乎成了記者的一種思維慣性。在這里不妨借用“異化”這個詞來說明,許多時候不是記者在用模式,而是模式套住了記者,記者為模式支配,被模式牽著走。如果不從這種思維慣性中解脫出來,就很難表現(xiàn)西部大開發(fā)的“新”。因此,我們要求記者稿件必須篇篇新,這個新應(yīng)包括新聞事實新、觀點新、見解新、結(jié)構(gòu)新、語言新。當然,一篇稿件中不可能具備這許多“新”,但是至少要有一兩項“新”,那種一項“新”都不具備、老腔老調(diào)不傳達任何信息的稿件絕對不用。
對編輯來說,也有求新的任務(wù),不能就稿編稿,不能有啥稿就編啥稿。不能把編輯理解為拼湊,理解為劃版,理解為簡單的裝配。編輯是創(chuàng)造性勞動,編輯的過程就是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在版面上要有編輯的智慧、編輯的思想、編輯的語言,要力求版式新、標題新、設(shè)計新、編排新,除此,還要有生動的評點,要有思想內(nèi)容厚實的按語,編輯對重大事件要有自己的態(tài)度。
經(jīng)過八年的新聞業(yè)務(wù)改革,在求新這一點上,《新疆經(jīng)濟報》的編輯、記者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培養(yǎng)成了創(chuàng)新思維,寫出了許多好的新聞作品,編出了許多好的版面。但是也有一些編輯、記者還缺乏創(chuàng)新思維,還是維持著重復(fù)性思維,奉行著經(jīng)驗主義,在舊式框架中轉(zhuǎn)悠。“新”就是事物發(fā)展中現(xiàn)出來的“異”,記者的天職是尋找事件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異”,記者的本領(lǐng)正表現(xiàn)在對“異”的敏感上,異是新,同則不是新,而我們的記者恰恰不善于求異而慣于認同。這種思維方式的存在是辦好報紙的嚴重障礙。為了迎接西部大開發(fā),從現(xiàn)在起,報社要求把求新當作一項重要的奮斗目標,每天的報紙都要給讀者以新鮮感覺。無論是編輯還是記者都要培養(yǎng)新的思維,要用新的視角去觀察、認識西部大開發(fā)的“新”,去觀察、認識,表現(xiàn)時代的“新”,要用新的形式去表現(xiàn)這些“新”。“新”是報紙的生命,沒有新意的稿件會切斷報紙和讀者的聯(lián)系,會使報紙失去生存的價值。為此,我們決定,長期不能改變自身狀況的編輯、記者要逐步淘汰。另外,觀察事物的表象、事物的運行過程多表現(xiàn)為“同”,只有進入事物的義理層次,進入人的心理層次,才能發(fā)現(xiàn)千差萬別的“異”,所以我們要求記者不要滿足于事物的表象層次,要鉆研事物的義理。對于新聞中的人,則要進入心理層次,特別是社會新聞一定要透過采訪對象的行為表現(xiàn)人物的心理。
西部大開發(fā)是新形勢下的新事業(yè),亟待我們用新思維新眼光去捕捉新聞,用新形式新手法去努力表現(xiàn)。探求西部大開發(fā)之“新”,展現(xiàn)西部大開發(fā)之“新”,就是我們報人的責(z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