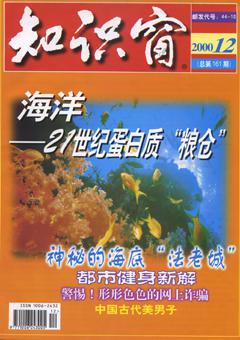我所了解的陳寅恪先生
周一良
我認識、了解的陳寅恪先生,是否可以用這樣12個字來概括:儒生思想、詩人氣質、史家學術。
先談儒生思想。我覺得陳先生的文化交流是儒家思想,聽說當初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有三位名教授,一位是馮友蘭先生,一位是湯用彤先生,一位是陳寅恪先生,當時就有儒、釋、道三種說法。馮先生是大胡子,人稱“馮老道”,代表道教;湯先生是研究佛學的,是代表釋教的;陳先生就是儒生,代表儒教,故時人用儒、釋、道三字來代表這三位教授。當時這固然是開玩笑,但現在看起來也有一些道理。陳先生代表儒家,他的主體思想是儒家的。
怎么理解這句話呢?我想還是用陳先生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思想是介于湘鄉南皮之間。湘鄉指曾國藩,曾國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曾國藩的思想核心及他一一生的行為、言論的表現都可以說是典型的儒家。而陳先生說他的思想介于湘鄉南皮之間,可見他對曾國藩的敬仰。南皮指張之洞,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也是陳先生欽佩之人。當然,介于湘鄉南皮之間的說法是比較早期的說法,是30年代的說法,到了60年代,陳先生晚年是否依然如此呢?我覺得是沒有根本的改變的。陳寅恪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導地位的,這一點,我還想通過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來加以說明。他在給王觀堂的挽詩中已經講了關于儒家傳統文化。有一位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講過這么一件小事:王靜安先生遺體入殮時,清華一些老師與學生都去了,對王先生遺體三鞠躬以敬禮。不久,陳寅恪先生來了,他穿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叩頭,并是三叩頭,一些學生見陳先生行跪拜禮,也跟著行跪拜禮。實際情況我不大知道,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陳先生在王靜安先生入殮時行的是跪拜禮,這個就是封建文化、封建傳統的很典型的一個表現。
還有一個例子,我也聽別人說的。說陳先生在國學研究院時,有一些陳先生的學生到上海陳先生家中去謁見散原老人,散原老人與這幫學生談話,散原老人坐著,這幫學生也坐著,而陳先生是站在旁邊的,并堅持到談話完畢。這說明什么?這是過去時代很嚴格的舊式家庭的禮教,指導這種禮教行為的是什么思想呢?當然是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
接著前面“湘鄉南皮之間”說,南皮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要是講船堅炮利,指西方的聲光電化,而陳先生對西方之學的認識,比張之洞要高得多。關于此點,我們從陳先生留學時期與吳宓的談話(據《吳宓日記》)中看出,如陳先生對照中、西方哲學,認為西方哲學比東方哲學高明,更有思辨性,所以,陳先生對西方的文史之學有很深刻的認識。陳先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方面表現在學術自由。陳先生送北大學生的詩,是這樣說的“天賦迂儒自圣狂,讀書不肯為人忙”,說天生我這么一位狷介的儒生,我念書不是為別人,是為了我自己,我根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研究。然后又對北大學生講,“平生所學寧堪贈”,我平生所學沒有什么值得告訴你們的,最后一句,“獨此區區是秘方”,意思是只有這區區的一點是我的秘方。秘方是什么呢?就是“讀書不肯為人忙”,就是強調讀書一定要獨立,獨立思考,并有獨立之思想,不為別人希望的某種實用主義左右而讀書。對學術自由,陳先生是一直堅持下來的,直到解放后寫《柳如是別傳》,我覺得這一點是陳先生受西方學術思想影響的一個方面。
還有一點,就是蔡鴻生教授《“頌紅妝”頌》中談到的“頌紅妝”。陳先生所謂的“頌紅妝”,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西方男女平等、民主自由之思想。當然,他的思想比西方民主自由還更深一步。對紅妝的理解,對紅妝的同情,對紅妝的歌頌,他的思想基礎,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如果沒有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完全是儒家的東西,如7L孟之道的“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那就是另外一種想法。所以說,陳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三綱六紀是他信奉的東西,同時,也有西學為用,他的“西學為用”表現在學術自由,表現在頌紅妝等許多方面。這看來似乎很矛盾,實際上恐怕并不矛盾。因為人的思想是比較復雜的,特別是在轉變時期,有這方面的東西,也有那方面的東西,可以理解。
第二講陳先生的詩人氣質。陳先生詩人氣質是十分濃厚的。他作詩有各方面的因素與條件。首先是他的家世,父親散原老人是一位著名詩人,成就很突出。據說宣統年間(1909~1911年),有一個叫陳衍的福建詩人立了一個“詩人榜”,榜上沒有第一名,實際上第二名就是第一名,這個第二名就是漢奸鄭孝胥,第三名就是散原老人。可見當時公認散原老人的詩是很好的。陳先生的母親俞夫人,也有詩集傳世。他的舅舅俞明震,也是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有名的詩人。所以,陳先生的家世是一個詩人的家世,他從小受到作詩的訓練.受到了詩的熏陶,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我覺得陳先生的詩人氣質還表現為多愁善感。這是老話了,詩人都多愁善感,陳先生也是這樣的。善感,陳先生是一個有豐富感情的人,特別是《柳如是別傳》中表現出感情非常豐富、非常深厚,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愁呢,李堅先生講陳先生詩中體現的悲觀主義,講得十分細致。陳先生確實有悲觀主義,多愁的,這與他后半生的經歷有關:抗戰時期避難來到南方,已經流離顛沛;后來香港淪陷,又流離顛沛。這幾件事不能等量齊觀,但都使他產生一種流離顛沛的感覺,因而出現害怕戰爭,躲避戰爭的想法。加上陳先生晚年眼病,經過三十年逐漸加深并最終失明,復又腿部受傷,臥床不起,這切身的折磨使他感到悲觀,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陳先生的詩人氣質,我想還可以舉這樣一個例子。我的老師洪畏蓮先生有一個口述自傳,有英文本,聽說香港也出了中文本。在自傳中,他講到,他在20年代到哈佛去,夏天,在哈佛校園中看見一個中國學生口誦中國詩歌,來回朗誦。這位學生的襯衣整個都露在褲子外邊。大家都知道,從前西方穿衣服,襯衣后部因很長而應塞入褲子里面,露在外面是一種不禮貌、非常可笑的行為。洪先生看到這人有些奇怪,就問別人此人是誰,別人告訴他,這是哈佛大學很有名的一個學生,叫陳寅恪。從此記錄可見陳先生是落拓不羈,有詩人氣質的。
由詩人氣質我聯想到陳先生很喜歡對聯。他常以對聯這一形式來開玩笑。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聚會,他作了一副對聯,上聯是“南海圣人再傳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為)是梁啟超的老師,而這幫學生為梁啟超的學生,所以這幫學生也就成為了南海圣人的再傳弟子,下聯是“大清天子同學門人”,意思是王國維先生是南書房行走,在某種意義上是宣統的師傅,你們呢,就是宣統的師傅的弟子,與大清天子是同學啦!可見,陳寅恪先生對對聯很感興趣,而且有一揮而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陳先生出過中文題,一題目為“孫行者”,據說考試時,有學生對為“胡適之”,這個學生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謨先生。我問過周祖謨先生,他說確實如此,不過后來與胡適先生見面時,不敢把這件事告訴他。除此事外,那一年研究生的中文考試卷中也有一個對聯:“墨西哥”,據說也沒有人對出來,這個是聽北大西語系英語教授趙蘿蕤先生說的。
第三點,我想談的就是陳先生的史家學術。我的體會是,陳先生的學術是很廣泛的,博大精深,但歸根到底是史家,即陳先生的研究重點在歷史。雖然陳先生精通多種語言,研究佛經,又受德國蘭克學派的影響,對中國古典文獻也非常熟悉。總而言之,他具備了各方面的條件來研究歷史。陳先生的歷史之學歸根到底得益于什么?陳先生腦子非常靈敏、敏銳,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可以看到,怎么樣分析陳先生研究歷史看得這樣透徹、分析得這樣精深呢?我覺得與辯證法有關系。就是說,陳先生的思想含有辯證因素,即對立統一思想、有矛盾有斗爭的思想、事物之間有普遍聯系的思想。在許多混混沌沌之間,他能很快找出重點,能因小見大,而這些思想、方法與辯證法有關。比如說,他講唐朝的政治,把中央的政治與少數民族的情況聯系起來,把看起來沒有關系的東西聯在一起,陳先生的論文很多屬于這一類。我們從中看不到的關系、因果和聯系,陳先生卻能發現。又如,講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陳先生從這篇文學作品聯想到魏晉時期堡塢的情況。還有,講唐朝制度的來源,陳先生能找出眾多來源中的重點,加以分析。
(摘自《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