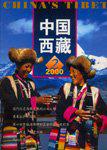陽光下的春堆
庭西
春堆村在林周縣的西北面,離縣城大約40公里,由于是普通的土路山道,行車差不多要兩個小時。1998年和1999年兩個夏天,為了藏語言的研究,我曾經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其他兩位研究人員來這里小住。羅絨占堆和旦增是藏研中心負責扶貧課題研究組的成員,近幾年一直在西藏農牧區進行調查,而春堆正是他們多年調查的點之一。
林周縣城印象
我們一行到達林周縣已是傍晚,走在街上,覺得林周縣和其他縣城幾乎沒有什么差別,人少,街道也不多。一條街南北走向,商店不多,街的盡頭是農田;另一條街東西走向,是全縣的繁華去處,街的兩邊商店、飯館很多,商業氣氛比較濃。我們每經過一家店鋪,店主都會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從口音聽得出來,他們大都是西北回族商人。 夏天,西藏的天黑得很晚,落日的余輝染紅了整條街道。幾個牧童趕著牧歸的牛群、羊群朝我們走來,剎那間塵土飛揚起來。這個場景讓我想起了兒時的生活,也是落日、牧童、塵土、牛羊,構成了我在拉薩和北京都見不到的風景。 很快,我們就走到了街區的盡頭,覺得沒有什么好玩的。街上有好幾家錄相廳,但是放的都是武打片,我們沒有興趣。我是搞語言調查的,所以每到一家錄相廳或是歌舞廳,都要進去聽聽他們使用的是什么語言,事實上,兩種語言都有。
虎頭山水庫豐采依舊
春堆村遠在林周縣的西北部,乘車前往,沿路的風景讓我興奮不已。陪同我們前往的是一位60多歲的老書記,他已經在林周工作了20多年,對林周縣和春堆村都了如指掌。 一路上,老人談得最多的話題是兩個,一個是我們路上經過的虎頭山水庫,一個是就是我們要去的春堆村。 虎頭山水庫離縣城約20多公里,去春堆的公路就在水庫大壩之下經過。這座水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修建的,因大壩北面的山峰形似老虎的頭,因此叫作虎頭山水庫,當時還很有點名氣。老人領我們登上10米高的水庫大壩。大壩長約百米,南北走向,一頭與虎頭山相連,另一頭伸延到南面的山上。水庫的水面不大,水源來自上游的河水,大壩實際上是將西面流來的河水攔腰切斷修筑而成。 說起水庫,老人的話就多了。林周縣是西藏最著名的農墾基地,六七十年代很有名的澎波農場就在這附近。當時要發展規模農業,首先需要水,需要水就要建水庫,虎明而又濃厚的色感,將遠遠近近一切,編織成一塊巨大的地毯,上面,幾點黃色,幾點墨色,幾點藍色,幾株柳樹,幾行農舍,幾面風幡。我在西藏還從來沒有看到過這么整齊的田塊列隊組合,這么多色彩搭配顯現,我真有點不敢相信這是人間創造出來的自然。 在春堆鄉政府院子的二樓,我們見到了帶領群眾描繪這塊美麗土地的幾位基層領導,他們對我們的感受和激動表現出一種平靜,在我們的一再請求下。他們才給我們提起下面幾組數字,而這些數字正是春堆鄉群眾擺脫貧困走向富裕的歷程: 1994年以來,全鄉連年豐收,糧油產量連續多年保持在660萬斤到670萬斤左右; 1996年達684萬斤,同年經鄉村兩級嚴格驗收達標,提前完成全鄉脫貧任務。當年有不少農民蓋起了兩層樓的新房。 在他們的會議室里,我們看到了好幾面錦旗,下面就是這幾面錦旗的內容: 1997年春堆鄉以開發資源為突破口,帶領全鄉農牧民脫貧奔小康,做出了突出成績,被自治區評為“農牧區基層組織建設先進鄉(鎮)黨委”; 1997年春堆鄉率領全鄉農牧民在脫貧工作上做出了突出成績,被拉薩市評為“率先脫貧光榮”獎; 1998年由于春堆鄉社會經濟建設和基層組織建設中繼續做出較大貢獻,再次被拉薩市評為“先進鄉黨委”;
金色的春堆新樓
從鄉政府繼續向西,不到10分鐘就是春堆村了。 我們進村時,已是下午7點多鐘,但太陽仍然高懸在西邊的山頂上,只是色彩更紅,更燦爛了。陽光中,春堆村的一座座小樓沐浴著金光,使我覺得仿佛在夢境中,因為我一時難以相信,這些金光閃閃的小樓,會是村民的新居。 我們的房東,是一位叫央金的50來歲的阿媽,仿佛知道我們要來似的早已等在門口,我把行李匆匆搬進屋里,就爬上了房東家的屋頂,因為我想把這景色拍攝下來。 房東的房子在村子的最南頭,站在屋頂舉目向西北一看,整個村莊盡收眼底。春堆村的農舍都集中在村子的西北面,從東往西,一棟一棟的兩層樓錯落有致地分布在約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樓房大都南向,樓前有一個大院,大院兩側建有養牲畜和堆放柴禾雜物的平房。主樓中一樓作為庫房,二樓住人。我在拉薩墨竹工卡縣的貢勒村曾經見過民主改革前的一家貴族的兩層樓,與之相比,它遠不如春堆村樓房的氣派。春堆的樓房除了有寬敞的院落,還有寬大明亮的玻璃窗,油漆或者木刻的大門,從院墻到門窗都點綴著傳統或現代的裝飾。而在這一座座小樓里擺設和展開的生活,那更是過去的小貴族所不能相比的了。 記得我在房東的樓頂上足足站了1個多小時,同行的旦增叫我下去吃飯,我才離開樓頂。“搞田野調查就是吃苦”,這是搞社會學同行的一句老話。因此我對晚飯不報很大的希望,心想,只要有熱茶喝,吃點糌粑就可以了。 當我在廚房的卡墊上坐下來,在太陽能燈的光線下,看著餐桌上的幾樣炒菜,高壓鍋做出的米飯,一瓶孔府家酒,一大壺酥油茶,一大桶青稞酒時,我才感到春堆農民的日子真正是從里到外、從住到吃都發生了想象不到的變化。這時,羅絨占堆和旦增他們已和房東噶瑪阿爸和央金阿媽以及村長等人談了許久了。 羅絨占堆這幾年一直搞扶貧研究,看著聽著老百姓有這么好的日子過,作為一個藏族知識分子,他也是一臉的燦爛。我剛端起茶,他就對我說:“你知道嗎,房東每周都要到城里去買蔬菜,你別小看米飯,還是尼泊爾進口的米呢。” 那天我很高興,盡管平時不喝一口白酒,但也陪房東干了好幾杯。飯桌上,村長告訴我們,全村有70%以上的人修了新樓,今年底又有好幾戶要動工蓋新房。阿媽一再告訴我們,她們家的木料和土坯已準備得差不多了,明年就準備動工。我問村長,大概什么時候全村能住上新樓,村長反問我:“這么好的形勢,你說會要很長時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