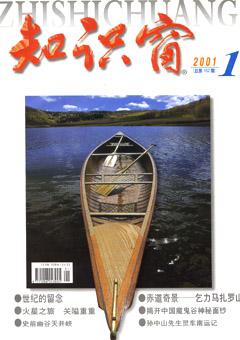火星之旅 關隘重重
張唯誠/編譯
2003年的某一天,一個全身乳白,如大鳥一般的飛行物突然出現在火星的大氣層中。它翼長10米,重150公斤,機尾上飛旋的螺旋漿,使它在離火星地表2000公里的高空上能自如地展翅翱翔。
這美麗的不速之客名為“基蒂霍克”號,來自地球,它上面搭載了20公斤重的觀測儀器,使命是對火星地表進行詳細的觀測。
“基蒂霍克”號無人飛行試驗只是人類登陸火星計劃的一個小插曲。提出這項設想的是美國航空航天局的火箭工程專家拉里·雷姆基博士。研究表明,火星上的大氣壓和地球上空28000千米高空的大氣壓相當。為了獲取準確的數據,科學家已經在地球上空25000千米的高空上,對這種以太陽能為動力的無人駕駛螺旋漿式飛機進行了幾次成功的試飛。
“基蒂霍克”號的翅膀是可以折疊的,它將被置于一個密封囊中由太空飛行器拋入火星大氣層。拉里·霍姆基博士認為,根據目前人類的技術,“基蒂霍克”號飛行計劃是完全可行的。
超越“阿波羅”
然而,“基蒂霍克”號飛行即使成功,也只是一次富有想像力的探測行動。要把人類送上火星卻遠非如此簡單,它比人類登陸月球的“阿波羅”計劃要困難得多。
登陸火星的航天器根本不能像“阿波羅”飛船那樣直接從地球上飛抵目的地,它非常巨大。人們必須首先將重達400—500噸的組件分成幾次送上位于地球軌道上的宇宙太空站上,在那里組裝后才能踏上飛抵火星的漫長旅程。這次飛行將搭載6名宇航員,飛行時間長達6~10個月。宇航員到達火星后,要在這顆荒涼的星球上至少滯留一年以上。他們將身著宇航服幾百次地走出登陸倉,從事各種科學考察活動。
火星之窗
和月球相比,火星不僅非常遙遠,而且適合飛行的最佳時間十分難得。當飛船利用地球公轉速度轉入飛向火星的“遷移軌道”時,火星必須恰巧出現在正前方,這樣的機會大約每26個月才有一次。如果抓住了這個機會,火星之旅可能只需10個月,科學家將這段珍貴的最佳時間稱為飛向火星的“窗口”,然而遺憾的是,這扇窗口每次僅僅開啟幾周時間。
返回地球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當宇航員到達火星時,返回地球的窗口已經關閉了幾個月,他們必須在火星上等待10~20個月,下一次窗口才會開啟。
因此,即使選擇最經濟的路線,從出發到返回也需要至少3年時間。有些人認為,如果燃料充足,或選擇橫穿金星軌道的線路,時間會進一步縮短,但那樣來回也要18個月,出發的良機少和旅行的時間長增加了登陸火星的難度。
火星生活
長期滯留在宇宙空間,太空人容易產生一種稱為“季節沖擊”的心理不適,表現為煩躁、焦慮、忐忑不安。專家們認為,從火星上返回的宇航員產生這種不適的可能性很大。
火星的環境可能使宇航員的感覺發生紊亂。火星的一天比地球上的一天長38分鐘,滯留火星一段時間后,對時間的感覺將逐漸變得和地球上不同。火星上也有季節,它的公轉軌道是地球的兩倍,因此季節轉換要比地球慢一倍,而且它上面季節的變化要比地球嚴酷得多。
對宇航員沖擊最大的是在火星上和地球的通訊非常耗時,電波在地球和火星之間往返一次至少需要8分鐘,有時甚至需要30分鐘,因此,一個小時只能交談幾句話。
為了克服這些障礙,科學家需要進行各種實驗和研究,還要對宇航員進行多種訓練。
燃料問題
燃料是火星之旅的一個重大課題。科學家認為,資源的就地籌措是火星探測的重要特征。比如,用火星上的氫和大氣合成甲烷,從而生產出人們所需的燃料。就地生產的燃料不僅可用于航天器的返回,也可用于火星上的遷移。如果這種方法得以實現,飛向火星的航天器上的燃料重量可望減少一半。
另外,原子能也被一些科學家所推崇。1960年,美國已經設計出使用鈾235的原子能火箭,這種火箭靠噴出超高溫氫氣獲得推動力,其燃料效率是利用化學反應獲取動力的2倍。因此,這種火箭可使攜帶燃料減少一半,這在長途宇宙飛行中十分誘人。不過原子能火箭需要高度的可靠性作保證,在技術上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沙塵風暴
目前,對于火星地表的環境,人們并不太清楚,特別是火星上的灰塵可能給科學家帶來很大的麻煩。在火星地表,細小的沙粒漫天飛舞,其速度最快時可達每秒100米,它們可能導致強烈的靜電,但究竟強到什么程度依然不得而知。沙塵風暴可能使沙粒灌滿容器,或沾在航天器的窗子和太陽能電池板上,也可能引起機器故障甚至侵入人體內。它們的許多特性,比如是酸性還是堿性,能否和氧反應,是否易著火,是否有毒等都不清楚。為此,近幾年,科學家將把一架火星環境適宜性評價儀(MECH)發射到火星表面,它的數據將為人類設計火星考察設備提供科學依據。
火星之旅,關隘重重,科學家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飛行中宇航員的健康怎樣保證;在從未有過的太空長途旅行中,乘員怎樣搭配;從火星上取回的樣品和宇航員身上可能帶有未知的細菌,怎樣進行檢疫才能保證地球不受外太空細菌的污染等等。盡管如此,人類登陸火星的號角仍然即將吹響,地球人百折不撓的精神和日新月異的當代科技肯定會使這個偉大的夢想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