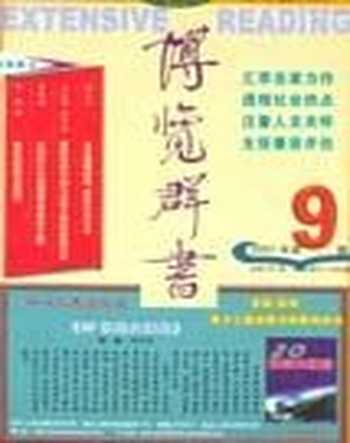點評王朔的點評
劉東超
世紀之交,王朔在玩文學、玩電影、玩電視之外又新添了一個行當——點評文化人物和文化現象。這是他在《無知者無畏》(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1月)和《美人贈我蒙汗藥》(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8月)兩本小書及一些報刊文章中所作的工作。在這里,王朔以自己的方式隨興指點評議了現當代中國文化中的一些人和事,其中包含少量的肯定和贊賞,大多數內容還是貶低或諷刺,甚至還有點罵罵咧咧。而無論褒貶,他還是用自己特有的“痞子”式語言表達出來。如王朔的其它行當產生的影響一樣,他的點評工作也引起了大量的議論和反駁,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反響。這和他善于選擇大眾焦點有關,同時也和他點評內容的正確和荒謬交雜有關。因此,點評一下王朔的點評就是一個有些必要也有些趣味的事。
坦率地說,王朔的點評中包含許多深刻、獨到的見解。比如,他說自己小說中流露出的是“極其陳腐極其庸俗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無知者無畏》49頁)。這比僅僅把王朔看作是前衛、后現代(在他身上當然也有這些成分)更要深刻、本質一些。王朔小說所表現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不過是:一切都是騙人的、沒用的,只有感官滿足是實在的,所以感官是衡量一切價值的尺度。這的確算不了什么新鮮思想,也不過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山大王哲學在今天的體現,也不過是人類粗鄙的低級本能的表達。王朔能看到這點,說明他對自己有著清晰的把握。再比如,王朔對于金庸小說的評價也有一些點到痛處。他談到金庸小說的情節時說:“永遠是見面就打架,一句話能說清楚的偏不說清楚,而且誰也干不掉誰,一到要出人命的時候,就從天上掉下一個擋橫兒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亂的深仇大恨,整個故事情節就靠這個推動著。”(《無知者無畏》74頁)談到金庸小說中的人物時他又說:“那么狹隘、粗野,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沒有容量,只能認知眼前的一丁點兒人和事,所有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無知者無畏》77頁)我們說,如果濾去王朔這些議論中的刻薄、夸張和簡單之處,可以看出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金庸小說情節(例如《天龍八部》中的喬峰尋仇)和人物(例如楊過、黃藥師等)的某些實際情況的。對此,金庸本人也是承認的。而王朔之所以得出這些看法,應該說和他長期寫作實踐及由此實踐悟到的小說好壞標準有關。也正是因此,他觀察到的金庸小說的一些缺點就往往是一般讀者看不到的或無所謂的。從以上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王朔基于個人經驗的文化點評絕非僅能嘩眾取寵,而是包含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內容,有其合理和可取之處。類似的內容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如他對大眾文化的警惕、對語言(尤其北京話)的認識、對一些青年批評家的批評、對性描寫的設想、對無恥的譴責、對老舍和鐵凝的評價等,都有一些較深的見解。很顯然,王朔這些認識的深刻和獨到之處和他經歷較為豐富、接觸面較為開闊有關,同時也和他個人悟解能力較強有關。
與王朔點評中值得汲取甚至值得欽佩之處同樣多的是他的錯誤和偏激之處,這是更值得我們進一步點評的內容。并且,我們有必要對這些錯誤和偏激產生的影響保持清醒的警惕。比如,王朔和老俠對錢鐘書的貶低就相當偏激。王朔認為錢先生拒絕媒體采訪和國外名牌大學的邀請“像是一種成心”(《美人贈我蒙汗藥》94頁),意為這是錢先生故作的一種姿態,是邀名的一種策略;王朔還認為,錢先生及其夫人楊絳(和贊美他們的人)似乎從不提他們“文革”前不錯的境遇,只講他們的“文革”厄運,“感覺上,他們四九年以后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美人贈我蒙汗藥》96頁)他的意思是錢、楊在“揚長避短”地“塑造”自己“淡泊名利”的公眾形象。我們說,根據這兩本小書的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話是王朔在根據自己的心理和成名經驗來猜度錢先生,這只能得出甚低的評價和歪曲的認識。我們在此無意將錢先生捧為“圣賢”,這不符合錢先生的實際。但像王朔那樣將錢先生想象為極工心計的“演員”,恐怕更遠離錢先生的實際。我們可以根據一些基本的事實對錢先生的人格做出一個原則性的判斷:作為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學術中去的嗜學老人,錢先生不對紛繁復雜的外部世界和媒體不感興趣是正常的,合乎其心理實際和感情真實。這倒未必是清高,而是這個年齡、這個知識層次的人實在沒有這方面的需要和興趣了。從此可知,錢先生的人格未必多么崇高,但至少是一個有操守、低物欲、心神有所棲止的人。這樣的人雖然并不太多,但也絕非少到鳳毛麟角的地步,在現實生活中還是時有所見。因此,對于錢先生的人格和處世方式一般人還是可以理解的,也并不認為高不可攀。王朔(以及那個老俠)對錢先生人格的懷疑和輕薄是缺乏起碼的同情理解所致,也是毫無道理的求全責備。對于錢先生的文學作品,王朔也進行了諷刺和貶低。他說,錢先生的《圍城》“是在玩花活兒,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實里面沒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并不想嚴肅地說點什么。”(《美人贈我蒙汗藥》95頁)我們也并不是說《圍城》中有多少微言大義,但這本書對婚姻和感情的理解還是相當準確的,符合現當代人的心理真實。恐怕多數讀者都這樣認為,從今天人們經常將婚姻比喻為“圍城”可以曲折地反映出人們對這部書的某些認同和接受。王朔當然也不會讀不出這層意思來,問題在于,他以相當高的思想標準來要求《圍城》,他的所謂“什么”是極難達到的東西,這實際上是在苛求于錢先生(而他對于魯迅、老舍、金庸等也有各式各樣的苛求)。恐怕可以說,按照王朔的讀法,不僅《圍城》,就算再好的文學作品,里面也沒有什么。因此,出問題的是王朔的閱讀標準,而不是錢先生的作品。
王朔對錢先生的非難和攻擊當然有其較為復雜的原因,其中一個最值得分析的思想根源是他對知識分子整體的看法。在這兩本書的許多地方,王朔對知識分子整體進行了過分的挑釁和褻瀆,按他自己的說法是“跟知識分子過不去”。這一點在他談到自己的知識分子化時表現得非常清楚。他說:“我為自己從思路到文風的知識分子化感到惡心。我曾經想靠講幾句粗話和挺身叫罵阻止自己的墮落,可笑的是我在大罵知識分子時發現自己只有站在知識分子立場上才罵的出口罵的帶勁兒。這真沒意思。我想不出好的比喻。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東西你要指責它就會變成它像知識分子那么神奇。”(《無知者無畏》109頁)說句實話,我一直不理解為什么知識分子能令王朔這樣厭惡,我在他的書中和文章中一直找不到有力的和充分的理由。我們只能就他一些表述較為集中的理由進行一些分析,下面看一條“基于歷史”的理由。他說:“以我之偏見,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于偽善,而偽善風氣的養成根子在知識分子。中國歷代統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國人。他們無不利用知識分子馭民治國,剛巧中國的和尚不理俗務,世道人心,精神關懷又皆賴知識分子議論裁決,這就造成知識分子權大無邊身兼二職:既是神甫又是官員。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信仰與利益,超凡成圣和過日子往上爬,再偉大的知識分子也難以自處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偽善便成了普遍的選擇。”(《無知者無畏》141-142頁)這段話略加分析就會發現這里面存在一些嚴重的邏輯問題和史實問題。從邏輯層面看,這里的矛盾極為明顯,不可能同時存在著統治者和知識分子這兩個“權大無邊”者,否則,二者誰管誰呢?從史實層面上看,自古及今的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擁有過“無邊”的權力,恐怕這是人人盡知的常識。這里只有一個表述上的例外,那就是將歷代統治者也劃歸進知識分子的范疇,而這顯然不是王朔的意思,也不符合這一范疇的一般用法。再如,所有知識分子難道真的不能在“超凡成圣和過日子往上爬”中“割舍其一”嗎?從王朔貶低知識分子的意思來看,至少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可以割舍“超凡成圣”,而一心一意“過日子往上爬”,這在古今中外難道不存在大量事例嗎?從另一方面看,即使按王朔這兩本小書中的說法,不是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如陳寅恪、顧準、林昭等)割舍了“過日子往上爬”,而將全部精力甚至生命寄托到自己的精神追求或信仰上嗎?所以,不管是否偉大,知識分子在“超凡成圣和過日子往上爬”中“割舍其一”并非太難。這里,我們進行的兩點分析主要還不是想證明王朔如何無理和錯誤,而是想說明他自某些“批評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那里“道聽途說”來的這些說法經不起簡單的邏輯分析和史實分析。
進一步,我們可以直接對王朔這段話中提出的關鍵問題做一些討論。王朔在此提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理解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及中國社會文化中的一些弊端(比如王朔最恨的“偽善”)是否來自知識分子。對于前一個問題,王朔將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歸結為精神領導和社會管理兩個方面,應該承認,這是基本準確的。可是,他卻對此持批評態度,因為他認為這讓知識分子擁有“絕對的權力”并“導致絕對的腐敗”。我們說,知識分子承擔這兩種社會功能是社會長期博弈的結果,是符合必然規律的歷史選擇。而歷史之所以作出這種選擇,顯然在于它(相對來說)可以推動歷史的進步、增加歷史主體——人們的福祉。在中國歷史上并不乏“秀才遇到兵”的先例,比如“文革”中將“臭老九”打倒,結果決不是僅僅造成一些流傳廣泛的關于“無知”的笑話,在社會歷史的深層則是我們民族精神機體受到傷害,科技水平、經濟發展深受影響。這里的道理極為簡單,知識、文化及其載體(知識分子)總比無知、野蠻及其載體更能促進人類的幸福、文明的進步。當然,我們肯定知識分子承擔社會功能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性,并不意味著其中不會產生消極的東西或說負面價值,王朔認為中國社會的偽善便是從中產生。這即是我們要分析的后一個問題。我們說,偽善及人們經常提到的許多負面品質并不是中國社會所獨有。從根本上看,它們源自人類的自私本性,是這一本性在非道德層面的人格積淀,這是為各個民族、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人所共有的。在社會現實生活中也的確存在各個階層的偽善,偽善絕非知識分子的“專利”。但是,偽善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表現得可能要多一些,知識分子掌握的偽善“花招”可能要復雜一些。這當然和他們的職業訓練及文化背景有關。受過其他職業訓練的人同樣可能較易沾染另外一些惡劣品質,比如屠夫之于兇狠、商人之于奸詐。
王朔之所以得出這樣偏頗、武斷的結論,和他缺乏一些基本知識有關,但更為重要的還和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厭惡知識尤其是概念化的知識(《無知者無畏》107-108頁)有關。實際上,他對知識分子的反對只是出于某種特定的心理情結和功利需求。和他有沒有充足的反對理由無關。如果我們從正面來理解,王朔的偏激心理可能來自他對我們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殘酷的痛恨、對現存諸多弊端的仇視(《美人贈我蒙汗藥》160-162頁)。可是,他將歷史上的殘酷和現實中的弊端歸罪于知識分子,毫無疑問是看錯了靶子、打錯了板子。也許王朔心中并非不清楚其中是非,只不過出于某功利目的故意如此說而已。但不管怎么說,在王朔近期文化點評中的錯誤和偏激是相當明顯的。
有些復雜的是,王朔點評中深刻、獨到的見解和錯誤、偏激的結論往往混雜在一起,有時他是以偏激的語言表達某種獨到的見解,有時他的錯誤議論中還暗含某些可取的成分。實際上,對錯混雜是他思想的宿命。因此,我們對王朔點評中的認識價值應該透過偏激或錯誤的帷幕來看,而對于他思想中的荒謬和偏頗也應該抱以同情和理解的態度。這些認識價值倒未必意味著王朔有何思想建樹,而是在于他的批判開拓了一些思想空間。當然,這里的思想空間主要針對的是對社會大眾的思想活動。
另外,王朔點評中還包含更值得解讀的文化意義。他(以及老俠)縱橫捭闔式的點評中雖然包含了對大眾文化的嚴厲批評,但其實質上仍然是基于大眾文化市場,是為滿足大眾需要而生產的“文化快餐”。對此,王朔本人和出版者及讀者都是十分清楚的。王朔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中最為著名的大眾品牌,成為文化市場上的一棵搖錢樹。他的文化點評暗示著市場對于思想的進攻和浸染,暗示著思想經過包裝后可以走上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