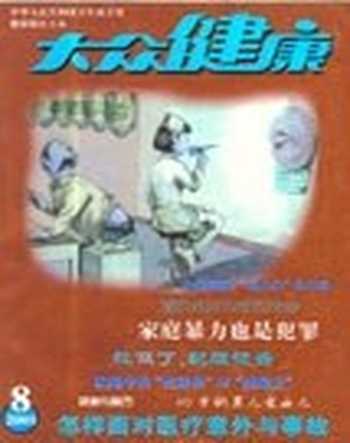怎樣面對醫療意外與事故

醫療意外:現階段醫學的無奈
9歲的曉洋終日呆傻地坐在家中,失控的口水流淌在衣襟上……面對病前兒子活潑可愛的照片,他的父母很難接受這個現實:兒子因天生睪丸長在腹腔,做了分步引睪手術,豈料在第二次手術牽拉精索時發生麻醉意外。手術臺上的曉洋呼吸心跳驟停,雖經搶救保住生命,卻因大腦缺氧造成腦癱。
事后,麻醉學界權威們認定這屬麻醉意外,但患者家屬認為這屬于醫療事故。這個醫患糾紛一拖數載,給雙方都帶來沉重壓力。它使我們不能不認真思索如何面對醫療意外與醫療事故。
主持人:目前,對“醫療意外”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一般人往往將病人在醫療過程中出現的嚴重不良后果統稱為醫療意外,如死亡、殘疾和嚴重功能障礙。而醫學界則根據現實的醫學技術水平,將這些不良后果按能否避免、有無過失,細分為醫療意外、難避免的并發癥和事故。下面請浙江大學醫學院丁涵章教授解釋這三者的區別——
丁涵章:醫療意外,是指醫療護理過程中由于無法抗拒的原因,出現難以預料、難以防范的不良后果。如利多卡因硬膜外麻醉,有時會出現心跳驟停的不良反應,雖及時搶救,死亡率仍較高,有的會由于嚴重腦缺氧而成植物人。
難防范的并發癥,是指醫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雖能預料其出現的可能性,但防范的難度大。如腦瘤切除手術很易引起肢體癱瘓;某些化膿性疾病手術后很易引起穿孔;腹腔鏡下腹部手術易并發出血等。對于這些并發癥,醫生事先會告知病人家屬,并做好防范準備。但醫護人員盡力了,未必全能防范,這受現有醫療技術條件限制。
醫療事故是指因醫護人員的過失給患者造成的嚴重不良后果。也就是醫護人員該做到而未做到、能做好而未做好,而引起嚴重損害的。包括對醫療意外和并發癥的處理不利,未予重視,加重了不良后果,也依具體情節負一定責任。
由國務院批準頒布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在診療護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屬于醫療事故:(一)雖有診療護理錯誤,但未造成病員死亡、殘疾、功能障礙的;(二)由于病情或病員體質特殊而發生難以預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三)發生難以避免的并發癥的;(四)以病員及其家屬不配合診治為主要原因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的。”
主持人:隨著醫學的發展、法制的完善,隨著公眾科學文化素質和法律意識的提高,人們對該《辦法》規定的基本精神將有更透徹的理解,新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正在修訂中,我們相信,實事求是,懲惡揚善,罰所當罰,保護應當保護的,永遠是法治的根本宗旨。
增強共御醫療風險的意識
主持人:有病找醫生救治,自古如此。我們在電視里也看到,古代的皇親國戚有病也是急呼太醫。但醫學不是萬能的。盡管以前很多不能治的病,現在能治了,但未攻克的疑難問題還有很多。面對患方的過高期望,有必要強調醫療過程的高風險:祛病不像洗澡那么簡單!醫藥是把雙刃劍。醫護人員只能因勢利導,促進生命過程向健康、康復方向發展,但事與愿違的事是難免的。對此,懂醫的人往往更易理解。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趙友文教授對醫療意外就有深刻體驗。
趙友文:“前年,和我相濡以沫幾十年的老伴住院做溶血栓治療,就在療程快結束時,忽然他腹內的大動脈破裂,搶救無效死亡。當時很多人擔心我承受不了,我卻冷靜地對有關醫務人員說:“我曾經在這個醫院工作過,醫護人員的心情我能理解。你們可以對這個病例進行討論分析,吸取經驗教訓,不必告訴我,我也不追究!
“我先后在婦科、外科、精神科做了40多年醫生,醫學領域的未知數太多了,許多醫生都是越干越膽小了。有些患者家屬抱怨醫療意外發生時,說患者是走著進去,躺著出來的。他們不知道治療就是對人體這個極其復雜精密的系統進行干預,有些是無創性的,有些是有創傷性的;有些副作用小,有些副作用大,尤其是個體差異和各組織器官的承受能力千變萬化,現在的醫療技術尚不能完全掌握和監控。拿我愛人來說,他雖僅65歲,可患糖尿病多年合并下肢動脈梗阻,醫生先后為他做了手術取栓、搭橋,又發生血栓再注射藥物溶栓時,發生了意外的腹腔大動脈破裂……
“當時,很多人叫我找醫生算賬,我的態度是我既是患者親屬,又是醫生,我知道這種意外是難以避免的:用藥少了,血栓溶不掉;用藥多了,就有出血的危險。而且誰能事先知道他腹內的動脈那么脆弱?如果我們處處苛求醫生,醫生還有積極性嗎?
“在我行醫40多年中,與很多醫生共過事,盡管各人性格不同,有的細致些,有的粗獷些,但在醫療的關鍵時刻,沒有誰馬虎過!生死攸關、性命相托啊!出了醫療意外,親屬悲痛,醫生的心理壓力也不輕呀!”
主持人:對醫療高風險,醫生、患者及家屬都要有心理準備。這就是手術等有風險的診療項目實行前,往往要將種種可能發生的意外和并發癥告知患者及親屬,簽字后執行的原因。
華衛律師事務所主任鄭雪倩律師:家屬在有關治療單上簽字,就意味著了解該項治療的風險,同意承擔可能出現的醫療風險。因此,患者、家屬對治療前簽字一定要重視,認真問清緣由,慎重對待。當然,醫生并不會因為患方簽了字,出現意外就不搶救了,不及時處置了。如果醫護人員在此醫療過程中有過錯仍要承擔責任。
主持人:基于對醫療風險的深刻理解,醫療、司法和醫療事故糾紛爭取協商解決

從醫療訴訟案例學維權
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紛紛建議,探討建立全社會共御醫療風險的機制。新興的保險業陸續推出相關險種。據悉,京城醫務界已有30%從業者加入執業保險,百姓也開始關注或購買以生命和自身為保險標的的各種人身和健康保險。國外成功經驗證明,這是合理化解醫療風險、減少醫患糾紛的可行之路。
主持人:近年來,媒體不時有醫療事故案件報道。如北京某職工醫院手術中將金屬鉗遺忘在患者腹中,給她造成遷延不愈的病痛。烏魯木齊幾家醫院推諉拒收一患兒,延誤治療時機使患兒夭折。這都是嚴重違反診療制度造成的,責任明確,患方理所當然受到賠償。但更多的醫療不幸事件是在復雜的醫療干預和復雜的病情演變中發生的,因此首先應冷靜對待,弄清情況。丁涵章教授對解決醫療糾紛有25年實踐經驗,請聽聽他的意見——
丁涵章:如果不幸醫療事故發生在您身邊,或懷疑是醫療事故,您可首先與醫院協商,口頭或書面提出給予調查解釋的要求。對院方的解釋,涉及技術很專問題難以聽懂時,也可向其他有關醫生請教。
實踐經驗證明,與醫院協商解決此類糾紛是簡便有效的。衛生部《關于<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若干問題的說明》中,將醫患協商處理列入程序,要求“醫療單位要首先進行認真的調查了解,做到事實清楚,責任分明,結論準確,處理得當。”“只有在協商無法進行,發生爭議時,才提請當地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進行鑒定。”
主持人:近年來,隨著維權意識的增強,通過法律訴訟解決醫療事故糾紛的案例在增多。應運而生的北京華衛律師事務所成立一年來,已代理了60多起訴訟,并開設了國內首條醫療糾紛咨詢熱線。下面是他們的見解——
37歲便出現幾縷白發的鄧利強律師說:醫療事故官司涉及復雜的醫學專業內容,勸告患方不要打賭氣官司,必須采取冷靜客觀態度,必須有證據證明存在醫療過失,而且這種過失與不良后果具有直接因果關系。有些醫療不良后果是難避免的醫療意外或并發癥,并非醫務人員過失,狀告醫院最終是不會得到支持的。近年來,已有10位當事人接受鄧律師忠告,撤消了訴訟。
華衛律師所的幾位律師走路似小跑,頻繁的電話鈴聲使他們不時放下手中沉甸甸的代理案卷。復雜的訴訟 案卷有四五本之多。包括有關陳述、票據,有關病歷和醫學資料復印件,醫療事故鑒定書復印件等等,不厭其詳。有著醫學、法學雙學歷的鄧利強代理過100多起醫療事故訴訟,深知其艱難。作為律師,他受當事人委托代理訴訟事宜尚且疲憊不堪,當事人在精力財力上的消耗可想而知。一起醫療事故官司短則一年半截;長則拖延數年。很多人深陷其中,悔不當初調節解決。因此鄧利強說:我最不主張打醫療官司!他常勸導咨詢求助者,能調節解決是最理想的。
一位6歲的男童因醫療事故死亡,其父母提出60萬的高額索賠。經鄧利強苦口婆心地調節,引導雙方換位思考,終于使醫患雙方達成諒解,找到了雙方均能接受的處理辦法。
鄧利強認為,調節解決成功的關鍵是兼聽雙方意見,提出的要求必須合情合理,具現實可行性。
主持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98條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在就醫過程中,如果您的此項權利受到侵犯,可依據《民法通則》或國務院頒發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如果您想通過司法程序維權,就須向屬地法院提出訴訟。下面請律師講講有關問題:
林江湧律師:法律是重證據的。如果你想狀告醫院在診療過程中對你或親屬的健康有損害、有過失,你就要有起碼的證據。
14歲的學生劉某因左睪丸疼痛約30小時,于去年10月10日去某醫院泌尿科診治。醫生檢查不仔細,未認真閱讀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報告,造成誤診,沒有及時手術,使挽救患兒扭轉的左睪丸的最后一線希望從醫生手中流失了。尤其讓當事者難忘的是:接診醫生檢查了病情后,邊寫病歷邊對另一位醫生說:前些天看過一個男孩,是睪丸扭轉。劉某的母親當即便問:“我們孩子是不是也是睪丸扭轉?”那個醫生說:“不是。”
過后,劉某的睪丸疼痛加重、陰囊紅腫,4天后,手術切開時發現:左睪丸扭曲360度,睪丸呈紫黑色壞死,只好切除。患兒家長今年5月向法院遞交了損害索賠的訴狀。
在律師代理案卷中,巴掌大的一張診斷書復印件上赫然寫著:“(左)急性附睪睪丸炎,建議休息叁天”,成了誤診的明證。
律師還復印了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泌尿生殖系統急癥》有關章節,其中熒黃彩筆標示的語句強調:“睪丸扭轉,若不及時診斷,盡早治療,將會發生失去挽救睪丸的機會,以致影響生育功能等。”“更重要的是醫生在對于睪丸疼痛者就診時,要想到睪丸扭轉這一疾病,這就能提高睪丸的挽救率。”多普勒超聲儀檢查,對睪丸扭轉、急性睪丸附睪炎診斷準確率可高達81.1%~90%。
林江湧律師:這些醫學專業性很強的論述,是確認醫療技術過失必不可少的科學依據。
北京郊區待業女青年雍愛民因嘔吐腹痛,1997年3月27日8時許,由其父母陪同來某院急診室就診。值班醫生懷疑她患宮外孕,請婦科會診。雖家人再三否認:“她沒男友,就在家學習,門都很少出。”但經治醫生仍固執己見。11點后,患者要排尿,值班醫生說:“正好驗驗尿吧,”開出二張驗尿單。
下午1時許,值班醫生看了妊娠試驗陰性報告單,說“這就好了”,婦科會診醫生離去,可患者病情越發嚴重,不停輸液輸氧,仍出現休克。下午5時許,醫生發出“病危通知單”。之后,醫生才注意到中午化驗單上尿糖的4個加號,于是才趕緊抽血送檢……第二天凌晨3點40分,患者心臟停止跳動。雍愛民死后11個小時,家人將尸體送去火化,未接受醫生做尸檢的建議。
2000年1月,北京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根據當時病情推斷雍愛民死于感染中毒性休克,合并糖尿病酮癥酸中毒,“構成一級醫療技術事故”。據此,其父母將該院告到區人民法院,索賠101969.2元。
2001年4月10日,該區法院審結此案,原告敗訴。其判決書再次重申:“凡發生醫療事故或事件、臨床診斷不能明確死亡原因的,在有條件的地方必須進行尸檢。醫療單位或者病員家屬拒絕進行尸檢,影響對死因的判定的,由拒絕的一方負責。”
主持人:據了解,雍愛民之父因感情原因,未同意尸檢,給維權造成無法彌補的證據缺撼。專業律師認為,此案病因不清,但死因清楚(病歷資料證明死于中毒性休克),而醫生未及時對癥采取搶救措施,是有責任的。可見,解決因素復雜的醫療糾紛,聘請專業律師是必要的。他們常能為解決爭議較大的醫療事件提供思路和切實幫助。
汪老太太患尿毒癥做血液透析治療,護士在做頸動脈穿刺時,連扎了幾次,造成局部滲血,形成腦水腫,壓迫呼吸中樞死亡。
專家們在鑒定此事件時,意見分歧很大。有人認為,穿刺時用點止血劑可減少滲血,從而避免不良后果;但也有人認為,尿毒癥晚期的病情已無法逆轉,死亡是疾病自然的轉歸。穿刺處置欠周只在死因中起次要作用。
鄭雪倩律師認為:對混合因素造成的醫療不良后果,應區分主要責任、次要責任。很多醫療事件,可能既有醫護人員的工作未到位或瑕疵,又有患者自身特殊體質、病情發展的因素。這就要組織有關醫學專家、法學家共同討論分析各方所應承擔的責任,再依據責任大小確定經濟損失(醫療費、誤工費、喪葬費、打官司費用、鑒定費等)分擔的比例。
主持人:“性命相托,責無旁貸”,白衣戰士從選擇專業那天始就接受了這崇高的理念。“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做百分之百的努力”,很多醫護人員都在履行著職業的承諾。正是他們的奉獻,保障了我國人民健康水平和平均壽命的提高。發生醫療意外與事故畢竟是個別現象。但這少數人的不幸牽動著全社會的目光,當然也引起醫院和醫務人員的反思:怎樣把不幸損失壓縮到最小?怎樣讓醫患之間的糾紛得到最佳解決?這是需要認真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