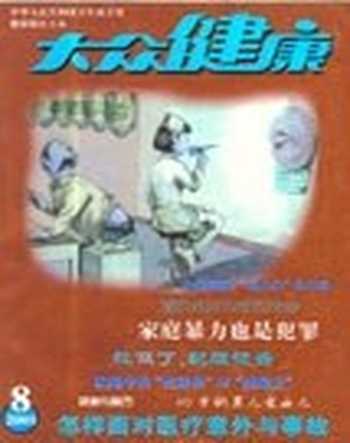在激情消失的地方
劉慶云
1921年秋,聞名世界的美國舞蹈家鄧肯與俄國偉大詩人葉賽寧在莫斯科的一個藝術沙龍上邂逅了,兩人一見鐘情,隨即墜入情網。次年早春,比葉賽寧大18歲的女舞蹈家與年輕詩人結了婚。婚后,夫婦倆輾轉西方各國,以他們的藝術才華“征服世界”,為他們初始的激情而沉醉。兩人的婚姻生活是在顛沛的旅途中度過的,雙雙執拗于不要事實上的共同的住所及家庭,但是,好景不長,兩人之間的感情很快出現了裂痕。對于兩人感情出現重大波折的原因,德國女作家卡羅拉·施德朗認為,他們“沒有掌握使愛情天長地久的規則,它需要寬容和諒解,給雙方以自由,在激情消失的地方注入友情……”1925年,在西方幾乎得不到承認的詩人葉賽寧,在長期沉湎于酒精的混亂、孤獨和失意之下,在圣彼得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1927年,在尼斯,鄧肯死于車禍,原因竟是她跳舞及日常喜用的一條紅色的長圍巾被卷進一輛剛發動開出幾米的“布加蒂”自用車的車輪……
鄧肯之死,一直作為一出充滿隱喻的悲劇被唏噓流傳,她與葉賽寧共同的婚姻和生命遭遇也令人扼腕嘆息。但在閱讀施德朗的傳記文學《鄧肯與葉賽寧》時,被我反復咀嚼的還有“在激情消失的地方注入友情”這句話。放眼日常生活,激情至上的觀念在影響著絕大多數人。人們往往將愛情等同于激情,繼而對愛情的發展變化產生出極大的誤會、苛責乃至失望,這樣的心態的確需要調整,施德朗的感慨和愛情觀值得我們體味和深思。無獨有偶,周國平在其《婚姻中的愛情》中也有相似論述。周在文中“對作為婚姻之基礎的愛情重新進行定義”,他認為“人們往往對愛情的理解過于狹窄,僅限于男女之間的浪漫之情”。這種浪漫之情依賴于某種奇遇和新鮮感,這種感情誠然是美好的,但不可能長久,并且這種不持久與婚姻無關。因為婚姻本身就是一個讓奇遇歸于平凡、讓陌生變成成熟的過程。“試圖用婚姻的形式把這種浪漫之情延續下去,結果當然會失敗,但其咎不在婚姻。事實上,愛情不僅限于浪漫之情,還有別樣的形態。”
隨著戀齡或婚齡的增長,無論是“激情”還是“浪漫之情”必然會遞減,但倘若“情”的基礎是健康和牢靠的,就會有另一種更為成熟和可靠的感情漸漸生長起來。這種新的感情由原來的戀情轉化而來,它可能不如原來那般熱烈和迷狂,卻具備了許多新的因素,“最主要的便是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互相的信任感、行為方式上的默契、深切的惦念以及今生今世的命運與共之感。我們不妨把這種感情看作為親情的一種,也是愛情的一種形態,而且是一種成熟的形態。”周國平稱之為“親情式的愛情”。
愛情是人類諸多美好情感中最為神圣和獨特的一種,而并非截然割裂、自行其是的一種。只有將愛情“進行”和上升到親情般的自然、無怨、難分難棄,融入責任與牽掛,并且了無功利,才可能獲得愛情的持久和穩固;只有將寬容、諒解和自由的精神賦予愛情,“在激情消失的地方注入友情”,才可能永葆愛情的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