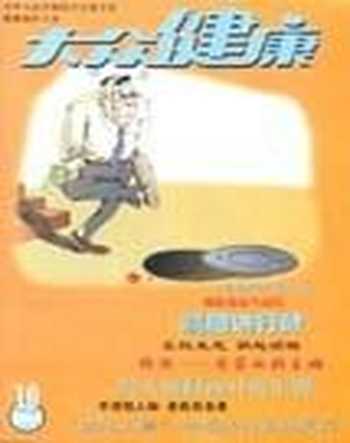珍愛生命
楊志松

星期日的晚上,我和電視劇《雪城》、《今夜有暴風雪》、《年輪》的編劇梁曉聲去北京立水橋的建筑工地看望昔日的兵團戰友王振東。本來約好是白天去的。后因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要采訪梁曉聲,只好臨時改變了計劃。
在工地的門口,保安攔住了我們。我們說明了來意后,保安扭頭問在燈光下納涼的工友:“哪個是王振東?”有工友接茬道:“就是那個王老頭。”
“王老頭?”我和曉聲相互間驚詫地望了一眼,這或許是我們第一次聽到有人管我們這樣年齡的人稱作老頭。驚詫之后,便是一聲喟然長嘆:歲月悠悠,當年風華正茂時上山下鄉的情景雖歷歷在目,我們卻轉眼間進入知天命之年,看看曉聲雙鬢間的白發,人家稱我們為“老頭”又何嘗不是名副其實的稱謂呢?
可我們仍在拼搏。那種“頤養天年,別無他求”的奢望離我們似乎仍很遙遠;即便我們背熟了詩人杜甫的“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又不得不在工作、生活的重壓下繼續地拼搏。
孩子們理解不了“知天命”的父母的心態,他們在假日可以約上豆蔻年華的伙伴們去麥當勞,無憂無慮地大口朵頤;可以連續幾小時在網上眉飛色舞地聊天,絲毫感覺不到隨著指鍵的跳動,流淌的全是父母的血汗錢。只有父母的韌性是最強的,責任和天性,使他們依然像一頭牛,心甘情愿地勞作,無怨無悔地奉獻。
不知道這一代的孩子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父母的。而我們這些知天命的人,盡管雙鬢已經染霜,卻恭恭敬敬地孝敬皺紋更深、頭發更白的父母。這是生靈的天性,當年我們的父母不也是“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的父母嗎?我們不能泯滅做兒女的良心。為了養育之恩涌泉相報,知天命的人們又不得不再次增強自己的韌性,去拼搏,去吃苦,去掙錢——為了夕陽下的父母更加幸福。
知天命的人或許是天下最辛苦的人。記得前不久,我去新華社拜訪一對老年夫妻作家,他們與我見面時的第一句話就是:“咱們見面是越來越難了,難道忘了當年的友情?”我說:“今年與當年不一樣了。當年是幾個人干一個人的活。現在是一個人干幾個人的活。這是因為計劃經濟時代的鐵飯碗早已成為過去,當鐵飯碗變成瓷飯碗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捧著它。為此,知天命的人們不得不迎著烈日,頂著嗆人的西北風,騎車上下班;不得不忍著汗臭味,沙丁魚般地擠在公共汽車里。看看我們不斷滋生的白發,看看我們日漸急迫的腳步、日漸焦慮的目光、日漸蒼老佝僂的軀體,就知道我們是如何對待自己現在的這份職業的。
在燈火通明的建筑工地,我們和“王老頭”——當年的兵團戰友暢談了許久。除了回憶當年近乎頑童般的往事,就是深深的感嘆,感嘆歲月如梭,感嘆轉眼就是人生百年,感嘆至今還卸不下工作、生活的重擔。分手時,曉聲留給振東幾樣“禮品”:幾本雜志——休閑解悶用;一罐茶葉——納涼解暑用;幾包藥膏——傷筋動骨用;200元錢——養護身體用。振東很動情地說:“你是大作家,還想著我這個普通工人!”曉聲說:“人生易老天難老,哪能忘了當年的感情。你們能蓋起這么一大片高樓,比我寫幾本書更能造福于百姓。但振東啊,你要記住,我們開始變老了,腿腳變得不靈便了,既然歲月不饒人,我們就要學會養老護老,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關鍵時刻,千萬不能讓身體垮了下去!”
這一刻,我們都沉默了,在久久回味曉聲話中的含意。是的,進入知天命之年的我們,恰似一艘帆船,載著我們的父母,載著我們的兒女,還有我們的希望在遠航。如果我們經受不住工作、生活的重壓,那么桅桿就有可能斷裂,就會留下白發蒼蒼的父母,就會留下“白頭偕老”的另一半,就會留下還沒有完全走向獨立的孩子。為了這,我們也應將自己的自信感、奮斗感、成功感留給下一代,而不應將自己的疲勞感、掙扎感、失敗感留給下一代。為了這,我們也應好好地活著,不為自己,而是為了那些還祝福著我們、還深愛著我們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