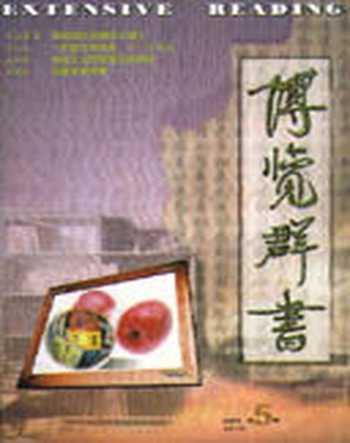古老問題的新學問
賀力平
信任或信用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面臨的基本問題。社會是人的集合體,凡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人發生交往關系,便會出現信任或信用問題。哲學家孔子在兩千多年前說過,“民無信不立”,其含義實際上指的是一個正常的社會離不開社會成員相互之間的信任,缺少了信任,社會關系就會陷入紊亂之中。
多少令人驚訝的是,論者的許多言論僅僅限于指出信任的重要性,不斷地重復著諸如“取信于民”、“以信立國”等等陳詞濫調。非常有諷刺意味的現實是,信任一直是許多社會的稀缺物品,人們渴望得到它,卻往往失望而歸。人們現在不僅希望在社會交往中得到信任,而且希望能夠理解何以在某種情況下他們得不到信任。
中國學者鄭也夫和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為克服信任問題上的認知差距作出了新貢獻。鄭也夫的《信任論》探討了信任概念的含義;信任與人的本性、習俗、人群共同體等等之間的關系;信任的社會功能;信任的各種表現形式;現代社會中信任扭曲行為的新特點。在這本篇幅并不大的著作中,作者旁征博引,融古貫今,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信任問題上極其豐富的面面觀,而且深入淺出地剖析了信任概念的內涵,揭示了這個概念與我們日常生活中許多司空見慣的現象之間的聯系。
從方法論上看,鄭也夫的《信任論》可以視為信任問題研究中的微觀論,即對信任問題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進行邏輯梳理,著重弄清這些概念的內在含義和相互關系。讀者如想找到這方面的代表性事例,可特別閱讀書中的第六章“信任對復雜的簡化”。這一章的主要分析思路可以概括如下:
從決策論的角度看,人的行動就是決策,而決策需要信息,正確的決策需要“完備的信息”,但“完備的信息要以嚴格的邊界和小的場景為前提”,在現實生活中這很難遇到;“生存環境中的信息是復雜、龐大、不完備的,生存中充滿了未知、風險和不確定性”,然而,人的決策往往是不能等待的,因此,人們需要發明既便捷又安全的決策方式,從有限信息中獲得關鍵信息。換言之,人們在應付和處理信息的過程中需要講究節約,以節約的方式概括和留存關鍵信息。人類語言是這么一種方式,金錢或貨幣也是這么一種方式,他們的共同特性都在于通過把握基本的(或者說關鍵的)信息而服務于社會成員的相互交往,從這個角度看,信任也發揮著相似的作用。信任的信息基礎是已有的信息,是歷史的記憶,這種信息相對于決策所需的“完備的信息”來說顯然是不完備的。但是,人們使用這種不完備的信息來進行決策不僅可以顯著節省信息成本,而且可以提高決策的安全性。經過多次重復的實踐而確立的關鍵信息便成為聲譽(或說信譽)的構成成分,這種信息盡管也是不完備的,但對人們決策的幫助作用更加突出。
鄭也夫是一位社會學者,但從這個事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他對經濟學分析已經有了非常精湛的把握和運用。在另一個事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思維方法的應用。在討論信任與秘密社會一章,作者指出,秘密社會或亞文化現象中存在著其成員對信任的需要,本來這種需要可通過正常規范的社會組織方式來滿足,但往往由于政府機構及其職能的不健全而得不到滿足,因此出現了部分社會成員尋求非規范的、有時是違法的替代性滿足方式。從這種分析中人們可以正確地推論說,現代社會如果欲致力于消除或縮小秘密社會和亞文化的影響范圍,最有效的措施往往不是直接去加重打擊或鏟除這些社會成員,而是努力改善政府和社會的服務體系,促使秘密社會和亞文化自然失去對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吸引力,從而失去其社會基礎。相反地,如果僅僅使用打擊和鏟除的措施,這很可能導致社會資源的低效率使用,因為——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根除了秘密社會的那個全權社會顯然不令人滿意,它滅絕秘密社會的刀劍也在傷害著社會的其他領域和成員”(第167頁)。
這些見解即使對專業經濟學者來說也是很有啟迪意義的。過去,在解釋計劃經濟體制的起源時,論者們往往從大工業的規模經濟觀點出發,認為正是由于存在著規模經濟效應,以集中使用資源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為了達到集中使用資源的目的,人們進一步認為應當對社會經濟資源實行國有化。但是,以現在的眼光看,這種對計劃經濟體制或國有化的解釋顯然是不夠充分的。如果說計劃經濟體制或國有化主要出于規模經濟的考慮,那么,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化的范圍也應當主要限于在那些其規模經濟效應較為突出的領域或經濟部門中。事實上,在過去的中國以及別的一些國家,政府實行了全面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化,其范圍已經覆蓋到諸如農村的小農經濟和城市的個體經濟。在這些遠沒有規模經濟的領域中也采取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化(或者較低級別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化措施),其理由需要從別的地方去尋找。在各種這類解釋性理由中,現在看來很有說服力和相關性的是鄭也夫著作中所說的“信任不足”的問題。很可能正是因為過去社會中存在著廣泛的信任不足問題以及社會成員對信任的強烈需要,由政府出面來組織所有經濟活動并以此來滿足社會成員對信任的需要便成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方式。換句話說,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化的原因不在別處,而主要在于社會成員對普遍信任的需要以及這種需要在非計劃經濟體制和非國有化環境中難以得到有效滿足的情形。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新見解,從根本上突破了過去那種對社會組織方式的機械物質力的決定論觀點。
福山的著作也表達了類似的見解。他在書中說,“信任并不存在于集成電路之中,也不存在于光纖電纜中。盡管這涉及到信息的交換,但是信任并不能分解成信息”(第29頁)。用另外的言辭來說,這段話的含義是,信息技術的硬件進步并不能消除由“信任軟件”落后所帶來的對人類發展的制約作用。在普遍性地缺少信任的社會環境中,信息技術硬件的進步所能帶來的積極作用將受到極大限制。也就是說,“一個信任程度非常低的社會將永遠無法利用信息技術帶來的便利”(第30頁)。
福山是一位祖籍日本的美國學者,在1990年代初寫了具有世界影響的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個人》(該書由美國Penguin出版社1992年出版,其原型是福山在1989年發表于美國《國民利益》(National Interest)夏季號的文章)。他在這本書中指出,現代世界的各個民族正在朝著越來越具有共同性的目標前進,傳統的社會制度之爭正在讓位于對實際利益的追求(讀者不妨比較這個觀點與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明確提出的“不爭論”的觀點)。福山的見解隨后被廣泛認為是看待后冷戰時代各民族發展趨勢的指南,并促使經濟增長問題上升成為各國政府和政黨的首要任務。整個九十年代,技術創新、民營化、開放政策等等事物在各國如火如荼地展開。很多人似乎認為,有了這些東西,國民經濟便可順利踏上高速增長之路。福山在這部題為《信任》的著作中又先人一步地指出,信任問題是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該書的副標題“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很能說明這個意思。
福山的論證方法是宏觀和比較的。他的這部著作又可以說成是信任問題的宏觀論和國際論。他選擇了世界上若干有代表性的民族來說明各國經濟中一般信任程度的高低以及信任程度與各自經濟增長情形的關系。他陳列的許多事例是研究者和觀察家們早已熟悉的,但他卻給予它們以新的解釋。例如,他指出,家族企業的流行實際上是一般信任程度較低社會中的一種典型。家族企業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普遍信任不足為企業發展帶來的種種限制。但是,家族企業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解決了人事信任不足的問題,卻難以為自己解決后續發展的問題。繼續依賴于家族成員操舵企業發展事業往往也是對自己最大限度利用社會優秀資源的一種限制。在這方面,福山舉了一個著名的事例。1980年代在美國電腦界叱咤風云的王安公司在經歷了多年高速擴張后栽倒在“接班人”問題上。王安是一個成功的華裔企業家,但卻固執己見選擇了自己的兒子接任企業總裁位置,眼睜睜地看著其他高層優秀人才的流失,以及隨后而來的企業業務的萎縮。這種類型的失敗在低信任的經濟體、企業體和政治體中都存在。這是很應當引起人們關注的重大問題。
鄭也夫的《信任論》和福山的《信任》兩書都是嚴謹的論著,圍繞著一個中心議題和主題來展開。前一本書對概念的探討更加深入和細膩,后一本書通過對各國事例的比較帶來了更加寬廣的視野。兩本書讀來都引人入勝,而且其程度遠遠超過了一般學術性著作。值得指出的是,鄭也夫的《信任論》在許多重要編輯體例上采用當代國際通行的方式,例如,在章末列示注釋并在文末統一按拼音順序列附參考文獻以及主題和人名索引。這非常方便讀者。中譯本《信任》的譯文是很流暢的,但卻省去了原著的文獻注釋和索引,實為一小小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