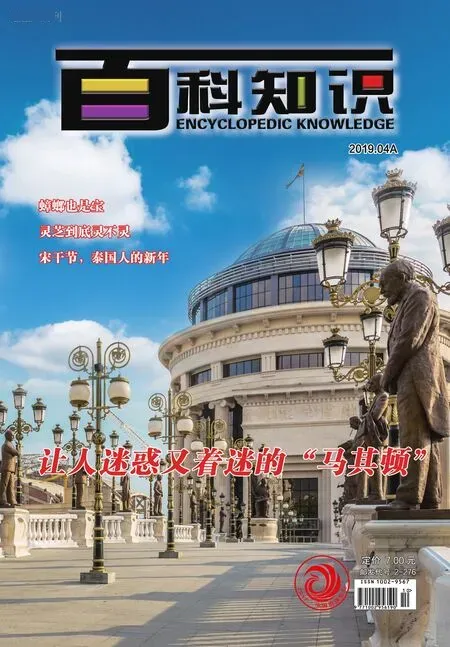疫情期間乘坐飛機安全嗎
沈海軍
當前,全國各地在切實做好防控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同時,正在有序推進企業復工復產。從2月中下旬開始,在感染人數較少的大多數地市,企業陸續開工,結束春節長假的人們紛紛返程。在疫情期間出行,是坐長途大巴、火車,還是坐飛機呢?究竟選擇哪種公共交通工具才更安全?這是大多數返程復工者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
作為一名航空從業者,撰寫此科普文章,供返程的朋友們參考。
呼吸道傳播需提防
病菌在飛機上容易傳播嗎?答案是肯定的。
病菌要從傳染源傳給被感染者,一般可分為呼吸道傳播、皮膚接觸傳播、口腔與眼睛傳播、消化道傳播以及泌尿生殖系統傳播等途徑。眾所周知,和長途大巴、地鐵、火車、市內公交車一樣,民用客機機艙內的乘客密度大,空間密封狹窄,空氣流通性差,這無疑為病菌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

以常見的空客A320客機為例,飛機密封艙內的容積粗略估計為3500立方米。目前,多數航空公司經濟艙內旅客的座位間距,前后約為80厘米,左右約為45厘米;公務艙要好一些,座位前后間距約為100厘米,左右約為65厘米。據此換算下來,A320可搭載的乘客總數能夠達到150人。通常情況下,人們會在中遠途出行時選擇搭乘飛機,這樣一來,飛行時間動輒三四個小時,100多名旅客和機組人員長時間停留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內,大家同呼吸、共命運,共享著有限的空氣;旅客咳嗽、近距離交流、打哈欠時的飛沫、呼出的氣體……均會進入這個有限的空間中。因此,呼吸道傳播是航班上病毒傳播的最重要途徑。
皮膚接觸是飛機上病菌傳播的另一個重要途徑。在整個旅程中,值機、安檢、候機、登機、航行、機上就餐、如廁、下飛機……旅客難免要觸摸座椅扶手、各種把手、安檢筐、柜臺、自動出票機、馬桶蓋等物品。你知道嗎?細菌無所不在,扶手、門把手都不是最臟的,機場中帶細菌最多的是每個旅客都避無可避的安檢區和安檢筐。研究顯示,有些安檢筐比廁所還“臟”。通過接觸上述物品,病菌便會悄然轉移到旅客身上。

此外,也不能絕對排除因食品、如廁、飛沫等因素引起的消化道、泌尿生殖系統或口腔與眼睛的病菌傳播。不過,與呼吸道、皮膚接觸途徑相比,這些途徑傳播病菌的概率要小許多。

坐飛機相對更安全
在公共衛生與病菌傳播方面,同長途大巴、地鐵、火車、公交車等公共交通工具相比,航空旅行無疑更安全一些。為什么這樣說呢?
首先,在眾多公共交通運輸方式中,機場的安檢最嚴格。
相信坐過飛機的朋友都知道,機場的安檢是極其嚴格的。其嚴格程度遠高于地鐵站、火車站和長途客運站。機場安檢不僅可以杜絕旅客攜帶可能會威脅飛行安全的物品,而且禁止那些未經檢疫、可能帶有寄生蟲和病菌的物品登機。這些措施能夠有效地切斷傳染源。此外,在重大傳染病疫情期間,許多機場還會增設專門的檢驗檢疫設備、隔離區甚至醫療急救點,以備不時之需。
以廣東珠海機場為例。該機場從2020年1月開始便在到達和出發層分設了若干紅外體溫檢測點、隔離區與急救點,同時對外公布了醫療急救電話。機場要求每位乘機旅客必須接受體溫檢測,并且必須佩戴口罩。對于特殊旅客,還制定了體溫監測流程。另一方面,對于到達航班,機場要求它們停靠在指定機位,再通過擺渡車將旅客送到指定通道,接受體溫檢測,如發現有發熱且有呼吸道癥狀者,須立即隔離,并報送珠海市疾控中心及當地衛生健康局應急科,以便將患者轉送到指定醫院。
其次,民航系統的公共衛生與防疫制度是最嚴格和最規范的。
患有傳染病的旅客是否可以乘坐飛機,民航部門對此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定。譬如,對于患有烈性傳染病的旅客,國家禁止其乘坐民航班機;對于患有急性傳染病的旅客,因急救或一定要乘坐飛機時,須持醫療單位出具的證明向民航管理局提出申請,經批準后方可購票乘機;至于患有其他傳染病的旅客,如需乘坐民航飛機,必須包艙或包機運送。不僅如此,對于公共衛生與防疫制度的具體實施,各機場和各大航空公司也歷來嚴格按照規定不折不扣地執行。
第三,機場及航班上的公共衛生條件是非常優越的。
不論是與長途汽車站、火車站、地鐵站、公交站相比,還是與長途大巴、地鐵、火車、城市公交車本身相比,民航機場和客機的公共衛生軟硬件條件都更為優越。
機場與機艙衛生間的常態是一塵不染,不僅為旅客提供免費衛生紙,還配備洗手槽、洗手液甚至手部自動烘干機與通風機;機場值機大廳與候機大廳、電梯與飛機客艙內干凈衛生,有專人定時消毒和不定時保潔;候機廳與飛機上的座椅總是整潔如新;機場大廳內的空氣由中央空調系統進行調溫和通風,為旅客提供了舒適的登機、候機與接機環境;飛機密封艙內也配備有專門的空調與通風系統,通風量和通風頻次可調;機組人員訓練有素,上崗前均要求他們掌握基本的防疫知識和對常見疾病的應急處理方法,其中亦包括對患有明顯傳染癥狀旅客的臨時隔離與應急處理等;機上與機場內的食品均需達到嚴格的衛生與檢疫標準……上述種種公共衛生軟硬件條件,能夠有效抑制病菌的滋生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