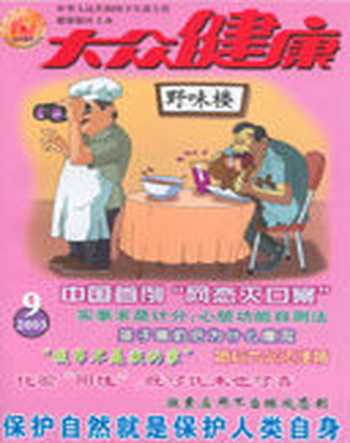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身
張荔子
2003年5月23日,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學宣布:從果子貍標本中分離到SARS病毒;5月24日,農業部和廣東省聯合組成的科技攻關組也宣布,從蝙蝠、猴、果子貍以及蛇等數種動物體內檢測到冠狀病毒。
這些野生動物真的是非典的肇事者嗎?帶著這個疑問,記者撥通了從廣東考察歸來的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張樹義的電話。電話那端,他說:“我高興地看到這些學者所取得的成績,但同時也有一種莫大的擔心:這些野生動物將會被如何處置?野生動物是無辜的,人類自己才是始作俑者。”張樹義與記者談起了最近幾十年與野生動物相關的疫病。
人類艾滋病病毒是怎樣起源的
張樹義說,在最初發現艾滋病時,這個問題令人十分困惑,世人眾說紛紜。經過不懈的努力和艱苦的探索,科研人員終于找出了該病毒的自然宿主,它很可能是生活在非洲的綠猴或稱非洲猴。
由于非洲炎熱的氣候和潮濕的居住環境,各種人畜共患的傳染性疾病在該地區的流行發展都很迅猛頑固。在一些地方,尤其是鄉村部落,人們對性關系的態度比較隨意。某些地區的居民還有一種世代相傳的習俗:用猴血注入人體來刺激性欲,甚至用于治療婦女不孕癥和男性陽痿等病。該地區為艾滋病高流行區,間接證明艾滋病病毒是從猴傳給人的。不過,如果追溯該地區這種習慣風俗,最早的年代可能遠遠長于艾滋病流行的歷史,使得這一觀點也有令人懷疑之處。不過,艾滋病專家們堅持認為,可能在很早以前,艾滋病就曾通過猴子傳染過人類,但因為某種偶然的原因而自生自滅;又由于某種契機,造成了今日的廣泛蔓延。
病毒學者從200只非洲綠猴的末梢血液中成功檢出70只帶有與人類艾滋病病毒極為相似的病毒,充分證明了上述由猴傳人的推斷。而這種生活在非洲的綠猴造成的艾滋病病毒流行所傳播的不僅僅是當地居民。由于它們多生活在人類居住地附近,或成群結隊于國家開辟的旅游勝地及公園等場所,或尋食、或與人們嬉戲,有時會咬傷游客,這樣就將猴艾滋病病毒傳給人,尤其多見于居住于扎伊爾的海地人。然后,又由移居至美國的海地人將病毒傳到美國,再通過美國這個世界各地人口流動性最大的國家傳播到世界。專家認為,這種猴艾滋病病毒進入人體后感染的過程中可產生突變,進化成為人類的艾滋病病毒。
埃博拉病毒與靈長類動物有關嗎
張樹義介紹,1976年,埃博拉病毒出現在非洲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其名字源于剛果境內的一條河流。埃博拉病首次暴發就顯現出巨大的殺傷力,奪走了270條性命,不過當時沒有人知道這究竟是何種病毒。埃博拉病第二次大暴發是在1995年,有245人死于非命。在發現埃博拉病毒后的20多年里,全世界死于這種可怕病毒性傳染病的大約有1萬人。
埃博拉病毒引發的癥狀十分恐怖。感染者發高燒,肌肉疼痛無比,體內的心、肝臟等內部器官開始糜爛成半液體的塊狀,最后患者眼睛、嘴、鼻子和肛門大量出血,全身皮膚毛孔浸滿污血而死。埃博拉病毒極易通過患者的血液、精液、尿液和汗液傳播,一般潛伏期為3周,感染者的死亡率高達90%。發病初期的癥狀極具迷惑性,容易被醫生誤認為是普通的發燒或者麻疹。
埃博拉病毒引起休克和大出血癥狀的機理很復雜。病毒侵害多種細胞,特別是免疫系統的巨嗜細胞和肝細胞。有些研究者認為,這些細胞的損害導致毛細血管內的血液倒流入外周器官,從而造成循環系統的崩潰并使人快速死亡。
前一陣子,剛果西北部與加蓬接壤的地區再次大規模暴發埃博拉病,已經有100多人因感染埃博拉病致死。據剛果衛生部部長對媒體公布的消息稱,此次埃博拉病暴發的原因是當地居民食用了附近森林里死去的靈長類動物。
尼巴病毒如何來自狐蝠
張樹義指出,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尼巴病毒在馬來西亞首次暴發,導致成千上萬頭豬死亡,并在幾周內傳染給人,所感染的276人中有105人死亡。系統學研究發現,尼巴病毒屬于副黏病毒,在現有的副黏病毒科成員中,尼巴病毒與亨德拉病毒親緣關系最近,被歸為一個新屬。
在尼巴病毒感染的豬場內,病毒傳播速度很快。同一豬場內的豬之間的傳播,極有可能是通過直接接觸病豬的分泌物或排泄物,如尿、唾液、喉氣管分泌物等,尤其是在封閉式豬舍內。病豬的典型特征是急性高燒、呼吸困難和神經癥狀。病人均為豬場或屠宰場工人,主要是通過傷口、病豬分泌物和排泄物(如唾液、鼻腔分泌物、尿液、糞便)、血液、以及呼出的氣體等直接接觸而感染尼巴病毒,表現為起病急、發燒、頭痛、行為改變、肌痙攣、心動過速、視力輕度模糊。接著,病人開始昏迷,神經癥狀和體征呈進行性惡化,呼吸極度困難,不可逆性低血壓及峰形發熱。典型病人從發病到死亡僅6天。沒有發現尼巴病毒在人之間傳播。
鑒于尼巴病毒與亨德拉病毒有很近的親緣關系,所以蝙蝠就成了首要的監測目標。馬來西亞蝙蝠種類多樣,包括至少13種食果蝙蝠和60多種食蟲蝙蝠。對14個種324只蝙蝠血清進行檢測,其中5個種(包括1種食蟲蝙蝠)的21只蝙蝠有尼巴病毒中和抗體。后來又從黑狐蝠尿液內分離到尼巴病毒,進一步證實了狐蝠就是尼巴病毒的自然宿主。
對尼巴病毒的研究結果表明,這場病毒的暴發與砍伐森林密切相關:森林面積減小、食物不足,迫使狐蝠從傳統的森林環境中遷移到森林邊緣附近的果園取食;而馬來西亞有許多養豬場與果園毗鄰,受狐蝠污染的果實掉落到地上,被豬吃掉,從而把致命的病毒帶到人類社會。
SARS病毒是否來自果子貍、蝙蝠、猴子、蛇
張樹義說,對這個問題,他已經不想陳述,只想問一句:這些野生動物怎么好端端地鉆進籠子里,跑到了菜市場?
病毒性疾病為何頻頻暴發
這涉及兩個問題:生命之間的協同進化,人類活動的日益增加。地球上所有的物種都是在過去的35億年間產生、繁衍和進化的,其中一些物種之間在進化過程中相互作用。也正是這些相互作用,使人類今天看到的自然界不僅是一個個彼此獨立的物種,而且是植物間的相生相克,動物間的食物鏈關系,一種生命依附于另一種生命等諸多行為和現象。
病毒也是一樣。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它們曾經“試探”了各種各樣的宿主。如果對方的“抗性”太強,它們便無法依附;如果對方的“抗性”太弱,便會被“斬盡殺絕”,導致宿主物種的消逝。就是在這漫長而又不斷的“磨合”過程中,物種之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協同進化關系,生態系統也平衡下來。然而,一旦一個新的、原本沒有任何抵抗力的物種接觸到病毒,因為沒有抵抗力而無法控制病毒的大量繁衍,病毒種群便會大暴發,災難也就出現了。當然,除了這種方式,病毒自身也可能發生變異,而導致宿主原有的抵抗力減弱或消失。
眾所周知,由于人口數量不斷增加,人類的各種活動日益頻繁,人們不斷和大自然中的動物發生直接而又密切的接觸,而這些動物原本和人類是根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可以說,是人類對大自然的肆意破壞,對野生動物的大吃特吃,打開了一個又一個“潘多拉”魔盒。這次SARS的流行再次告誡我們: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身,這真的不是一句口號;如果我們不遵從大自然自身的規律,下一個,甚至更大的“SARS”在不遠的將來也許還會出現。
最后,回到主題———如何對待這些“肇事”的果子貍、猴子、蝙蝠、蛇?張樹義認為,這應該是留給全社會的思考。他的答案是一句反問:事實上,相當多的野生動物都可能攜帶這樣或那樣的病毒,我們能將它們全部消滅掉嗎?
人類,應該獨善其身,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