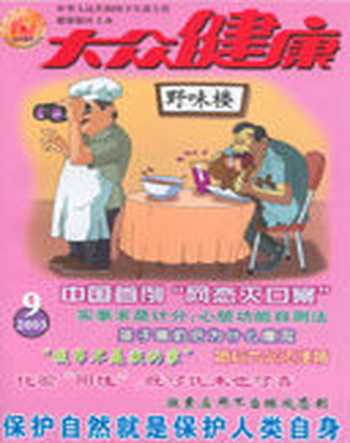“城市不是我的家”
孟慶普
“北京?別提那兒了。”電話那端,凡東的語氣憤怒中有些沮喪,“麥收后還回去?再說吧。”
32歲的凡東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縣隨莊村的農民,今年2月中旬來到北京,在一個裝修工地當泥瓦工。4月20日前后,他干活的小區內開始傳說非典的可怕和高度傳染性。“當時我們很害怕,哪里都不敢去,就想著趕快回家。”凡東說。
回老家的大部分運輸車當時都已停止運營,他決定騎自行車回家。第二天傍晚,騎了300公里的他終于到了家鄉的村口,卻被村干部們給攔住了,當即被隔離在早已在村邊搭起的塑料帳篷內。
三個星期后,凡東健康地回家了。
凡東只是非典暴發時期眾多逃離北京的外地民工中的一個。盡管從一開始,北京市就意識到民工返鄉可能導致非典擴散,三令五申,勸阻民工返鄉。但據北京市有關部門公布的數字,在北京暴發非典疫情之前,全市外來建筑施工人員超過70萬人,到了5月20日,建筑工地的民工總數已經銳減為62萬余人。這意味著在一個月之內,大約有10萬建筑民工離開了北京。
誰都知道北京的醫療條件和救治水平全國一流,即使染上非典,在北京獲救的機會也要大得多,但那些民工為什么不約而同地選擇回家?
一直關注農村外出打工者生存狀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譚深指出,民工返鄉的原因和大學生不盡相同,他們不完全出自對非典的恐慌。生病,而且是在務工地無法應付的重病,就要回家。這是歷來農村外出打工者的選擇,也是他們的無奈之舉。
生病對于在外打工的農村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首先,他們在生病期間沒有了收入,有些雇主和工廠還規定病假要扣工資。其次,看病需要自己花錢。民工是沒有醫療保險的,大病小病都要自己負擔,而除了必要的開支,他們的收入一般都寄回了家鄉,很少為意外的傷病預留。據媒體報道,在政府對非典患者免費治療的政策出臺之前,有的民工因經濟困難,被送進醫院后鬧著要出院;還有的交了住院押金之后,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了。如果是一般的病,民工仗著年輕,往往買些藥吃就扛 過去了;病情稍重一點,向親友借錢;倘若不幸得了重病,除了回家也就別無他法。難怪訪談中民工說:“生病就像塌了天。”
政府部門顯然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接連出臺了防止民工流動的措施:醫療費用方面從實行救助到全部免費;勞動用工方面規定不得解雇、轉移或遣送民工,治療或隔離期間工資照發等等。這些措施對于非常時期控制疫情、保障農村防非典襲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記者以外地在京民工都有何種健康保障為題,先后詢問了北京市社保、建設、衛生等部門,發現除了前不久臨時出臺的一些非常措施外,并沒有相應規定,而即便是這些應急措施,也僅僅適用于非典。非典以后怎么辦?沒有答案。
“他們是城市的建設者,但城市卻不屬于他們。”一位社會學者評論說。長期以來,這些支持著城市建設的民工們,并沒有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有些人的工錢都難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說醫療、工傷保險了。
不少民工的生活條件極其艱苦和惡劣。記者前不久在北京疾控中心采訪時,防疫人員曾說起一家發生過疫情的工地職工宿舍的糟糕環境:一個廢棄倉庫隔成3個大房間、3個中房間及一排簡易工棚,3個大房間分別住108人、110人和125人,每間面積只有380平方米。鋪位是上下兩層大通鋪,中間有通道,寬約1米。室內地面較室外地面低0.5米,每個房間的通氣口只有0.5米×0.2米。在30米×70米的工地內,生活著593人!宿舍旁邊是廁所和簡易食堂,廁所離食堂只有10米,食堂食品衛生和食品質量根本不能保證。垃圾露天堆放,離最近的宿舍出口只有5米。生活區到處是積水、痰跡。室外的水池下水系統污物暴露。“這種居住狀況為呼吸道和消化道傳染病的暴發創造了條件。”這是防疫人員調查得出的結論。
近年來,關于外出民工安全和健康的事故不時見諸媒體,觸目驚心。主要包括:職業安全,如頻頻發生的礦難、工傷事故、工作或居住場所的火災、化學品中毒等職業病,以及失業等;人身和財產安全,如春運高潮中及平時的交通事故、被殺、被打、被拐、被收容、被搶、被偷、被強奸、失蹤等;生活中的安全與健康,如食物中毒、一般疾病、重病、傳染病、人工流產,以及身上沒有一點錢等;精神健康,如一般心理疾患、精神病、自殺等。幾乎可以肯定,作為流動人口的民工,這些安全和健康事故的發生率,要高于穩定的人群。而其中除少量事件外,任何一個事故的發生都可能導致民工命運的逆轉,使其滑向貧困。
近幾年,有關學者在對農村外出務工者的研究中,開始比較多地關注到上述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譚深曾分別參與或組織過對全國和廣東的民工調查,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李強教授等也對北京民工進行了連續幾年的調查。當調查涉及民工打工期間的健康經歷時,盡管沒有發生嚴重的事件,但民工一般的安全健康狀況不容樂觀。比如當問到工作場所有無有害健康的情況時,廣東的外來工中有11%的人認為“嚴重”,45.7%的人認為“輕微”;而問到每天下班以后的感覺,有近一半的人回答“非常疲勞”和“比較疲勞”;另外有9.2%的人出現過工作時暈倒,27.4%的人出現過精神極度緊張的情況。
非典的流行讓政府注意到了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記者來到北京市朝陽區望京地區附近的某工地,只見大門緊閉,保安人員還戴著嚴嚴實實的口罩。一位民工熱情地告訴記者,他們的住宿環境變好了,每間房住的人比過去少了,每天回去都能聞到很濃的消毒水的氣味,還不時收到項目部送來的藥物和水果,伙食質量也有明顯的提高。
在另一家曾出現非典疫情傳言的工地,情況似乎更好一些。一位民工滿足地說:“如果將來非典鬧完了,還能這樣就好了。”
基于非典疫情本身傳染的特點以及集中居住、生活、工作的生存現狀,對工地上的外來民工來說,改善住宿條件和生活環境成了起碼的要求。那么,這種非常舉措在未來能否成為一種制度性的規定和安排呢?
另外,有關專家認為,以上措施主要是針對成建制的或是在正規單位工作的民工,而對那些散工或自營者,作用卻很有限。據專家分析,中國流動人口中自營勞動者占1/3強,在私營、個體中就業的占1/5,兩者相加占到流動就業者的一半還多。這部分人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往往更差,工作更不穩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有關專家介紹說,外地民工在城市屬于非正規就業者。這次因防治非典的需要而對民工生活條件的改善,作為一個特定條件下的特定行為,有可能成為加快城鄉一體化制度建設和改善民工境遇的契機。但專家同時也指出,對民工權益的保護,是一個太大的話題。
民工是連接城鄉的一個群體。從民工與家鄉社會割不斷的聯系來看,他們的衛生和健康似乎應考慮在農村公共衛生系統之中;但他們的主要工作生活又是在城市或其他地區,他們的健康狀況又與當地整體水平有著直接的關系。按照現有的制度,民工安全和健康的成本,最終是由本人、家庭和輸出地、社會所承擔的。但是非典的流行給了我們嚴重的教訓:其一,同一社會環境下生活的人都是“利益相關者”,城市人或當地人獨享利益是不可能持久的。其二,保護農村,就不能不保護農村的有生力量———那些為農村和城市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年輕的打工者。
因此,從保護生產力的角度考慮,當前應該把民工安全健康系統的建立放在首位。譚深認為,政府的公共衛生系統應針對弱勢人群的需求,而不是分城鄉覆蓋所有人群。所謂弱勢人群,大致包括不發達地區的農村人口、城市的貧困人口以及流動人口。在發達地區,特別是聚集了大量民工的地區,應建立社會救助等形式,以幫助危難之中的外來人口,同時緩解由于差距過大帶來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