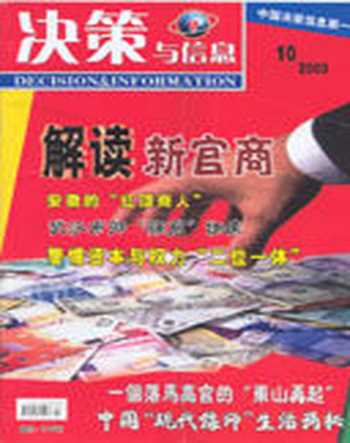“陸步軒事件”反思
胡云生
許多本來很尋常的現象,只因為人們以不同的視角去看,以不同的標準去衡量,便似乎成了不可思議的事。現年38歲的北大畢業生陸步軒因當街賣肉,被媒體報道后引起廣泛關注。嚴格意義上講,有幾個“陸步軒”在中國是算不了什么的,但事件帶給我們的思索卻是不少的。北大生當街賣肉
陸步軒,陜西長安縣鳴犢鎮高寨村人,自幼喪母,家境貧寒。姐弟4人與務農的父親相依為命。1985年,陸步軒以長安縣文科狀元考人北大中文系。1989年,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只有300職工、經營狀況不好的長安縣柴油機械配件廠。后借調縣計委寫材料,但因借調,各種福利待遇都沒有。后來計委辦企業,陸步軒自告奮勇去了企業,辦過有色紙廠、飼料廠、化工廠,都因沒有資金,廠子難以為繼。陸步軒開始自己組建了一個裝修公司,漸漸地翻了身。最輝煌的時期他手下有100多人,然而,一次貿然投資讓他一下子栽了進去,此后“再沒有翻過身”。
事業上的失意也讓他的生活遭遇到打擊,妻子離開了她。2000年,迫于生計,陸步軒和現在的妻子租房子開起了肉店,取名“眼鏡肉店”,因誠信不欺,保證質量,為鄰里稱道。如今以“縛雞之力”日售五頭已不在話下,被戲稱“屠夫狀元”。
隨著年齡增長,過去的理想被現實生活負擔所代替。幾年來,陸步軒也曾試圖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早在1997年,他到西安一家報社應聘,但因月薪300元無法養家糊口,也就作罷。2002年,他通過熟人提供的信息,到長安區一家中學去聯系工作,并為此寫了篇上萬字的文章送了過去,但之后就沒了回音。他說,自己還是喜歡研究語言文學,適合做編輯詞典的工作,但求職無門。
“陸步軒事件”被媒體報道后,已有多家單位表達了愿給陸步軒提供就業機會的意向,有20多家單位還派人親自到長安尋訪陸步軒。從窮困潦倒到“聘者如云”,陸步軒似乎看到了希望。可謂“柳暗花明”!
“陸步軒事件”說明什么
實際上,“陸步軒事件”涉及到人才問題的很多方面,其意義早已超出了事件的本身,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和重視。
反思一:構建科學的用人機制,真正做到人盡其才。
新世紀以來,黨中央提出了“人才強國”戰略,為全國各地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腳踏實地地做好人才的基礎工作,構建科學的用人機制,真正做到人盡其才,這是做好人才工作的基礎。
分析“陸步軒事件”,他從北大畢業后被分配到國營企業,后來也曾辦過企業,搞過裝修,現在以賣肉為生。這些工作與他所學的專業都離得比較遠。陸步軒的“轉業”是不是人才浪費?是不是西部人才機制的問題?在沒有做深入研究以前,我們不能簡單地進行這樣的價值判斷。但從實際情況來看,近幾年來,從國家到地方都在喊“人才缺乏”,特別是西部欠發達地區,最缺的就是人才。調查數字顯示,東部地區平均每100人擁有科技人員18名,西部只有2名;東部鄉鎮領導學歷在大專以上的占64%,西部不足20%。即使是在改革開放2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仍需要每年“招募”數千名應屆大學畢業生支援包括陜西省在內的西部地區建設。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家花那么大的力氣去培養大學生,“陸步軒們”卻在干著與他們的知識不相稱的工作,特別是“陸步軒事件”發生在西部長安,這本身就需要我們反思。一方面呼吁人才匱乏,一方面本地人才卻未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花很大氣力引進人才,一方面卻使人才用非所學。如果不改變人才使用的大環境,如果不是真正用求賢若渴的心情去關心人才的成長和使用,相信還會出現“陸步軒事件”。
反思二:建立健全人才的社會服務體系,真正解除人才的后顧之憂。
“陸步軒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配”、“借調”等典型計劃經濟時代行為的產物。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人才制度而言,政府不再是恩賜地分配工作,而是應該建立健全人才的社會服務體系,創建一個人才發展的平臺。
人才的社會救助機制不能僅靠媒體效應,它需要的是程序化、理智化的救助,應該以社區為單位,對社區內所有居民的就業狀況、個人學歷以及所長有個比較詳細的了解。最近媒體還報道了一位博士回家相妻教子的事。37歲的計算機博士劉同波,是一家著名的計算機公司的技術部經理,他的妻子經營一家玻璃工藝品公司,生意甚是紅火,其經營的玻璃制品已經打人歐洲市場。由于孩子降生,先后請兩個保姆都不得力,在無人照看小孩的情況下,為了不影響妻子蒸蒸日上的事業,劉博士毅然辭職回家“相妻教子”。從某種意義上講,博士的舉動也暴露了社會人才服務體系的漏洞。怎樣建立起“人才社會救助機制”,建立暢通的人才信息反饋系統,真正為人才服務,避免人才資源浪費,是各級各部門不容忽視的。
反思三:重新界定人才標準,真正轉變人才的就業觀念。
“陸步軒事件”之所以會引起社會反應,主要是由巨大反差引起的。陸步軒是以當地狀元的身份考進北大的,而北大是中國最好的學校之一。因此陸步軒的賣肉行為很快就激起很多讀者懷才不遇的共鳴。無獨有偶,日前新聞報道說:某地“舞女當了法官”,言外之意當過舞女的人就應一輩子下賤;浙江一位女廳長淪為貪污犯,強調的是“她初中畢業,過去是賣面條的”,賣過面條竟被視為不光彩歷史。和“陸步軒事件”相似,這些報道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國人對職業與成才過程的認識表面化、簡單化,對人才標準的劃定還停留在文憑崇拜上。
文憑不是“金書鐵券”,套用丘吉爾那句名言:沒有永恒的文憑,也沒有永恒的地位,只有永恒的價值。能力導向和業績導向,是今天人才標準的核心理念。如果我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對陸步軒個人遭遇的感嘆上,則有可能對當代大學生的就業觀會產生負面影響。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212萬,一次性就業簽約率為50%。就業情況為什么不理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大學生就業期望值過高,想找工作環境、薪金等條件比較好的而又專業對口的單位。所以,只有重新界定人才標準,轉變人才的就業觀念,才能使大家的眼光更開闊一點,期望值放低一點,把畢業就業與終身職業選擇分開來,真正有利于人才的全面發展。
反思四:注重人才的職業生涯設計,真正提升人才自我能力。
在“陸步軒事件”中,完全把責任推給人才制度和用人機制是不對的。畢竟陸步軒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最重要還在于他個人能力方面存在著許多缺陷,比如說個人推銷、自我包裝、自我定位、人際交流等方面的能力不足。一個北大中文系的畢業生,14年來始終偏離自己的專業,自我封閉,死守長安。借調機關,卻主動要求去跟隨領導辦企業;一事無成后又“自己組建裝修公司”,終因學非所用,“一下子栽了進去”;到一家報社應聘,干得好不會亞于操刀賣肉,最后卻“因三百元工資無法養家糊口也便作罷”而沒有堅持下來。
市場經濟條件下,告別了統包統配,就業和職業選擇成為了人才的個人行為。職業的流動是一種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投資是一樁風險的買賣。一個人盡管不能決定自己是成功還是失敗,但多一分對自己的了解,未來就多了一分勝算。作為個體的人才需要的是努力提升自我,拓寬知識、創造機遇、調整心態、運籌人生,而不能完全等所謂伯樂發現自己這種撞大運的事情發生。
嚴格意義上講,北大生當街賣肉該與不該的爭論并不重要。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說:“不用說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為公例。”黨的十六大提出要把優秀的人才吸引到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中來,注重人才的全面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堅強的人才支撐。這是一種深切的人文關懷。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改變觀念,最大限度地發展人的興趣,挖掘人的潛能,振奮人的精神,讓每一個人都能在最合適的位置獲得自由、舒暢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