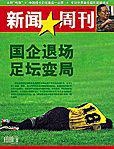誰掌控著國企進退球市?
張邦松 饒 勇

中國足球沒有形成真正的產業和市場,直接導致甲虛假繁榮和泡沫。
金錢的力量早已深深地滲透到足球領域中
經營足球俱樂部不是一項賺錢的“買賣”。但是這并沒有阻止后來國有企業大量涉足足球領域,因為除了國企領導個人或主管政府的偏愛外,他們還有個共識:搞足球可以獲得許多足球之外的利益
2月14日下午,成都全興大廈八樓茶莊,許勇坐在靠窗的位置上,面前是一杯熱氣騰騰的龍井,茶葉浮浮沉沉。
“我已退出足球江湖了。”這位原四川全興俱樂部的總經理說。2001年初全興集團退出足壇后,許勇似乎和當初轟轟烈烈的全興隊一起,從媒體的視線里消失了。
3年前也是在全興大廈的8樓,全興集團董事長楊肇基和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僅用了20分鐘就完成了轉讓談判,最終全興集團以4200萬元的轉讓了全興的足球資產,其中俱樂部作價400萬,訓練基地3800萬。據說,來遲一步的健力寶集團董事長張海聞知此事后,還曾后悔不已。
當時許勇已意識到國企的退出潮僅是剛剛開始。

只見錢去不見錢來
2000年開始,一些國企陸續退出綠茵場。表面看去原因不一。
2000年,前衛寰島(寰島集團是原公安部下屬企業)由于中央要求黨政軍(含武警公安)系統不得辦企業,必須與企業脫鉤,脫鉤后的寰島集團隨即對足球失去了興趣。兩年后,深圳平安的退出原因是新《保險法》第四章規定,保險公司的資金不得用于建設保險業之外的企業。
但更多國企退出足球場,還是由于在經營上出現了問題。
從1999年開始,全興考慮到經營形勢。當時全興集團董事長楊肇基覺得足球不能再玩下去了。他對身邊的人說,資金上的壓力很大,全興拿不出更多的錢來搞足球,否則連主業都要被牽連。
據了解,即使在1997年全興集團全面接管俱樂部時,全興俱樂部也沒有脫離“賠錢買吆喝”的局面。當時成都是全國聞名的“金牌球市”,全興俱樂部一年的門票銷售收入有1000萬以上,純收入在七八百萬元,加上電視轉播費160多萬元,以及球衣胸前背后廣告和場地廣告的收入,俱樂部各項收入總和大約為2000多萬元。
但在1998年以后,全興俱樂部的投入每年都在5000萬元左右。“因此俱樂部每年虧3000萬以上。”許勇說。
大名鼎鼎的紅塔隊也未擺脫經營困局。從2002年開始,紅塔集團開始進行多元化戰略收縮工作,作為集團下屬一個“只賠不賺”而且還是逐年加大投入的項目,足球成為集團高層多元戰略化收縮項目中的一個議題。
其次,2001年和2002年連續兩年甲A聯賽中,紅塔隊的表現都是起伏不定,使得原本剛剛升溫的昆明球市又慢慢冷了下來;同時,日益猖獗的假球黑哨讓聯賽的信譽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紅塔6年來為足球已經投入的數億巨額資金,沒有帶來多少回報。
2002年下半年,紅塔集團高層換屆,原總裁字國瑞離開紅塔集團前往云南省政協任職,紅塔當家人換成了姚慶艷(總裁)和柳萬東(書記、董事長)。新班子上任之后,紅塔最終選擇了“逃離”足球場。
國企紛紛殺入的初衷
奇怪的是,在甲A十年中途,已經不少足球俱樂部認識到它是一個不賺錢的“買賣”,但這并沒有阻止后來國有企業仍然介入足球。
1997年,紅塔集團總裁字國瑞決定投資足球,集團內上下一片反對之聲。但當地政府對此爭議項目卻非常支持。字國瑞最終一手促成了紅塔集團收購當時的甲B球隊深圳金鵬隊,轉而正式組建了云南紅塔足球俱樂部。
全興集團也是在那時加入足球圈的,它的領路人也是當地政府。“最初,全興也沒想過,要和足球沾邊。”原四川全興俱樂部總經理許勇說。
據本刊記者在成都了解,1994年,四川足球以那年甲B聯賽第四名的身份搭上首屆甲A聯賽末班車。由于參加聯賽必須以俱樂部的形式,當時四川足球隊的所有者——四川省運動技術學院希望找一家企業來出錢,一起組成一家俱樂部。而當時,四川省內實力較雄厚的企業當屬全興酒廠、成都卷煙廠等帶有壟斷性質的國有企業。
“省里分管體育的領導找到全興集團,問能不能把這個擔子接下來,當時的四川成都全興酒的廠長,即現在全興集團董事長楊肇基,聽了以后很快就拍板了,決定一年投入100萬和省運動技術學院共同組建俱樂部,簽了8年。”許勇回憶到。
盡管投入很多,但開始全興集團并沒有介入俱樂部的經營和管理。“實際上幾乎所有的俱樂部總經理都是體委系統的,這也證明企業介入足球帶有明顯的贊助性質。”許勇說,“而全興那時正處在上升勢頭中,想通過足球做廣告,作為一個宣傳企業的載體,只是獲得了冠名權。”
就這樣,國企在復雜的參與初衷下走進了足球場。是禍是福,中國足球之后的發展道路已有證明。
“這使得整個市場中的各類資源的價格和價值偏差太大。”遼足俱樂部總經理張曙光對本刊說,“一些國有企業花錢不心疼,他們會不擇手段地想贏,結果把整個足球市場都搞壞了。”
經營差不是退出的理由
沒有人會相信,紅塔集團會玩不起足球。它的退出有更深層的原因。
“紅塔集團目前面臨著經營和發展兩難的處境時,希望能夠借助政府給予一些優惠措施和政策來扶持球隊的建設和和發展。”云南足球界一位人士說,“作為國企的紅塔集團在退與不退之間,主要是看政府的態度。”
紅塔集團采取了一個投石問路的辦法,在12月初向省政府有關部門遞交了一份有關紅塔投資足球以來的總結式的報告。
報告中主要就紅塔集團6年來在投資足球方面獲得的經驗和教訓,以及存在的諸多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講述和總結,并向省府提出了一些自己今后的設想和建議。紅塔集團此舉的意圖就是想借“訴苦”而大造聲勢,尋求政府領導和有關部門在某些政策上給予支持和傾斜,以減輕企業的負擔。同時,也是在為一旦找不到較好解決方法的情況下留好退路,為“退出江湖”預留伏筆。
然而,政府方面對此事表現出來的態度打破了紅塔集團的如意算盤。在處理紅塔遞交的報告時,省政府的批復是,“建議紅塔集團繼續搞足球,報省委決定”,而在報告轉到省委后,省委方面最后給出的批復卻是“尊重紅塔集團的意愿”。
就這樣,這個沉重的“足球”最終又被踢回給了紅塔。
最后,紅塔集團只有選擇離開。
同樣,四川全興集團退出足球是政府態度的另一版本。
據說,全興集團退出足球緣于其向政府提出能否把俱樂部的稅收減免一部分但未果。全興集團自認為是政府把它帶入了足球圈,但自己經營上有困難時,政府方面卻沒人挽留。
“2001年9月,全興做了一個報告,談了經營上的困難,并說全興集團有退出的打算。當時分管足球的當地官員,并沒有挽留的意思。”許勇回憶說。
等到12月17日,全興俱樂部上下全傻眼了。當天《華西都市報》頭版頭條刊出,“全興決議退出職業足球”。許勇說,“后來知道是省政府里透露出來的消息,就這樣全興被動地退出了。”
沒有了政府的支持,在中國搞足球不僅是賠本生意,而且社會效益也要打折扣。
國企從進到出,對其本身來說也許影響不大。但他們的“運作”風格,卻對中國足球市場造成了影響。
虛假繁榮的“原兇”
2003年,中遠集團投資的俱樂部買進球員申思大約花了900萬元,這個價錢在中國幾乎都能養一個小俱樂部。“花這么大的價錢買隊員,為什么?一句話,不是自己的錢。”原沈陽海獅足球俱樂部總經理章健感慨地對本刊說。
“如果說早期在甲A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過程中,由于產業不成熟、市場不成形,在一定程度上還需政府扶持。那么到了后期還要靠政府推動,而不是通過市場的自然競爭,這很不正常。在國企強勢資金的支持下,甲A的虛假繁榮和泡沫得以支撐。”中體產業公司董事長魏紀中說。
90年代末,在強勢國企的進入,中國足球開始脫離“小本經營”的時代,足球成為金錢堆砌的游戲。
在本刊的采訪中,有業內人士認為,甲A的“泡沫”是從球員轉會開始產生的,而始作俑者就是“兵馬轉會”事件。1995年,黎兵以64萬元被稱為“天價”的轉會費轉會到廣東宏遠俱樂部,和他一起轉會的馬明宇身價則是42萬元。這被認為是炒高球員身價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之后兩年,隨著大量勢大財雄的國企紛紛介入足球,球員的身價和工資更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1996年甲A新貴松日隊以120萬元的高價買走了年事漸長的高洪波。
1997年,郝海東以220萬元天價轉會大連萬達。
1998年,彭偉國以235萬元身價再創紀錄,區楚良則以230萬元屈居第二。
在當時的轉會市場上,前衛寰島俱樂部無疑是一個“狠角色”,中國的足球開始出現花錢如流水的局面是從前衛寰島開始的。前衛寰島俱樂部的大股東是寰島集團,屬于中國企業500強之列。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前衛寰島把其他俱樂部的許多優秀隊員都籠絡到它的旗下,姜峰、高峰、符賓、彭偉國等都是那時候被其召入麾下。
圈內許多人戲稱,前衛隊是“錢喂隊”——依靠金錢的力量,在當年聯賽取得了第4名的驕人戰績。
“這就刺激了其它一些俱樂部,他們的理論變成了錢可以換來成績。遺憾的是,與此相伴產生了聯賽中的假球、黑哨,使得職業聯賽的關注度大大降低。”章健說。
中遠集團是甲A“燒錢派”的后起之秀。在2001年接手浦東隊(當時為甲B隊)后,中遠集團投入了大量資金。當年為了爭取升入甲A,球隊的贏球獎金是:在單場40萬元的基礎上連勝累積;進球獎金是每多一個凈勝球加10萬元,結果全年投入超過1億,在甲B聯賽中創下了紀錄,連甲A球隊都自嘆弗如。
升入甲A的第一年中,上海中遠也連出大手筆,分別以950萬和900萬購進祁宏和申思,創下當年紀錄。2002年,上海中遠再次加大投入,僅在引援方面就投入了3500萬。
與此同時球員的收入,也隨著俱樂部的投入水漲船高。
談到球員工資時,已參與中國職業足球5年的重慶力帆董事長尹明善對本刊說:“李章洙(韓國著名教練)親口告訴我,中國球員的收入是同等水平的韓國球員的三倍。”
韓國最近的世界排名是22位,而中國隊在國際足聯的排名,從1993年的37位下降到今年80多位。
“足球運動員的收入開始直線上升,但他們的競技水平沒能像身價一樣直線上升,反而促成了球員許多不良習慣,到現在都沒有恢復。”原沈陽海獅俱樂部總經理章健說。
“這是中國職業足球的瘟疫,瘟疫的溫床實際上是來自國有企業。”章健說。衡量一項體育運動市場化或產業化成功與否的兩大指標,一是競技水平,二是市場化程度。
從技術積累上說,十年來中國足球水平或許有提高,但談不上有質的飛躍。
其次是市場化程度。在足球聯賽創辦最初的幾年,球迷的關注、贊助商的熱情都空前高漲,如果以當時的勢頭發展下去,中國足球聯賽的前景將會非常可觀,但接下來的幾年,地方政府的強勢介入、黑哨賭球的大肆橫行以及足球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使得中國足球聯賽變得越來越畸形化和泡沫化,球迷和贊助商的熱情都受到極大打擊。
后五年與前五年相比,甲A的品牌形象嚴重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