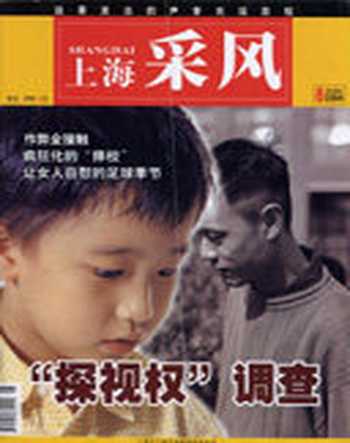成都新名牌之爭
王樹庭

一個城市的包裝可以是充滿了復雜的政治意味的理論過程,可以是充滿了人文意味的文化過程,也可以是充滿了經濟意味的營銷過程。成都,顯然屬于最后者。
一篇關于旅游開發的工作筆記
他反復強調他是個文人。盡管他寬大的局辦公室里進出著忙碌的人群,盡管他確實是中國基層科層體制組合體的重要環節,但他肯定喜歡文人這個身份帶給他的快樂:比如,說出話來,至少不像政府工作報告那樣謹慎;再比如,他有一圈文人朋友,大家的交流勝過了在官場上正經的交談。
另外的原因是,他在2003年的科學世界網絡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成為成都現在獲得“東方伊甸園”雅號的起因。他不愿意大家將他的官場身份和那個大名鼎鼎的成都新綽號聯系在一起。
因為他的堅持,所以,我們還是稱呼他為“子德”。那篇文章是他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的一篇作業《知識產權制度與科技創新》,作業中,他提出伊甸園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和母國,中國農業文明的三大發源地古蜀文明當得起伊甸園的稱號。因為老師說值得發表,他就投石問路似的貼上網。沒想到,一上網就引起了軒然大波,批判和稱頌的跟貼一直持續不斷。直到現在,大半年過去,子德還會在電腦前,每天進行例行公事似的檢查。“年輕一代稱贊的多,學者不贊成的占多數,但我覺得,這東西還是有學術價值的。”他嫻熟地操作電腦,在他這樣50多歲的領導干部中,喜歡上網的人群不是主流。
他的思考方式也不是主流。
實際上,真正刺激眾多成都人,包括他的,還是云南香格里拉成功注冊,當香格里拉縣涌入大量的游客時,他覺得那種包裝真是絕妙。“我們的成都總是稱呼自己天府之國,都有審美疲勞了。不像香格里拉,一舉成功。”他嫻熟地用著各種流行詞。
事實上,近幾年成都一直在努力地尋找著自己的新名片。甚至策劃過全國性的“尋找成都新名片”活動。
“其實當時贊成叫休閑之都的人相當多。可是有些老領導覺得光強調休閑,使人覺得城市沒有上進心。”成都市委的一位同志輕聲說。老早叫過的“熊貓之鄉”又怕被人誤會成都是深山老林斷然廢棄。當時還有大量的“某某之都”參加競爭,四字格式,層出不窮。包括我們聽來不合邏輯的“首善之都”都曾經出現過,并且被認真考慮過。結果是折衷的,現在,仍有些宣傳畫在成都街頭懸掛。青城山、峨眉山、都江堰的眾多畫面之中,是最后選出的三句話“多彩之都、休閑之都、成功之都”。
這場宣傳戰的暫時性結尾,也是高潮——巨款請來了張藝謀,他制作的成都宣傳片的結尾語“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成為這座優美城市最佳概括。可惜還是一句話。
子德當然一直也在這種潮流之中,當然,身為官員的他更能體會成都市級領導的意圖,這種包裝不是針對一般市民而言的,更多的是針對外面,或者說,外國旅游者、投資者的。目的就是喚起對成都的注意,“注意力經濟”直接針對那些有實力的而又陌生的人群。
子德的這篇影響巨大的關于旅游經濟的作業的主要觀點是:中國一支古人類起源于斯;山川、氣候適宜人們在此安居樂業;一連串古代的天文學家、文學家被他引用,作為文明燦爛的標志。看得出,他下了工夫,一般人甚少接觸的《巴蜀古史論叢》被他拿來引經據典,更少人看見的一本書籍《彼岸視點:國家地理雜志中國探險紀實》也被他引用,網上傳說此書不存在,他氣定神閑地翻開此書,“盜版的,所以很難查對。”
那里面是美國人羅林· 夏柏林發表于1911年的《登臨中國西部的阿爾卑斯》和約瑟夫·比奇發表于1920年的《東方伊甸園——中國西部》。在這兩個外國人眼里,中國西部是古老而又神秘的。他在兩篇文章很多段落下面認真做了記號,當然,最吸引他的,還是那句“東方伊甸園”的話,一句泛指的贊揚話。
他隆重地將成都平原作為“伊甸園”推介出來。他沒有想到,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迄今已經形成成都官員和一些專家們常規話語,幾乎背誦得出。
這篇作業掛在網上,也許是他那振振有辭的論點太過于肯定,反駁之貼迅速跟上,學者覺得他引用的文獻都不成立,一般人覺得他夸張,更多的人看熱鬧。“其實我是張揚天府文明的嗎,誰說伊甸園就是光屁股的男女?他們的理解有問題。”他有點憤然。“再說了,文章的落腳點是推廣旅游經濟,和學術有什么相干?”
其實,如果這只是一場網絡之爭的話,那一切就簡單了,每天有多少網絡論壇會起風波?沒有人說得清楚。
但是,這場風波一直波及到了成都市委。
一位領導的決策和一群專家的參與
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也是喜歡上網的,他看了網絡文章還不夠,要求子德將文章送到他的辦公室里。認真讀過之后,他覺得城市的新名片似乎有了著落。但是,他也拿不準,于是將問題交給了專家。
一個概念的討論開始牽涉到更多的人。
應該說,整個決策過程中還是尊重了專家的意見的。
十多位各行各業的專家在今年年初被召集開會,專門討論成都是否能被叫做“伊甸園”的問題,當時,很多人的反映和考古學者黃建華一樣,是“即驚且疑”的,覺得成都和“伊甸園”相隔何其太遠,“我們學考古的,發現那篇文章寫得很外行。”但他們很快發現,問題的實質不是文章的好壞,而是成都應該如何包裝自己,將自己閃亮地營銷出去。
“天府之國不是不能用,而是太老了,不好用了。”當這種話多次出現時,專家們發現自己的新任務其實是為 “伊甸園”這一名目尋找合理的推介方式,他們提出了“東方伊甸園”的概念,顯得比最初的提法合理;他們也提出成都是不是“東方伊甸園”,不應該由自己說,最好由外界人士來宣布;他們認清了政府的目的,是營銷城市,而不是尋找最合適成都的稱呼。
當然,也有不少專家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他們還是從學術角度提出種種質疑,很難在兩種專家面前判斷誰是誰非,因為,贊成票的投票人比較理解政府的苦心,反對派則始終將其放在學術范疇討論。
但是,“東方伊甸園”及其一套更完備的營銷理論被建立起來,關乎“東方伊甸園”有了種種完備的解釋,我們現在幾乎能在每個贊成“東方伊甸園”的人口中聽到那幾經論證的理論。
四川才子魏明倫的話也許最有代表性。當年,他的川劇《潘金蓮》同樣被眾多人圍攻,結果加上“荒誕川劇”的頭銜而過關。現在,以他的聰明才智,為“東方伊甸園”辯護再合適不過了,他覺得天府之國多幾張名片沒有什么不好,“誰的名片上沒有三四個頭銜?”他敏銳地認識到這是個經濟活動,而根本不應該是學術討論。“為了招徠洋人,叫個洋名有什么不合適?又不是說我們就此放棄老名稱。”

“我是中立派的。”他覺得叫這個洋名沒有負面效應。“伊甸園不就是皇道樂土嗎?誰說都是男女之事?伊甸園這個詞,誰能從里面看到什么是誰的事情。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性者見性,人性者見人性,這和魯迅當年評紅樓夢一樣。”很快,這些專家會上的論述成為贊成者解釋這一問題時的最好論點,確實有它的高妙之處。
達觀的他還說,把成都叫什么都不要緊,比如安樂窩,比如安逸之都,文采之都,成都都當得起,這位喜歡成都的人覺得成都的快樂很奇妙。
論證結尾,隨手拿來的例子,是周恩來將《梁祝》叫做“東方的羅密歐和朱麗葉”;葉挺送給郭沫若的對聯是“壽比蕭伯納,功追高爾基”,非常文人氣慨。
但另一句話不好聽。“學術的解釋是迂腐的。不要以學術的眼光來看現代社會。”
這位四川才子的話我們后來在多位專家口中聽到,很難說,這種“思想統戰”沒有合理性,正是他們的參與使得“東方伊甸園”的營銷理論成熟起來。一些先前反對的專家也開始擁護這項營銷工作,比如四川文藝出版社的林文詢,盡管他最初也是“驚疑”,但是最后舉雙手擁護。他的著作《成都人》中溫情描摩著成都人的達觀、聰明,現在他自己就是例證。“新鮮、響亮的洋名片沒什么不好。在現代化交流上,使用借代符號是聰明的。”他說。
一位美國來客
2004年3月,隨著一個美國人來成都尋訪“東方伊甸園”,這個城市營銷的計劃正式露面在市民面前。
繪聲繪色的成都媒體甚至精心設計了這樣的開場:一位焦急的空中小姐將這位尋找東方伊甸園的老人從機場帶到報社里,說明他的焦急是找不到近一個世紀前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文章中提到的“東方伊甸園”。
媒體當然現場跟蹤了三天。把這個美國人的形象推向人心,甚至街上的三輪車夫都認識了他。
從媒體的報道中,我們了解到了這樣一個故事:5年前,美國著名制片人比爾·愛恩瑞夫在近一個世紀前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看到了這兩篇描繪四川風光人物的文章,從此他就一直有一個夢,就是有朝一日能夠尋訪文章中提到的“東方伊甸園”。懷揣著這個夢想,他來到了成都,在這個夢中的城市生活了3天,尋找成都就是“東方伊甸園”的證據。3天的行程讓他確認,成都就是他尋找的東方伊甸園,并計劃今年晚些時候在成都拍攝一部1個小時的紀錄片,在片中講述證明成都是“東方伊甸園”的所有地方。
事實上,這樣的策劃來自市委宣傳部門。年初,市委宣傳部接到宣傳“東方伊甸園”的任務,一直在努力創意。他們像一家公關公司,必須拿出讓人一震的計劃,最后和專家一起想到通過外國人之口來訴說的合理性。
“自己說自己長得漂亮有什么意思?尤其是一個中國人,突然說自己長得像西方人一樣漂亮更不合理。”外宣處的宋敏雯處長,因為一直大力宣傳“東方伊甸園”,被人戲稱“宋伊甸”,她笑著說找到比爾·愛恩瑞夫還是通過她朋友的關系,好不容易找到這位看過當年《國家地理雜志》的美國人,他當時正在江蘇拍片,了解東方伊甸園的概念并且又想來拍片,效果非常之好。
他是個快樂而夸張的美國老頭,在布滿民俗擺件的皇城老媽火鍋店和真正的古人類遺存金沙遺址面前,他一樣快活得掉下淚來,有著旅游者的不辨真偽和合理的矯飾。
比爾的長項,不在做秀,而在于他在美國電視界的關系,能夠以較合理的價格將他拍攝的成都宣傳片在美國眾多電視臺播出,一段兩分鐘的宣傳片,在10多家電視網絡播出,費用只要10萬美元,比之張藝謀的拍片費用還要少許多。至于他的勞務費,按照“宋伊甸”的說法:“讓我們保持一點商業秘密好不好?”
比爾的有些話語夸張了點,他說:“如果一個地方被稱為‘伊甸園,一定和圣經的‘伊甸園有聯系。圣經中的伊甸園提到了高山、河流等,和成都的地理環境很吻合,這是我認為成都就是‘東方伊甸園的第一個證據。第二個證據是以精神為主。‘東方伊甸園這個概念一定與生命、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成都我也找到了這些。當我們談到‘東方伊甸園時,更多時候和神秘聯系在一起。當我們回顧成都幾千年的歷史時,有很多神秘的東西。現在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和幾千年前生活在這里的人看上去不是同源的,因為幾千年前的人們留下的文字和圖像我們不能理解。圣經中提到了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園,而被逐出的人必須靠汗水和努力來生存,同時他們始終有一個信念,要重返伊甸園。我感覺現在的成都人民也有同樣的想法,想與幾千年前的那段歷史重新聯系起來。”

3天的時間太短了。
種種生硬的對比的說法讓有些市民覺得過頭,包括市委宣傳部也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比爾還是比較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務,他的視角新奇的紀錄片沒有突出成都的美麗富裕,而是將眾多外國人的成都印象剪輯在一起,對于美國觀眾也許真正有效。
成都市委宣傳部已經通過審片。
但是,這位美國制片人和許多美國人一樣,大力做秀有點過頭,宣傳部沒有讓他說什么,一切讓他自由發揮,可他那沖上都江堰的茶馬古道,充滿蠱惑地揮手,說這就是三千年不變的古老伊甸園的鏡頭傳遞到市民家中時,不少人覺得他有點像“托”。
除了應邀而來的比爾,來到成都的還有16個副省級城市的黨報老總,成都在進一步炒作自己的新概念。他們最初的反映也是喜憂參半,但是,專家團用他們成型的理論,說服了這些專業的媒體從業人員。
一群商機的尋覓者
周小丁,四川康輝國際旅行公司總經理,西南地區唯一的全國特級導游。無論是在市委宣傳部眼中,還是他朋友心目中,都“是個很聰明的人”。是他,將“東方伊甸園”帶來的商業機會首先顯現出來。
首次聽到這一提法,是今年年初的專家討論會上,他說自己“一震”,川劇流行變臉,他覺得這樣在旅游上變臉非常合適。做為商人的他一直羨慕著“香格里拉”的“一舉成名”,現在的“東方伊甸園”應該更是身價百倍。
“那些研討會說實話沒什么意思。和伊甸園一一對比有什么意思?學者的討論和我無關。他們太矯情了。”他直截了當地說。
周小丁利用了康輝國際旅行公司在全國連鎖的優勢,說服北京總公司與成都市政府簽下“百架包機游”的合同,在一年之內,全國各地的旅行分社將組織一百架飛機的游客來成都,他們將享受市長晚宴的待遇。
第一架飛機從昆明起飛,成都市領導親自到機場迎接,晚上由市長為客人點菜,并且發表歡迎感言,為成都造勢。游客們上前摟著領導照相,不管是跟誰,端起杯子就碰——這種不常見的親民場面在成都發生,可以看出官員們的良苦用心。
事實上,康輝的整合手段非常之好,100架包機的任務在年初就完成了10余架,每完成一架的使命,就能從市政府那里得到1萬元的獎勵。最后將是100萬元。這也是成都市政府在目前最大的一項投資在“東方伊甸園”的項目。他們巧妙地利用到了旅行社的宣傳廣告功效,也許,去“東方伊甸園”的招貼正在眾多的城市墻壁上招搖。
“其實應用在旅游上,這名字再好不過了,與現在國際流行的體驗式旅游暗合。讓來了成都的人還想來。可惜,現在在國外宣傳得太少了。”本著職業導游的本能,他說。
“又沒有傷害到誰,為什么不這樣叫。”針對新名片,他這樣說。
也許,被傷害的人的聲音是不會被這位成功的商人所聽見的吧。
省外的商人也看到商機。陳逸飛,此次出現的面目應該是一位成功的商業運作人,但他是以“一個視覺藝術工作者”的身份,誠懇地對成都要打造成“東方伊甸園”這個創意,提出了兩點建議:“好的城市應該是一個好的視覺學院,如果讓到過成都的人們在很多年后,重提成都或成都的某個建筑時仍是津津樂道,這才是最高境界。”
陳逸飛看中了市中心的龐大樓盤熊貓城,他和該集團共同投資5000萬美金籌建“熊貓城—逸飛國際文化廣場有限公司”,開發的逸飛國際文化廣場,將打造為“中國西部的都市伊甸園”,與“東方伊甸園”的主題相呼應和配合,從視覺文化角度來說,給成都城市建筑文化形成強烈的沖擊力。
廣場將設立“逸飛畫廊”、“逸飛視覺空間”、“逸飛服飾文化展館”、“逸飛視覺學校”等,并將借助逸飛的文化資源,進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動,如年度性的“中、美、法時尚服飾展”、“戛納影視展”、“逸飛新品服飾展”等。
時尚的引入將賺走愛趕時髦的成都人的大批鈔票。
旅游所帶來的效益還沒有在成都顯現出來,但關于此的旅游計劃卻始終在操作之中,千年文化和現代城市的提法也確實讓人感覺到成都在進行著新的旅游資源的整合。
至于招商引資,對于有此弱項的成都來說,也許還有更長的路。不過,他們是寄望與知名度的增加會改變這種狀況。
一種未知
成都市政府事實上一直在調整自己的宣傳攻略,由最初的尋找新名片,到現在的將此名片當作眾多名片的一張,由改造式的運動變成了僅僅和旅游招商有關;由盲目對外變成僅僅針對西方游客,他們在調整中獲得成熟。
也許,過多少年之后,人們回望這段歷史,會發現那時候的東方城市還在以與西方某個名字聯系上而自豪,按魏明倫的話說:“這名字反映21世紀初的中國現狀。”
也許,過不了多久,這名字的缺陷會顯露,像“熊貓之鄉”一樣被放在角落里。
也許,這名字會流傳下去,會成為成都的別號。
但這一切也許,現在都還沒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