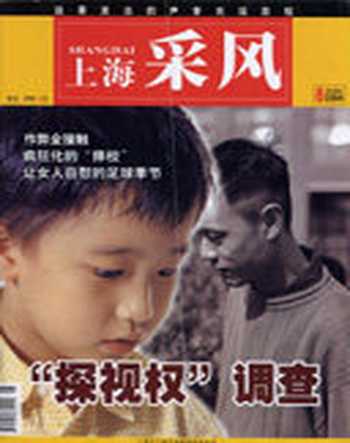是愛,還是害?

編者按:本期“案件聚焦”所選擇的兩個案例并沒有曲折的情節,案例一雖說是人命關天,但是兇手說實話也并非窮兇極惡之徒。案例二甚至法院都沒有給予立案。但是這并不就意味著這兩個案件是平淡的,它們同樣發人深省。值得我們在意和探討的是這兩個案件或者說所有與此相似的案件背后的原因,為何會出現往往一個所謂“好”的出發點卻總會導致一個壞的結果這樣的現象?為何明明應該是偉大的“父母之愛”卻最終成了“害”?這種“愛”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東西,自私?愚昧?或者還有其它?相信這兩個案件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案件一
高考生因“復讀”制造“殺人”慘劇
文、圖/千 華
2004年6月10日,黑龍江省阿城市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21歲的劉志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已經在看守所里呆了一年的劉志曾經學習優秀,家庭條件優越,在犯罪以前參加的高考模擬考中曾考出全市文科最好成績。但是他卻親手毀掉了包括女友生命在內的一切,這又是為了什么呢?帶著這個疑問,筆者在法庭宣判以后在看守所里和劉志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
被逼復讀
劉志的開場白是“爸媽非常疼我。”劉志說從小學到中學,他都是“班里吃得最好、穿得最好”的學生,特別是在考入省重點中學后,他更享受到了不菲的待遇。普通學生一個月300多元的生活費,他卻要花上1000多元——名牌服裝、耐克鞋,一日三餐吃飯店……而父母開出的惟一價碼是:“只要你成績好!”
“家里優越的條件,加之自己一直不錯的成績,讓我一直很自信,也很自負,總覺得前方的路一片坦途,一片光明,挫折與不幸肯定與自己無緣。”劉志說就是在這樣的心態里走向了2002年的高考。
但劉志也把以后發生的一切歸結于這次考試。當時劉志考出了490分的成績,完全可以被他所填報的哈爾濱商業學院本科錄取,可這樣的分數,卻讓篤信“兒子肯定上重點大學”的父母大失所望:“這不是你的真實水平,你應該再考一年”。父母冷冷地拋過來的這句話,讓剛剛走出“黑色七月”的劉志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壓力與寒意。“我太累了,不想再考了,再說去商學院不是挺好的嗎!”他曾試圖說服父母。“不行,有了今年的基礎,明年一定會考上重點!”父母的話絲毫不容質疑……家里曾經輕松和諧的氛圍,一時間被高考打破并陷入可怕的僵持中。一個星期后,劉志妥協了。“父母的態度我無法抗拒,同時我也知道他們是為我好。高考前母親曾放棄生意,悉心陪讀、照顧我3個多月。”劉志說,母親每天做好晚飯,站在門前盼他回來的情景他至今難以釋懷。
同年8月末,劉志在父母的安排下,轉到阿城市另一所高中開始復讀。之所以轉學,劉志說父母考慮到“一來是這所學校對像劉志這樣高分復讀的學生非常重視,在學費上給予了減免,更主要的是,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里,劉志不會再看到以前的老師、同學,也就不會覺得難堪。”
然而劉志說:“一想到厚厚的復習資料,周而復始的測驗、考試我就頭痛,甚至反胃惡心。我害怕進班級,更不愿和同學說話。”一向自信的劉志說自己那時就像個賊一樣,整天灰溜溜地,低著頭,背著大書包急匆匆而來,一聲不響地離去。喜愛的書籍被扔進了廢紙堆,籃球被扎破扔掉了;以前經常做的健身活動早已停止;他也不再顧及自己的衣著……復讀,如同一塊巨石壓在他的胸口,讓他很難透過氣來。
承受著巨大壓力的同時,劉志給自己繃緊的神經上足了發條:上完了一天的課后,回到在學校附近租住的房子里繼續學習,直到凌晨;5點30分起床,10分鐘洗漱完畢吃完早餐;6點鐘,準時坐在教室里……
“該死的高考,快來吧,別再折磨我了!”無人處,劉志不止一次地這樣歇斯底里地大喊著。“這次,我必須考上重點,否則沒臉見人!”喊過、發泄完之后,他還得機械地面對那些沒有一絲新鮮感的題目和試卷。
不堪重負
復讀4個月的時間里,盡管劉志的成績在全班一直遙遙領先,可絲毫沒有緩解他日益加重的心理負擔。“我真不知道自己還能熬多久?”有時劉志甚至一個月也不回家一次。難得跟父母訴苦,他們只會說:“兒子,咬咬牙,一年很快就會過去的。”父母根本不想知道他在想什么,自然無從知曉他心中的痛苦和憂傷,就在這種情況下,劉志和班里19歲的英語課代表柳瑩開始了初戀并發生了關系。對于這場感情劉志說讓他又重新找回了自信和久違的快樂,同時他還寄希望于戀愛能成為自己的一棵“救命稻草”,幫助自己走出復讀的陰影。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柳瑩曾與劉志約定,一起報考北大,如果不能一起考上,兩人就哪兒也不去!劉志說,盡管這是他們立下的誓言,可他心里清楚,以自己的實力考取北大仍沒有十分的把握,況且是成績較為一般的柳瑩。“如果我考上了,她落榜了,我該怎么辦?如果我們雙雙落榜,我又該怎么辦?”本已被復讀壓得喘不過氣的劉志又陷入這個矛盾中,心理壓力更重。為了排解心中的郁悶,劉志開始迷上了小說,特別是警匪類、暴力色彩濃厚的內容。劉志說當時《黑洞》是他最為青睞的一本,看了不知多少遍,每每讀完,心中都暢快淋漓。一種極端的想法,在他的腦海里漸漸占了上風:“活著很累,殺人很發泄。”
計劃自殺
在高考的最后兩個多月里,劉志心里的壓力達到了所能承受的極限。
2003年4月初,在高考前進行的第二次模擬考試中,劉志考出了624分的全校、也是全市文科最好成績。當時這樣的成績,讓父母、老師和同學全都欣喜異常:“照這樣學下去,劉志考上北大肯定沒有問題!”然而,所有人,包括女友柳瑩都沒有想到,這樣優異的成績非但沒有令劉志感到一絲一毫的驚喜,反倒讓他繃得太緊的神經突然崩斷了。 “那天,我獨自一人在宿舍里看著成績單時,突然莫名地煩躁起來,感覺累極了。晚上,想盡快入睡,可還是失眠了。一連好幾天都是那樣,越怕睡不著就越睡不著。好幾個晚上,我都在胡思亂想:考不好的時候,很累,因為要不斷地學習、忙碌;考得好的時候,還是累,因為隨時擔心被別人攆上,被別人踩在腳下;考上北大能怎樣,以后還得考研,考博……就在我感到疲倦的時候,一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多大的福我都享過了,也活夠了!這是小說《黑洞》里的主人公聶明宇的聲音,而我心底的聲音則是:‘這么高的分我都得了,作為一個學生,還有什么留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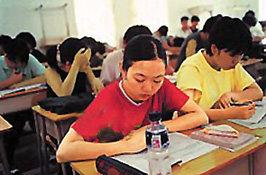
深陷痛苦的掙扎中,劉志最后萌生了“死了就解脫了”的極端念頭。從4月20日這天,他開始曠課,整天神情恍惚,終于決定一死,但他怎么也放不下自己的戀人柳瑩。
“我們倆的感情太好了,如果我死了,她肯定受不了這種打擊,不但會影響高考,一生也不會幸福;再者,我們第一次發生關系時,我就對她說過要對她一輩子負責……”想到這里,劉志開始有了更加荒謬的想法——和女友一起自殺,一起離開這個煩躁的世界……罪惡的念頭,他一直不露聲色地深植心底,讓女友柳瑩看不出絲毫破綻。與此同時,“雙雙自殺”的計劃卻在悄然地進行中……
臨死后悔
“兩人如果死了一個,另一個決不會獨自活在這世界上!”這是劉志“自殺計劃”的主導思想——先殺死女友,讓她在毫不知情中的情況突然死去,像睡著了一樣沒有痛苦;然后自己打開煤氣自盡。
4月27日,劉志專門打車到哈爾濱市買回了5大瓶乙醚,還在當地購買了大量膠帶和一個嶄新的煤氣罐。作案前,他一度猶豫,可這時另一個聲音告訴他:“做什么事兒,事前事后別想太多!”這是《黑洞》中二號反面人物張峰的一句話……在警方的訊問筆錄中,記錄著血案發生的前前后后。
“4月29日16時30分,劉志找到剛剛放學的柳瑩,騙她說他媽媽想見她。單純的姑娘既緊張又興奮,跟著劉志來到他的房間,等著與未曾謀面的劉母見面。這時,劉志拿出泡好乙醚的毛巾捂住柳瑩的面部,柳瑩邊躲邊讓他不要鬧。可是劉志一只手按住她的頭,另一只手狠狠地掐住她的脖子……直到女友的雙臂癱軟地垂了下來……”19歲的柳瑩就這樣走了,在全然不知中,她竟稀里糊涂地成了男友“自殺計劃”的犧牲品;來不及向母親、老師和同學們道別,更來不及完成那一張張空白的高考試卷……她走時,離高考僅有一個月。
把女友的尸體藏在床下后,正當劉志要打開煤氣時,同班一個來問數學題的女同學敲響了他的房門。因怕女同學發現真相,劉志將其騙到一處飯店吃飯。當他要返回時,接到柳瑩母親尋找女兒的電話。在隨后的五六個小時內,劉志若無其事地和柳母一起尋找、報案……打發走柳母后,劉志返回住所,用膠帶封住了窗戶和門,在午夜時分,打開了煤氣的閥門……
然而,劉志在女友“按計劃”死去以后,自己卻沒能“按計劃”行事,如今的劉志道出了原因:“煤氣開了兩個多小時后,我感到一陣陣眩暈、惡心,狂吐不止。但到了凌晨3點時,我還沒有死。在等待死亡的時候,我的腦海里突然涌出了柳瑩母親的形象。她尋找女兒時肝腸寸斷的情景讓我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到自己短暫的一生中,父母所付出的辛苦和期望……我后悔了,我覺得就這樣死去不值得,在昏昏沉沉中我關掉煤氣,睡著了……”
4月30日,劉志走進了阿城市公安局的大門,用他的話說:“如果我只顧及自己的父母,我會跑掉;之所以投案自首,是想給死去的柳瑩一個交待;我對不起柳瑩、她的母親還有我的父母,我的罪行不容饒恕,罪有應得。”
2004年3月12日,黑龍江省阿城市人民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將劉志提起公訴,6月10日,劉志被黑龍江省阿城市人民法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在看守所里,透過黑漆漆的鐵柵欄,身著沉重鐐銬的劉志,在淚水中向筆者坦陳了復讀給他帶來的種種苦楚,以及自己不堪重負而萌生“與女友一同離開這個世界”的心路歷程:“如果不復讀,我也許就不會產生殺人和自殺的邪念;如果不再參加高考,也許……”
“今年高考的重點錄取分數線是多少?”當筆者轉身要離去時,劉志突然一臉茫然地這樣問道……
案件二
女翻譯做“人流”引發“香火”官司
文、圖/西 川
一場車禍使已有身孕的女翻譯失去了丈夫,懷著遺腹子的妻子終日以淚洗面,悲痛欲絕。死者尸骨未寒,公婆和媳婦之間卻爆發了一場“保根大戰”……媳婦由于強烈的反感,也為了自己的將來和對孩子負責,最終到醫院做了“人流”。可是,“保根大戰”卻并沒有因為胎兒的消失而“停火”,相反卻愈演愈烈,直至把“戰火”燒上了法庭……
丈夫留下遺腹子
成都某翻譯公司工作的女翻譯何燕和軟件開發工程師向斌在2004年1月25日前,是世界上所有幸福夫妻中的一對。兩人才貌相當,自2003年夏天締結良緣后,兩人憑借自己的才華共同為了未來努力著,在短短的半年時間里,這個小家庭已經顯示出了良好的開端。
2003年年底,何燕和向斌用積蓄在環境優美的“濱河花園”購置了一套商品房,剛剛有了新家,何燕又發現自己懷孕了,可謂是“雙喜臨門”。尤其是何燕懷孕,不僅給小夫妻倆,更是給向家所有人帶來了巨大的喜悅,由于向家已經是兩代單傳,何燕的肚子承擔著給人丁單薄的向家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巨大責任。
向斌的父母得知兒媳已經有了身孕后高興得合不攏嘴,向斌的母親張玉英對兒媳何燕親熱得勝過親生父母,她不僅為兒媳買回各種高檔營養品,還教兒媳怎樣才能生下一個健康聰明的寶寶,因此婆媳關系非常融洽。由于小夫妻購買的新房剛剛裝修好,為了避免裝修可能產生的污染傷害到腹中的胎兒,向斌遂把父母接到新房居住,而他和妻子則還是居住在父母位于“聯合小區”的舊房里。人們全力以赴地期待著又一個“向家人”的誕生。至此,應該說一場皆大歡喜的人間喜劇已經接近了高潮。然而,正所謂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
就在2004年1月25日大年初四這天,向斌開著車回老家探望親戚,行車途中,突然一輛汽車和他迎面相撞,車禍在一剎那間發生了,向斌還未來得及和懷孕不滿一個月的妻子道別便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丈夫向斌的意外去世使得到消息的何燕當即昏厥過去。當好不容易醒來后,她在心里不停地責問:“為什么老天你如此狠心,轉瞬之間竟奪走我心愛的丈夫的生命?”向斌的父母也哭作一團,畢竟兒子是他們的獨苗,白發人送黑發人怎能不讓人肝腸寸斷!
何燕一蹶不振,精神恍惚,好幾天都茶飯不思。但當何燕想到自己腹中還有丈夫的親骨肉時,她也曾努力振作起來。當時她的確是立誓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來,讓親愛的丈夫的生命得到延續,也為兩代單傳的向家留下一個后代的。
保“根”大戰大婆媳之間爆發
在辦理完兒子的喪事后,向斌的父親向明星和母親張玉英在悲痛之余又開始有了新的擔憂,因為他們的兒媳何燕才20多歲,還很年輕。他們認為將來兒媳再婚是難免的,而兒媳腹中的胎兒是他們向家這一世唯一的“香火”,不管怎樣也得讓兒媳把孩子生下來,保住這條唯一的根,為此老夫妻倆經過商量,定下了“保根”計劃。
隨后,婆婆張玉英來到兒媳居住的“聯合小區”家里,以照顧何燕為名,日夜“陪伴”在兒媳的身邊。然而,婆婆的到來卻給兒媳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婆婆像“保鏢”一樣對何燕嚴防死守寸步不離,就連媳婦上衛生間,婆婆都要跟進去,所找的借口不是拿拖把,就是洗衣服,讓何燕感覺很不方便。
雖然何燕時刻盼望著婆婆能早日離開自己,回到“濱河花園”去,可是礙于過去一直和睦的關系不便開口,只能在心里寄希望于婆婆的自動離開。可婆婆卻一直沒有要走的意思。迫不得已,何燕只得對婆婆說:“我現在能照顧自己,您應該回去照顧公公!”
“你是有孕之身,我如果走了,你一個人,我放心不下,干脆咱們就一起回去住吧!”張玉英對兒媳說道。
“現在離‘預產期還早,我連上班都沒問題,沒什么不放心的!就是有啥事,我可以找我父母幫幫忙!”何燕回答。
張玉英不好再說什么,她一個勁地叮囑兒媳千萬要自己照顧好自己,然后萬分不情愿地離開了。
丈夫去世后,何燕一直沒有心情去單位上班。2004年2月21日,在家休息近一個月之后,何燕才到翻譯公司上班。然而剛到單位上班,公婆便走進了何燕的辦公室。
何燕很是詫異,忙問公婆有什么事情。公婆尷尬了好一陣后,解釋道:“我們是路過,順便上來看看你的!”但是這一“看”竟“看”了2個多小時,公婆卻絲毫都不見有離開的意思,何燕有些著急了,公婆的長時間辦公室“看望”不僅讓她無法工作,而且會在單位造成不良影響。無奈之下,何燕只得“實話實說”,希望公婆離開。婆婆見兒媳下了“逐客令”,隨即把來意和盤托出:“我們是希望你早點搬到‘濱河花園來住,這樣,我們也可以照顧你的生活起居!”為了盡快讓公婆離開辦公室,何燕連忙點頭,張玉英和老伴向明星這才步履蹣跚地離開了翻譯公司。
下午下班后,何燕走出公司大門,卻意外地發現公婆居然坐在街邊。見何燕下班了,公公和婆婆隨即笑吟吟地迎了上來。就這樣,何燕被公婆“挾持”著一起乘坐出租車前往公婆居住的“濱河花園”。即使在出租車上,公公和婆婆也把她夾在中間一起擠在后排座位上。回到家后的當天晚上,公公婆婆分居,無論何燕用什么方法,婆婆張玉英卻說什么也要和兒媳何燕同睡一張床。
由于有身孕,當晚何燕共上了3次廁所。可是,每一次她起床上廁所,婆婆都會跟著進來。婆婆的理由是自己人老體弱,有些尿頻。
直覺告訴何燕,婆婆張玉英所做的一切其實并不是如她所說的“照顧”,而是不折不扣的監視!何燕心里很不舒服,她真恨不得早點天亮,好早點離開婆婆!天剛蒙蒙亮,何燕沒吃早餐便匆匆前往單位上班去了。
下班時,何燕回到了“聯合小區”自己的家中。可她剛一到家,婆婆張玉英又風風火火地趕來了。婆婆說:“我打算住下來照顧你!”何燕沒有同意。迫不得已,婆婆向兒媳道出了她心里的擔憂,原來婆婆是怕兒媳為了自己的將來而打掉腹中的孩子,斷了向家的“香火”。婆婆對兒媳說:“你人還年輕,肯定是要再婚的,可不管怎樣,孩子是屬于向家的,你必須得把他平平安安地生下來!”
婆婆的話使何燕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怎樣也想不到婆婆張玉英竟然對自己如此不信任。
兒媳獨自去“人流”,公婆怒告斷“香火”兒媳
應該說在這之前,何燕對肚子里的孩子的命運并沒有想得太多,出于對去世丈夫的愛和懷念,她對這個遺腹子也是充滿期待的。但是公婆的所作所為卻“提醒”了何燕。已在丈夫去世的巨大悲痛中漸漸冷靜下來的何燕開始思考,假如自己生下這個孩子,孩子一生都將得不到親生父親的愛,他能幸福嗎?而自己現在還年輕,不可能就這樣守寡一輩子,倘若再婚,繼父會對不是自己親骨肉的孩子好嗎?但當何燕轉念想到向家兩代單傳,公婆巴望她生下向家唯一的“香火”時,她的心里又充滿了矛盾。
就在何燕在對待孩子的問題上不知何去何從時,婆婆最終還是在“聯合小區”何燕的家里住了下來。婆婆要求有身孕的兒媳別再去單位上班了,每天只管在家休息,由公婆按時給付她全額“工資”。考慮到翻譯公司還有不少工作要辦,而且對公婆的提議感覺很不好,何燕沒有同意。于是,只要何燕去單位上班,婆婆張玉英便隨即一路跟蹤,時刻提防兒媳去醫院打掉孩子。
2004年3月初的一天,何燕途徑省醫院時,在醫院門口突然遇見了在此工作的老同學。何燕和身穿白大褂的老同學站在路邊聊了起來。這時,跟在后面的婆婆張玉英見兒媳正和醫生說話,以為是在咨詢“人流”方面的問題,不由分說隨即上前把何燕拉開了。這件事后,婆婆張玉英對何燕加強了監視,她像影子一樣一刻不離地跟著兒媳,生怕一不留神兒媳就會去打掉孩子。如此行為讓何燕對婆婆產生了強烈的反感和厭惡,只要發現婆婆在跟蹤自己,她就會拼命想法甩掉她。婆婆的“鍥而不舍”讓何燕對婆婆的反感越來越強烈,婆婆無休止的監視使何燕時刻生活在痛苦之中。
2004年4月29日,眼看就要到“五一”節了,不少人都開始籌備外出旅游。何燕也準備和幾個朋友一起到都江堰風景區去散心。可是正當何燕準備外出的行李時,沒想到婆婆張玉英和公公向明星也開始收拾起行李來。老兩口對兒媳何燕說:“我們不放心你,今后你到哪兒,我們也去哪兒!”這句話終于讓何燕忍無可忍了,她想到幾個月來自己被婆婆監視跟蹤完全喪失了“人身自由”,她徹底憤怒了。她猛地朝兩位老人大聲吼叫道:“這是我的家,你們沒有權利住在我這里,你們更沒有權利干涉我的私生活!!!”
何燕的大聲吼叫使婆婆張玉英和公公向明星驚得目瞪口呆,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一向溫柔恬靜的兒媳今天會如此“潑辣”。經過一番權衡,為了不激化矛盾導致媳婦做出“過激”行為,也為了保證向家的“獨苗”不受到任何影響,婆婆張玉英和公公向明星沒有任何吵鬧,默默地離開了兒媳何燕的家。但是矛盾還是激化了,氣憤之下,5月3日上午,她獨自來到婦產科醫院,做了“人流”手術。
2004年5月7日,公公向明星和婆婆張玉英得知兒媳何燕已經到醫院做了“人流”手術,頓時氣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們當即跑到兒媳的家里,厲聲質問兒媳:“你為何不經過我們同意就私自去做了‘人流?”公公和婆婆接著還對何燕很明確地說:“你腹中的胎兒是向家的骨肉,你無權一個人處理掉腹中的胎兒!”躺在床上休息的何燕沉默不語。
回到自己的住處,向家老兩口想到費了這么大心思,還是沒有保住向家唯一的“根”,氣不打一處來,他們認為兒媳不經過他們同意就擅自做了“人流”,已經給他們造成了精神傷害。2004年6月8日,張玉英和向明星一紙訴狀把兒媳何燕告到了成都市成華區法院,要求何燕賠償精神撫慰金共計5萬元。
法院接到兩位老人的起訴后認為,按照《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7條第1款的規定,婦女有按照國家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因此,何燕的公公向明星和婆婆張玉英無權要求兒媳生下腹中胎兒,是否生育是她自己的事情。因此,法院最終沒有受理兩位老人的起訴。但隨著這場“保根大戰”的被迫結束,何燕和公婆的關系也從此無法挽回了。
編后 :
身陷囹圄的劉志在面對漫漫的鐵窗生涯和沒有自由的未來時,沒有為失去生命的女友和自己的人生掉眼淚,卻在時隔一年多后,想起當時的“恐怖復讀”依然淚眼婆娑。失去丈夫曾經發誓要生下遺腹子的何燕卻最終毅然打掉了孩子,并且將和丈夫一家的情緣徹底斬斷。我們當然無法斷言如果劉志沒有被父母逼迫復讀就不僅不會成為“殺人犯”而會成為一個人才,也無法肯定如果何燕的公婆沒有對兒媳如此“步步緊逼”,何燕就一定會生下孩子為亡夫傳宗接代,但至少我們可以斷定,事情不會發展到目前這樣不可收拾。
每個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無論這個人是年僅19歲的青年還是失去了丈夫的妻子。當然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能夠享受到他人的關愛和期望是一種幸福,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愛和期望可以左右或者主宰一個人的命運。當人們將自己的所謂“愛”和“期待”強加在別人的頭上并且強制別人接受的時候,與其說這是給予還不如說是強迫別人付出。這種“愛”和“期待”里便只有自私、愚昧、絕路而沒有其它,即使來自父母。
愿天下父母如此的“愛”和“期待”越少越好,如此人倫間的悲劇才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