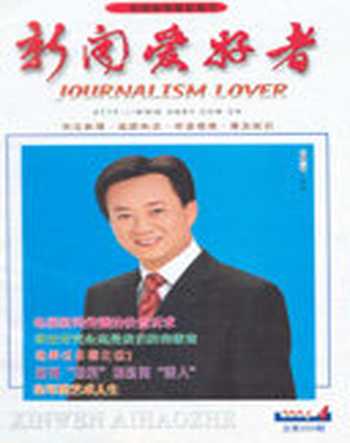法制報道中的悖論分析
徐 強 章敏輝
法制報道是新聞報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隨著法制報道的勃興,其中所掩藏著的矛盾也日益凸顯,它們往往以悖論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保障公民權利與侵犯個人隱私
我們的《憲法》和《民法通則》等有關法律法規(guī)明確規(guī)定,公民擁有實現(xiàn)相應的物質和精神方面需要的權利,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隨著群眾法律意識的加強和認識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越發(fā)重視。近年來,我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也正在向保護個人權利的方向傾斜,如允許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給犯罪嫌疑人戴頭套、個人的名譽和隱私依法受到保護等等,這些都反映了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進步。但令人遺憾的是,法制在向保護個人權利傾斜的同時,一些法制報道卻在侵犯個人隱私方面失衡,以至于造成新聞侵權。最近幾年,新聞侵害名譽權、隱私權、肖像權、榮譽權、姓名權、著作權的案件層出不窮,尤其是涉及侵害個人隱私的糾紛屢見不鮮。對新聞事件,公眾當然享有知情權,但在保障公眾知情權的同時,絕不能侵犯公民固有的權利,更不能以保障公眾知情權為擋箭牌,炫耀記者的采訪特權,把純屬個人隱私的事實公之于眾。
著眼證據(jù)翔實與賣弄犯罪細節(jié)
現(xiàn)代法制,講究證據(jù)的翔實和取證的嚴謹,對涉及量刑定罪的事實、過程、手段和證據(jù),必反復查證,務求真實可靠。但這并不是說法制報道就應當對犯罪過程全程實錄,甚至津津有味地渲染其細節(jié)。有些媒體為了片面追求新聞對受眾的吸引力,繞開犯罪事實中蘊含的嚴肅的社會問題,避開違法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性,強調感官刺激,把某些犯罪過程或手段作為“賣點”,不惜筆墨描寫暴力和性愛,描繪作案犯罪的細節(jié),格調日趨低級庸俗,甚至產生了青少年效仿犯罪等副作用,這與法制報道預防犯罪、懲治犯罪的終極目標背道而馳。
講究司法公正與制造媒體審判
為了維護法制的權威,司法必須體現(xiàn)嚴肅和公正,任何案件的審理和裁定都必須經過法定的程序,而執(zhí)行法定程序的必然結果,便是司法審判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滯后性。滯后性特點能夠讓當事人的情緒趨于平緩,讓大眾的思維趨于理智,能夠使各方注視的焦點從無據(jù)的猜測和過激的言行逐漸轉向事實和證據(jù)。但司法的滯后性特點往往與新聞傳播的及時性要求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當代新聞傳播對時效性和傳播面的苛刻要求使一些法制報道放棄了理性的思考,陷入情緒化的泥淖。一位資深法學家指出,“有指控而不容辯護的審判和報道,也許最能合乎‘正義的心情,但絕不合乎正義的程序”。但在當今媒體,合乎“正義心情”而不合乎法治精神的報道比比皆是,這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現(xiàn)象:“媒體審判”。有些案件在未經法院判決前就在公眾中形成了明確的意見。當法院的判決不同于輿論時,便會引起公眾的不滿,認為司法不公。馬克思在給阿爾諾德·盧格的信中談到,是“根據(jù)事實來描寫事實”還是“根據(jù)希望來描寫事實”,是區(qū)別“好報刊”和“壞報刊”的根本標志之一。當大眾傳播媒介把一定的觀點、態(tài)度、評價以仿佛獲得普遍贊同、代表大眾意志的形象來傳播給受眾時,絕不能忘記要在法制的框架內構建起受眾的價值評價體系。
法制報道中的悖論,是隨著法制報道的日趨繁榮而日漸顯現(xiàn)的。悖論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媒體從業(yè)人員缺乏一定的法律修養(yǎng),由于媒體沒有正確把握自身定位和職能,也由于新聞非理性競爭的壓力。悖論向受眾傳達的是含混的信息,給受眾帶來的是難解的困惑,倘若悖論長期存在,不僅會影響法制報道質量的提高,而且會成為受眾接受法制的意識障礙,必須尋找對策,化解悖論,達到和諧一致。
要在司法的他律和媒體的自律中尋求一致
社會學把新聞傳播看作是一種社會控制行為。新聞記者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在做社會控制的工作,“與軍隊、警察、司法機關所做的社會控制工作不同的是,他們不是在進行‘硬控制,而是通過傳播信息(事實與意見)對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施加影響,從而達到對社會進行‘軟控制的目的。”①既然如此,新聞記者本身就要依照一定的社會規(guī)范進行自我控制,履行一定的社會責任。新聞記者的自我控制要依靠兩種力量來協(xié)調,第一種力量是司法的他律,第二種力量是媒體的自律。媒體的報道,要在法制的框架內進行,法制報道更應以“法”為靈魂,絕不能跨越禁區(qū),擅入雷池。媒體也要在法制的框架內調節(jié)和規(guī)范自身行為,使法制報道在塑造自身形象、確認自身力量的時候,既體現(xiàn)出媒體的公信度,又體現(xiàn)出法制的權威性。該媒體挺身而出的地方媒體絕不能后退,該法律介入的地方媒體就應該客觀公正地退出,不能越俎代庖,干擾法律的執(zhí)行。
要在法理的揭示和心靈的感悟中尋求一致
法制報道的首要任務是揭示法理,讓受眾以法律為準繩,衡量報道內容和對象。但法制報道也需要深入受眾的心靈,撥動受眾的心弦,讓受眾通過報道感悟到法制的關懷。法制報道理應成為技術理性與人文關懷完美結合的有效載體。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過:“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xiàn)。”他又說:“公正不是德性的一個部分,而是整個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惡的一個部分,而是整個邪惡。”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在其著名的《法律篇》中說:“法就是最高的理性”,“當這種最高的理性,在人類的理智中穩(wěn)固地確定和充分地發(fā)展的時候,就是法。”采寫法制報道,就要以揭示法理為準則,選取典型事例和典型對象,不僅展現(xiàn)事件的過程,更要著眼于表現(xiàn)行為的動因,以過程吸引受眾的眼球,以動因打動受眾的內心,讓受眾通過心靈的震顫與法理產生共鳴,引導受眾求真向善,從而達到琴瑟和諧的理想傳播效果。
要在法制的剛性和道德的柔性中尋求一致
法律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強制力,人們稱之為合法的暴力,法制報道當無可厚非地突出這一特征。但法制報道畢竟屬于新聞傳播的范疇,新聞傳播的終極目標是讓受眾接受并引起反饋,如果新聞報道把法律的全部力量和威嚴僅僅寄居于法律的強制力,這種力量和威嚴只能讓人敬畏,卻不能讓人折服。展示法制的剛性必須以道德的柔性為依托,這樣才能讓受眾心悅誠服。雖然法律在一定意義和范圍上是嚴肅的、不通情理的,但只要透過這些表象,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各種法律原則背后都蘊含著巨大的人文力量,任何一個案件引發(fā)的深思并不僅僅是法律的啟示,而更多的是人文的追問。法制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guī)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而且,從司法實踐來看,今天的道德規(guī)范明天就可能變成法律的準繩。法制報道在讓人們體會到法制尊嚴的同時,更要讓人感受到道德的力量,只有二者互相聯(lián)系、互相補充,才能闡釋當前社會發(fā)展面臨的法制問題和道德困境,也才能真正拓展法制報道的表現(xiàn)潛力和發(fā)展空間。
要在法律的視角和社會的視野中尋求一致
法制報道首先應當姓“法”,以法律的視角觀察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分析法制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解答人們對于“法”的各種疑問。但法制報道既有法律屬性,又有社會屬性,要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必須將二者有機結合,缺一不可。法制報道倘若僅僅著眼于單一的法律視角,就有可能看不到自身在社會傳播框架中的正確定位,只有使之處于更加廣闊的社會多維視野中,處于不同視角的觀照之下,才能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中找到自身的坐標,體現(xiàn)出法制的價值和新聞報道的獨特魅力,才能在尊重公眾知曉權、盡量滿足受眾信息需要的同時,又準確把握新聞傳播的范圍、時宜和分寸,使新聞傳播真正有助于受眾正確地認識環(huán)境、認識世界,有助于社會的穩(wěn)定和進步。
注釋:
①程世壽、胡繼明《新聞社會學概論》,新華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