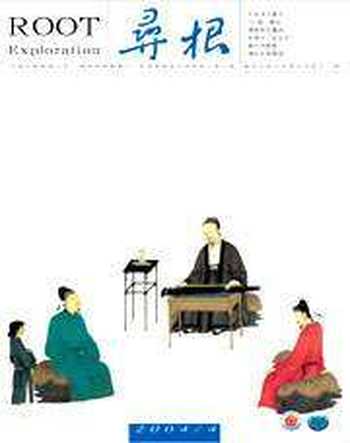解讀墨子思想體系的核心
公 振
墨子思想有沒有一個體系?有。這個體系,見于《墨子》的《魯問篇》: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君子,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這是墨子關于其思想體系的完整表述,由墨子的“十論”或曰十大政治主張組成。從以上這段話,我們知道,墨子的思想體系,是墨子本人所概括的,不是他的后學或后人總結的。這個體系很完整,包括政治、經濟、哲學、倫理、宗教、文化等等內容,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的綱領性文獻。這個體系,是一個實踐的綱領,有很強的針對性、實踐性、批判性和革命性。這個體系,是針對不同社會現實設計的,不是教條,是行動的指南,是結合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擇務而從事”。務者,要務也。即從緊要的事情入手。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這說明,墨家學派在理論的創造性和成熟性方面,要高于其他學派,而這一切又主要由墨子本人完成。因此,墨子的理論創造的貢獻,也當高于其他諸子。
關于墨子的十論,或曰十大主張,或曰十大綱領,是一個完整的整體,這是前輩學人所一致承認的。但是,說到墨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就不那么一致了。
復旦大學蔡尚思教授,有《墨子十大宗旨的主次問題》一文,主張大平等主義是墨子的中心思想,在這個大中心下,又以“兼愛”和“非命”為中心。對于墨子的十大宗旨,蔡尚思教授以為,又有“主要”和“從屬”之分,“兼愛”、“非命”與“尚賢”是主要的,其他則是從屬的。
我認為,大平等主義不是墨子思想的中心。十大宗旨在墨子那里是“一視同仁”的并列關系,是“大平等”,無所謂“重要”和“從屬”,只有“擇務而從事”。“兼愛”和“非命”也不是“大平等主義”的兩個中心。中心只能是一個,多中心就是無中心。兩個中心,肯定多了一個。蔡先生沒有找到墨子十大宗旨的中心。
梁啟超《墨子學案》認為墨學所標綱領,雖說十條,其實只從一個基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他認為,“非攻”是從“兼愛”衍生出來的,“節用”、“節葬”、“非樂”也自“兼愛”出。“天志”、“明鬼”是借宗教迷信來推行兼愛主義。“非命”則是人如果相信有命,便不會努力從事,所以要反對他。
梁啟超文章汪洋恣肆,語甚雄辯,影響甚大,但以兼愛為中心,則亦非中肯之論。蓋墨子若以兼愛為中心,則一兼愛足矣,何必十大主張并提?且以墨翟自言,兼愛與非攻排在最后一組,十大綱領中,兼愛位居第九,這與梁氏所說“兼愛”為惟一的“根本觀念”,差距太遠。兼愛為十大主張之一,不是墨子思想體系的核心。
南京大學楊俊光先生著《墨子新論》,以為墨子學說,就其本人在《魯問》篇所列舉以及門弟子記錄整理所成各專篇而言,主要是由“尚同”“尚賢”“非攻”的政治思想,“兼愛”的倫理思想,“節用”“節葬”“非樂”的經濟思想,“非命”“天志”“明鬼”的哲學思想所組成。政治思想是他的救世主義理論的核心和主體;倫理、哲學思想是他的觀點和方法。經濟思想則是一些具體的政策,都是為認識社會從而對之進行改造這個救世總目標服務的。在政治思想中,又以“尚同”為第一義,“尚賢”、“非攻”都是他的推衍。墨子是一位以救世為己任的政治實行家。
楊先生指出“墨學的核心”是其政治思想,我以為是正確的,但我認為十大主張是一個整體,應無第一第二之分,以十大主張中間的任何一項作為中心,或核心,都值得研究,應用“十論”以外的一個概念來表達墨子思想的核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譚家健先生在其《墨學研究》中,對墨子學說作如下評價:
如果以當代人文科學的分類概念來劃分,墨家學說是以政治學為綱領,以社會觀、哲學觀為指導,系統地提出了解決當時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倫理、哲學等許多問題的理論原則和具體措施。《墨經》則是邏輯學和自然科學著作。《備城門》以下各篇則是軍事技術及實施細則。
譚先生所論者,乃是整個墨子著作。關于墨家思想的特點,譚家健先生說,一、墨家思想是要求付諸社會實踐的行動綱領,不是只供空談的虛玄之學,無益之辯,有很強的實踐性;二、事事皆針對時弊而發,有確定的革故鼎新目標,有鮮明的批判性;三、淺顯明白,通俗易懂,是“賤人”之學。這是很有見地的。
南開大學哲學教授崔清田先生,有《顯學重光》之著,內專開“墨子學說的體系與核心”一節,對于“十論”的核心思想分“天、鬼”中心說、“兼愛”中心說和“義”為中心說以明之。
崔清田先生認為,“天鬼”中心說以郭沫若氏為代表。郭沫若認為,孔子否認傳統的鬼神,而墨子則堅決地肯定傳統的鬼神,這神有意志,有作為,主宰著自然界和人事界的一切……他的“天志”,即天老爺的意志,也就是“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規矩,這正是墨子思想的一條脊梁,抽掉了這條脊梁,墨子便不成其為墨子了。
崔清田先生認為,郭沫若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天、鬼”是墨子推行自家義事的工具,并非其思想的本質和骨干。墨子認為天有意志,天的意志就是所謂的“天志”。而這個“天志”不是別的,恰恰是墨子的意志。君不見子墨子有“我為天之所欲,天亦為我所欲”(《墨子·天志上》)之言乎?墨子以為“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儀法”(《墨子·法儀》),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墨子的結論是“莫若法天”。所以“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儀法”(《墨子·天志下》)。所以,“天志”就是墨子的意志,是墨子意志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已。“天志”之于墨子,只是一種工具。與其說墨子在“替天行道”,倒不如說天在“替墨行道”。“天、鬼”主要是適應墨子需要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派生出墨子思想的本源和骨干,也不是墨子思想的本質所在。崔清田先生的論證極為深刻。
關于“兼愛”中心說,崔先生作了歷史的考察,認為雖則近人俞樾、張惠言、梁啟超等認為墨子思想的實質或根本是“兼愛”,但其源卻是出于孟子。孟子曰“墨子兼愛”,“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此后,以孟子亞圣之尊,再借著《四書》之教,孟子之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于是“墨子兼愛”就被歷代儒士視為至明的真理,必循的玉條。但是,這種“兼愛”中心說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歷代有不少治墨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不少學者都認為“兼愛”在墨子思想體系中的地位是比較次要的。
“義”為中心說,是崔清田先生所贊同和主張的。崔先生認為,義是墨子學說的“核心”,是他的理想世界,也是他畢生奮斗的實踐目標。墨家對“義”的虔誠投入,執著追求,不為世人理解,以至被認為“有狂疾”(《墨子·耕注》),即今語神經不正常。
為了證明“義”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崔先生分別就“十論”與義的關系,作了簡要論說,認為:“尚賢”指的是施政治國時,人事上要尊賢用能。所謂“賢”,就是有“徒義”。所以“尚賢”實質上就是舉義。“尚同”即主張天下百姓的思想都要統一于他們的上司,并最終統一于“天”。天是有意志的,天意就是墨子的“義”。“兼愛”是“用義為政于國”在行為道德規范上提出的要求。“非攻”是用義“為政于國”在戰爭問題上的理論和措施。如果說以上四者是“用義為政于國”在人事、政治、道德、軍事等方面提出的要求,那么,“節用”、“節葬”、“非樂”三者就是在物質生活與經濟思想方面所提出的理論和措施了。至于“非命”、“天志”、“明鬼”,則是墨子出于推行義事之需,在宗教信仰方面提出的理論。
我認為,崔先生用“十論”之外的一個范疇,概括墨子思想的核心,無疑是正確的。對于“義”為核心也做了簡要的論證。崔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無疑甚為可取。而且也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墨家于義,有極嚴格的界定,“義,利也”(《墨子·經上》)。而兩千年來,儒家學派,定于一尊,關于“義”,習儒成是,已是思維定式。因此,在說到墨家的“義”時,一定要以墨解墨。而且,我認為,墨子書中,還有比義與“十論”更為密切的論述。關于最后一點,請容下文予以論說。
邢志第先生認為“國家百姓之利”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他說,墨子的最大特點是將國家人民之利作為其思想體系的核心、出發點和歸宿。墨子的思想內容很豐富,但都是圍繞著這一思想展開的。我認為邢先生的看法,已比較接近墨子思想的核心,惜乎他沒有繼續努力,而功毀于中途。
我的觀點是,墨子思想的核心,要從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張中去概括和提煉,應該統領墨子“十論”,而并非“十論”中的一項或兩項。表述墨子思想核心的范疇,應是墨子的原話,而不是現代人所賦予的。墨子思想核心應能在“十論”中的每一“論”中都體現出來。因此在我看來,墨子思想體系的核心,就是墨子反復講過的“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十個字。
墨子“十論”都是圍繞這十個字展開的。
墨子在《尚同》中說:
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
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圣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
不獨天子是天下賢良、圣知、辯慧之人,三公也是“贊閱賢良、圣知、辯慧之人”,左右將軍大夫,也是國之賢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一句話,從天子至里長,都是仁人,都是賢者。立各級正長的目的,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墨子說:
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逸也。維辯使治天鈞。”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錄,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
“為萬民興利除害”,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節語。
《墨子·尚同中》確有“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話,在“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之下,但世代傳抄訛誤成了“以求興天下之害”,大違墨圣本意。我在《墨子元典校理與方言研究》一文中,已校改為“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墨子》書這一段原文是:
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所以,墨子的“尚同”,是為了“一同天下之義”,是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兼愛中》開宗明義: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令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纂,人之與人之相賤,父子不茲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
由此,知“兼愛”自“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生,而不是相反。
墨子《兼愛下》,更反復論證之。如: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又如:
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
總之,墨子認為,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萬民衣食之所以足。這是圣王之道,萬民之大利。所以,我們說,“兼愛”只是墨家十為說,而將不可不察者也。
《墨子·兼愛下》曰: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也,于禹求焉。
顯而易見,“非攻”是從“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中衍生出來的。
墨子《節用》三篇,現存者,為上下兩篇。此二篇中,今不見“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十字全稱,但是《節用上篇》強調:
圣王為政,其發令行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財用不費,民德(得)不勞,其興利多矣。
這里的“興利多”,就是“興天下之利”的同義語。而在《節用下篇》,墨子更反復致意:
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王。
墨子節用思想極其輝煌,其自“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也是洞若觀火。
墨子主張《節葬》,《節葬》僅存下篇,其文不完,然而其中赫然便有“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個宗旨:
且(按:當作“是”)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
墨子還說:
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仁者將興之天下。
但是,如果“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在無法富貧眾寡,定危治亂,那么,他就是不仁不義,也不是孝子之事,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不僅如此,墨子還要求:
仁者將求除之天下。
墨子認為,衣食者,人之生利也;葬埋者,人之死利也。所以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也。
因此,“節葬”只是手段,而它的靈魂,仍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置天志以為儀法,遵道利民,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為行政,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墨子的天之(志),是度量天下萬事萬物的。因此也難怪有人把他作為墨家十大綱領的核心。然而,天志是墨子的工具:“子墨子之有天之(志),辟人無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墨子·天志中》)《天志》是為墨子的核心思想服務的:
故古有圣王,明知天鬼之所富,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為寒熱也節,四時稠,陰陽雨露也時,五谷孰,六畜遂,疾災戾役兇饑不至。
《墨子·明鬼》原有上中下三篇,今存下篇。《明鬼》下篇明確記載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個靈魂和核心: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為將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
因此,“明鬼”,只是落實“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手段。而在《明鬼》下篇結束的時候,墨子再次強調:
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
因此,《明鬼》自“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出,無可置疑。
《非樂》原有上中下三篇,今所存者,上篇。《非樂》上篇之始,墨子便書: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與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
可知“非樂”的出發點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至于“非命”,也是與“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緊密相連的。
墨子認為,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為的是“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三者無疑即天下之利,但是得到的不是富而是貧,不是治而是亂,不是人口增加,而是人口減少,亦即未見其利,而得其害。究其原因,乃是“執有命者雜于民間者眾”(《墨子·非命上》)。“執有命者”鼓吹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雖強勁何益哉?”阻百姓之從事,讓人民放棄努力,這當然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執有命者不仁”,于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所以,非命,事實上也是從“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個根本上發生的。
為了鑒別“命”之有無,墨子提出了“三表”,或曰三法。“三表”者,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他的本之者,指本之古代圣王之事,有似后代經典作家之言;他的原之者,指原察百姓耳目之實,這個是很有意義的,牽涉到百姓的社會實踐,但有所不足,不足之處在于他的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尚缺乏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制作功夫,所以有時得出的結論,并非全部是科學的。至于他的用之者,是“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墨子·非命下》),這第三表,是用社會實踐檢驗理論,很高明,特別是出現在距今2400多年前,尤其可貴。
墨子是貫徹實踐“三表法”的典范,他的鴻篇巨制,常常充滿著用“三表法”論證的范例。
針對“執有命者之言”,墨子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強聽治”、“強從事”的觀念。他說,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不危;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強必暖,不強必寒。所以,當《非命下》即將結束的時候,墨子大聲疾呼: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 ,不可不強非也。
所以,《非命》也是真自衍發于“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個總綱。
順便指出,這一大段中的“強”,是墨子故里魯山的方言字,讀qi ng,不讀qi ng,意為竭盡全力,不遺余力,十二萬分的努力,比現在人們常說的加大力度,還要過分一點。
以上,我們已考察了墨子“十論”中的九論,都是發自于“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個總綱,現在回過頭來,看看《尚賢》是怎么說的。
《墨子·尚賢》上中下三篇皆存。三篇無“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之名,而有“興天之利,除天下之害”之實。“尚賢”本身就是為了“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認為,尚賢是天鬼百姓之利,政事之本。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目的是“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所以國家要尚賢。賢者治國,“早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長官,“夜寐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所以官府豐富而財不耗散。賢者治邑,“早出暮入,耕稼樹藝,聚菽粟”,結果自然是:國家治理,政治清明;府庫豐實,萬民富有。國富民強,可以祭祀。對內則“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對外則“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所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萬民親之,賢人歸之。這難道不是天下的大利嗎?另外,于此順便指出,俞樾說這里的“將養”當作“持養”,是不對的。“將養”是墨子故里魯山地區一個方言詞。墨子書中“持養”皆應乙正為“將養”。
墨子《尚賢中》從反面論證了不尚賢的危害,他說:
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于貸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茍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矣。
那么,“不肖者在左右”則奈何可?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所罰不當暴”。其后果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所以,就引出一連串嚴重惡果:
入則不茲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背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強。
種種壞事的總和,必然是“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這當然是天下之大害了。
所以,“尚賢”,是墨子實現其“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總方針的人才戰略,組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