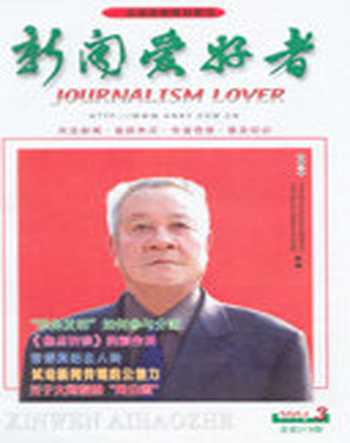“議程設置”與“新聞策劃”
張天定
新聞策劃是媒體運作中一項復合性工程,指的是媒體新聞編輯在新聞傳播過程中所從事的決策與設計性工作,以及對新聞傳媒活動的組織和管理工作。新聞報道策劃是新聞媒體對已占有的新聞線索、新聞資源按照新聞規律進行有創意的謀劃和設計,并制定出可行的報道計劃,使宣傳達到一定規模、一定層次、一定深度,并取得最佳的社會效果。
中國的新聞媒體作為黨的重要宣傳輿論陣地,肩負著神圣的政治任務和歷史使命。只有責無旁貸地致力于報道內容和報道形式的不斷創新,精心策劃組織,提高引導藝術,才能出色完成宣傳任務,形成良好品牌優勢。
我國傳統的新聞學理論從新聞報道的角度講,“新聞”作為事實信息,是由事實本體的存在及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新聞事件是不能人為策劃的。近兩年來國內新聞界圍繞新聞策劃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基本上肯定了新聞策劃的存在。
傳播學創始人之一的拉文認為,信息的傳播,由于一些規定或是某些“門區”的“守門人”個人的意見而流動。新聞媒體是受眾與外部世界的橋梁,人們對新聞事件形成的看法,大部分依據來自新聞媒體提供的材料,媒體解讀新聞事件的能力、制造新聞形象的能力是不言而喻的。
信息時代的人們面對狂轟濫炸的信息沖擊,要想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只好借助于新聞媒體對外界信息的過濾與篩選。從媒體的角度講,每日每時發生的事件不可勝數,把新近發生的事件都予以報道,不僅無必要,而且也不可能。這就需要媒體及時對新聞進行選擇處理,然后告訴人們哪些值得關注,哪些則不必費神。受眾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研究者認為:就物理視野和活動范圍有限的一般人而言,這種關于當前大事及其重要性的認識和判斷,通常來自于大眾傳播學中的“議程設置”功能。
“議程設置”是一種比喻的用法。其本意是經過安排的會議程序,喻為傳播媒體對所選傳播內容的次序排列與設置。作為一種理論假說,議程設置最早見于美國傳播學家M·E麥庫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輿論季刊》上發表的題為《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一文。其中心思想是:公眾通過媒介了解事件或問題,依照媒體提示的角度思考事件或問題。議程設置的目的基于兩種假設:之一即傳媒在改變人們的看法方面雖然效果不大,但它卻能夠成功地引導人們關注什么,忽略什么。這都是由于傳媒的把關人——編輯在起作用。媒體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何時報道,怎樣報道,無不圍繞著編輯預先設置的議程進行,它決定著新聞從選題策劃到制作發布的整個流程。表面上看,一張報紙或一本刊物,上面發表什么,不發表什么,發表在什么位置,用幾號標題等,純屬編輯業務問題,但決定這些問題的是編輯的編輯方針和策劃方案,通過編輯方針對報道定調、設定自己的議程,并通過這種方式影響社會公眾輿論。議程設置的另一假設認為,一個新聞信息在大眾傳媒中出現的頻率,是受眾賴以評價這個信息或議題的主要依據。傳播的頻率越高,擊中目標受眾的概率也越高,傳播的效果也就越好。媒介的這種影響輿論的作用,既可以是媒體的特征自然決定的,也可以用十分明確的意圖來引導。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不能直接得到的或本身較為復雜的信息,一般地需要依賴大眾媒介提供,于是大眾媒介無形中為人們建構著現實社會。2003年9~10月,《大河報》成功策劃了“客家遷移萬里尋蹤”的大型特別報道,在大河報的辦報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值得研究和借鑒。
客家是中華民族的一支特殊民系,史學家普遍認為,客家先民源自中原漢人,從西晉末年陸續遷移南方,逐漸形成漢民族中具有獨特文化、鮮明個性的族群,繼而再向海內外分散遷移。2003年10月26日,世界客屬第十八屆懇親大會在鄭州舉行,世界各地的客家團體云集中原,省親祭祖。2002年11月《大河報》的決策者聞訊后思考,拿什么奉獻給海天四萬里回家的親人。在近8個月時間里,他們多方采訪、查證,在2003年7月形成大型報道思路,決定派出特別報道組,從河南洛陽洛陽橋出發,途經安徽、湖北、江蘇、江西、廣東、廣西、海南等省區,在福建泉州洛陽橋終結,記者以進行式和集束式的報道方式,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隨時傳遞給中原廣大讀者。2003年9月24日,6名特派記者、2位特邀專家乘3輛越野汽車,攜8臺手提電腦,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特別報道行動。既追蹤了歷史,又記錄了現實。他們循著客家先民的遷移足跡,探索客家文化的脈絡。10月29日,更用了整整10個圖文并茂的版面,對懇親大會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集中強勢報道,給讀者形成強烈的視覺沖擊。第十八屆懇親大會的成功,《大河報》功不可沒。這次成功的新聞策劃活動也充分證明了只要我們遵循新聞策劃規律,精心組織,精心制作,完全可以打造出新聞精品,更好地發揮媒體的傳播效能。
但是,由于新聞傳媒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新聞“策劃”正在被濫用,其中一個典型的表現是策劃新聞。
《法制日報》2003年3月15日報道,因2002年在上海、南京等地鬧市街頭“怒砸空調”,當事人陳某等4人于3月14日分別被上海市奉賢區法院以損害商品聲譽罪判處有期徒刑并處以罰金。其中一名被告人是南京某報的記者錢某。錢某的主要行為是為砸空調者選擇了地點。本案中空調聲譽受損的程度和砸空調發生的地點以及此后的消息傳播范圍有直接關系。地點越是鬧市,傳播范圍越廣,聲譽損害顯然就越大。因此,從刑法學的理論上講,錢某的行為使其成了損害商品聲譽犯罪的共犯。錢某所受的指控和處罰給廣大新聞工作者帶來一個沉痛的教訓:在新聞傳播中,新聞從業人員只能客觀報道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實,千萬不能為了追求轟動效應而刻意“制造”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