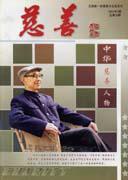孤殘兒的中產生活
潘 榮
大眼睛、童花頭,穿著一模一樣的白毛衣和白裙子,3個漂亮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撲向她們的母親,“媽媽媽媽,剛才有個叔叔說我們是3胞胎呢!”13歲的羅來歡一笑就露出兩個小酒窩,她有兩個妹妹來喜、來寶,還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
這是個快樂的大家庭,但不尋常的是,家庭成員之間并沒有血緣關系,6個孩子都是收養和助養的,并且都身有殘障。嚴啟倩喜歡孩子們叫她媽媽。她覺得只要做這些孩子的媽媽,就可以幫助他們。可是孩子們卻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與她“對抗”。
“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嚴啟倩、上海“新大地”酒吧的女老板,仰坐在皮質按摩椅上,黑著眼圈。來歡、來喜、來寶遠遠坐在桌邊,嘴里嚼著午飯,眼睛時不時瞟“媽媽”兩眼。
1998年,嚴啟倩把這3個女孩從兒童福利院抱回家,“她們身上多少都有些殘疾,所以只是進行家庭寄養,而不能收養。她們的監護權仍屬于兒童福利院。”
嚴啟伯和她們日夜相處了5年,“可我還是不知道她們在想什么。”她們的身體狀況,學習成績甚至品行,都沒有向著嚴啟倩希望的那樣發展。
更重要的是,她每天安排車子送孩子們上學,雖然學校離家只隔了3條馬路,而在母親節時,她們都不愿意在賀卡上寫些祝福她的話。她發現自己對孩子投入的感情愈來愈模糊,孩子回應她的感情也是同樣的模棱兩可。她覺得很累。
當初嚴啟倩和孩子的合影仍掛在墻上,甜蜜歡樂,神采飛揚,可是現在的她明顯地老了、憔悴了。她說她和孩子之間出現了問題。
一
嚴啟倩始終認定自己是在幫助這些孩子。
1998年,她是兒童福利院的常客。每隔三五天,她就會去一次。福利院里兩怖樓,一幢住的是健康的孤兒,一幢是殘疾孤兒。每次去,她就抱著糖果、餅干、衣服、鞋帽,在兩幢樓里奔上跑下。孩子們稚嫩地叫她“媽媽”。有時,她還會帶其他有錢人家的太太一塊兒去派發禮物。她知道孩子們在拿到禮物時是最快樂的。至少她小時候足這樣的。
嚴啟倩50年代末出生在香港,兄妹7人、家境很窮,晚飯通常足豬汕拌飯,想在飯里打個雞蛋,也常常湊不出7個。她10歲時父親去世,而在她記憶中幾乎沒有母愛的影子:“媽媽從沒有親熱地摸摸我的臉,讓我乖,聽活。她最疼的是老大和老幺。”
她的獨立性很強,自己決定,一切。20歲結婚、21歲離婚,和新男友去了美國。在她還沒來得及熟悉那片土地時,男友走了,留下她一人。
當時,她嬌咆迷人,喜歡自山,在美國6年,玩遍了歐洲。美酒、香煙和風情小鎮是生活的全部,直到她回到香港嫁給丈夫羅志明。1991年,她隨丈夫來到上海,日子迅速清閑起來。她可以每天花5小時去健身,每兩個月必須出國做一次短途旅游。
如果不足在1996年的平安夜,遇見那個沒有右手的10歲男孩,她可能不會成為這些孩子的媽媽。
當初,羅志明在—上海揚子江大酒店任部門經理。圣誕節,酒店和兒童福利院一起組織聯誼活動。晚上,大人、小孩一起唱詩。嚴啟倩拿著玩具逗引每一個小孩。她很快樂,直到她看見一個男孩拖著一只空蕩蕩的衣袖時,快樂猛地被抽空。
“他說想要—個媽媽。我忽然變得很傷感。我記得很清楚,自己小時候,媽媽都沒有抱過我一下。”后來,這小男孩成了她助養的孩子之一,她幫他取名為來福。每月,她會給來福100元零花錢。于是生活像是憑空多出了樂趣。她每周會帶兩三個孩子到家里玩,下周再換兒個。那些孩子都會叫她媽媽。兒童福利院一個班有30多個孩子,護理員很少,她對護理員說:“你們要是照顧不過來,我來照顧。”
二
1998午,羅志明與20多位香港、臺灣的朋友和兒童福利院共同建立了一個“愛心基金”,籌資100多萬元,專門用于救助孤兒。嚴啟倩則開始構建一個不同尋常的家庭,她要帶些孩子回家長期寄養。
最初她帶回了4個孩子。“羅先生利羅太太的經濟條件很好,而且也很有愛心。”兒市福利院負責家庭寄養的張先生說,所以才會在他們家寄養那么多孩子。這在上海是惟一的特例,通常一個家庭只能寄養1個孩子。而嚴眉倩最初的想法足要領7個孩子回家,她想組建山自己年幼時的那個家庭。
她放棄健身,減少旅游,開始用大量時間來照看孩子。為了有親近感,她把這些孩子的名字都改了,來歡、來喜、來寶、來來,4個名字里都透著祥和以及對自身的祝福。
孩子們跟隨嚴啟估住進了酒店,一個電話,服務生能幫助解決一切生活要求。家里的水果不斷,巧克力和玩具都是進口的。她們手上戴著日本手表,衣服都去“太平洋”買。
剛來的時候,她們都長得面黃肌瘦,每天,嚴啟倩安排她們服用維生素,還親自下廚煲排骨湯,幫她們補鈣。她忙亂的時候,雙手能同時炒菜,“八菜一湯,15分鐘搞定”。即使這樣,“孩子接回來的頭3年,還是一點個兒都沒長。就是現在,朋友的孩子和來歡同歲,但要比她高兩個頭。”
在兒童福利院,她們4個都被診斷是智力輕度低下。“來歡當初長得就像個鄉下孩子,臉是泥土般的黃、小眼、人也很內向。她現在13歲,比其他孩子大3歲,去年上4年級,今年和妹妹們一塊兒還上4年級。”
來寶和來喜都長著張漂亮的圓臉和一雙烏黑發亮的眼睛。但來寶腿上有血管瘤,病重的時候都沒法走,臉煞白,渾身不停冒虛汗,吃點東西就吐。“當初院里的人對我說,她是挺難養活長久的。”嚴啟倩知道,這樣的病更需要運動,就每天帶來寶運動,從最輕微的運動開始。現在來寶已經可以跑步、游泳了。
來喜顯然比她們都要好些,只是在左手臂上有一長條疤痕,10厘米長、微微凸起。“那是她小時候被人燙傷的。”夏天,她死也不穿短袖,誰要是動她,就尖叫,手緊緊捂著臂膀。嚴啟倩花了一年的時候解除來喜心理上的障礙。她說其實這個疤痕很漂亮,在上面添上兩只翅膀就像蝴蝶,這就像電視里美麗的人體彩繪,很時尚的。時間長了,來喜也信了。
來來有自閉癥。她不說話,見人只是傻傻地笑。在家會用頭撞墻,口渴了,到馬桶的水箱里找水喝。半夜,嚴啟倩被廚房里的動靜驚醒,以為是賊,亮燈后,看見來來趴在垃圾桶,撿里面倒掉的飯菜吃。
曾經有一對新加坡夫婦要帶來來回家,“他們也是我的朋友。在接觸了1周后,發現她有病,就不要她了。”嚴啟倩帶來來回家,她還記得,來來第一次叫她媽媽時,她有多開心,雖然只是啞啞的模糊的兩聲“媽媽”。
來來和嚴啟倩相處了一年,已經可以開口和人說話,而且很有禮貌,媽媽的朋友走了,她會輕聲說聲“拜”。“她只是自我的保護意識很強,其實另外幾個孩子也是這樣。”
嚴啟倩要去旅游了,把她們暫時送回兒童福利院。回來后,院里告訴她,來來已經被其他人帶回家了。“我也打聽過她的消息。聽說她現在讀書讀得很好。”
三
嚴啟倩除了3個孩子寄養在家,還有3個孩子助養在兒童福利院。每個月,花在這6個孩子身上的費用有1萬多元。“我妹妹說,有錢自己用不好么。那些孩子非親非故的,值嗎?”嚴啟倩說朋友大都不能夠理解,還有很多人在心理上會排斥她們,嫌她們臟。
嚴啟倩帶孩子們去朋友家玩。朋友的心就不得安寧,臉對著她,嘴在說話,眼神不停地掃那些孩子,“就像是在防賊”。吃飯了,他們不讓孩子們同桌,在邊上拼個小飯桌,隨便弄些吃的給她們。
有一次,去羅志明朋友家玩,“我們在別墅的2樓燒烤,孩子們在樓下玩。來歡去踩他們家孩子的單車,給大人看到了,就大叫大嚷地要把她趕走。”那種尷尬讓人難受。
朋友聚會時,燈紅酒綠的,孩子們顯得很局促,因為在現場總是沒人搭理她們。當有其他小朋友到時就會有人很夸張地扯著嗓子,“哎呀,Mary啊,孩子真可愛哦,多大了,上幾年級了?”這些,孩子都看在眼里。
到后來,朋友打電話叫羅志明出去玩,都事先申明,“孩子就不要帶來了,”等他們去了后發現,5對夫婦的孩子全在。
孩子們有時候說,“媽媽,今天在街上看見叔叔,他不理我。”嚴啟倩會告訴她們,“沒關系,即使他沒理你,你們也要叫他。至少你們不能沒有禮貌。”
通過這些孩子,嚴啟倩看清了很多人,很多這樣的朋友,他們再也沒興趣來往了。
但是更嚴重的問題慢慢出現了。
孩子們已經10多歲了,幫她們補習功課的楊孔清老師說,“她們真是該懂的一點都不懂,不該懂的什么都懂。”
楊孔清不久前把來寶接回家,讓她過過普通上海人家的生活,晚上來寶會和楊老師的女兒聊得很晚。她會說自己看到的豪華生活,人際關系,大人的穿著打扮。“我女兒已經進大學了,而她只有小學3年級,有些東西還是我女兒所不知道的。”楊老師說,“但她的閱讀能力簡直是一片空白。平時不做作業,會撒謊、吹牛,并把課本扔掉。”
嚴啟倩說,她們3人在一個年級上課,同一門課應該有3本書,讀到后來只剩下1本,“她們會對我說,老師沒發。”
2001年嚴啟倩接手新天地的一家酒吧后,她和孩子們相處的時間大大減少。最初的時候,每天從早上9點要工作到凌晨2點。“之前我也沒做過酒吧,我老公說我不行。”她把這視作挑戰。現在很多客人都喜歡她,覺得她很會琢磨顧客心理,而且酒量也好。為了應酬,她會拎著整瓶威士忌和客人周旋。
羅先生就更忙了。他換了一家酒店上班,需要他更拼命地工作。現在他每次去上班,孩子們都不會和他打招呼、說再見。對她們來說,他很陌生。
“孩子們愈來愈大了,有時候我真的很難理解她們的一些行為。”嚴啟倩說。她們會扔衣服、扔鞋子、扔書包,凡是她們不喜歡的,她們會統統扔掉,然后對大人說是掉了,沒了。“有段時間家里沒洗衣機,我讓她們自己洗衣服,她們就把臟衣服一件件扔到垃圾桶里。”
孩子們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嚴啟倩對抗。要她們洗頭,她們就把頭發用水淋一下。每回嚴啟倩都要聞過頭發上確實有洗發水味才能確認她們是真的洗過。臨睡前,她們說牙齒刷好了,可她發現牙刷還是干的。
嚴啟倩花幾千元買來的“小靈童”沖劑,“這是可以補大腦生長的。”她們會把它藏起來,或倒在馬桶里,然后說喝過了。
而讓嚴啟倩頭疼的還不止這些。
她們還會偷東西。從樓下超市,她們會偷各種各樣的小東西,吃的、用的。嚴啟倩發現好幾次,都讓她們送回去。有次讓她們去買東西,很長時間沒上來。嚴啟倩下樓找,發現她們被超市的保安抓住。
兒童福利院負責這幾個孩子監護情況的林小姐說:“可能她們以前在福利院玩的玩具都是公共的,拿來拿去很隨便,也成習慣了。或許并不是一種偷竊意識。”總之,嚴啟倩再也不讓她們獨自去超市買東西了。
孩子們的心,嚴啟倩是越來越看不透了。她們從不和媽媽說心里話。很多時候她們寧可和請來的保姆說,或是和楊老師說。有一段時間,她真想把孩子送回福利院,但是她們乖巧的時候又讓人心軟。她們會主動幫媽媽倒茶,會像大人一樣關照她在外面少喝些酒。
四
楊孔清,48歲,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她知道這個特殊家庭的情況后,直接打電話給嚴啟倩,想要提供幫助。接到電話時,嚴啟倩嚇了一跳,她沒想到有人的熱心能這樣直接。楊老師說,她的女兒曾經也走過彎路,不想看到這些孩子再走彎路。
楊孔清每周來輔導孩子兩次,科目包括語文、數學、外語,從7月9日開始,至今沒停過。她謝絕嚴啟倩提供的一切費用。
楊老師發現孩子們沒有學習的自覺性,心思不在學習上。“中產”的生活落在她們眼里,就是喜歡說些東家長西家短的事。看見美麗的媽媽出門,她們也開始涂指甲油和口紅。學校的暑假作業,她們一點都沒做。楊老師布置的一課一練也完不成,“其實也只有50分鐘的作業量。”楊老師說,“孩子的學習需要有人監督。”
她們的閱讀能力幾乎一片空白,在家不看報、不聽廣播。一次楊老師在改作文,語句不通順的地方用紅筆圈了出來。圈著圈著,孩子們的眼淚掉了下來。“哭得那個厲害哦。問了她們才知道,是怕媽媽看到有那么多錯。”她們說媽媽要罵的。孩子作業本沒了,也不和媽媽說,寧可不交作業。返校、開學的通知單,也都藏在書包里。
“如果在孩子的心理上多營造些親情感,情況或許會好些。”楊老師說。
嚴啟倩承認自己有時候脾氣不好。上午,她在睡覺,孩子不敲門就進屋來找媽媽,她會把孩子罵出去。“醒來后,我也后悔,會去找孩子們認錯。”來歡以前特別不聽話,嚴啟倩打她打得厲害。她又哭又叫,整幢樓都聽得見。“打完后,我也難過,為什么孩子就那么難管教”。她們會抱在一起哭成一團。
孩子們很明白相互之間以及她們和媽媽的關系,常常會有這樣的爭執,“我又不是你親姐姐,我為什么要幫你洗碗。”然后暗地里爭吵,媽媽喜歡誰多一些。
現在,楊孔清會給孩子們講“東方小故事”,告訴她們孟母三遷、孔融讓梨,指導她們的行為規范。家里只有《新民晚報》,她就讓她們看“夜光杯”,增強詞匯量。“她們對應用題的理解明顯有進步。作文也不像以前只是報流水賬。”
“但是孩子的教育三分靠老師,七分靠家長。孩子的將來,還要靠嚴啟倩對她們大長日久的教育。”楊孔清說。
嚴啟倩也發現,暑假里這兩個月,孩子們有很多變化。楊老師能讓她們按時交作業,她們一人有一個小豬儲蓄罐,每天能得到1角錢。以前保姆買菜問她們借1元錢,她們死活不肯。現在她們也懂得相互幫助,需要的時候也會主動拿出兩三元錢。暑期里她們的活動都是4人行,跑步、游泳、逛超市,“她們現在對關愛的需求很強烈。”
5年時間,使幾個陌生人的組合變成了一個融洽的大家庭,這種神奇的變化讓嚴啟倩、羅志明覺得特別有滿足感,“我現在明白家庭也是在慢慢成長的,讓整個家庭融合在一起的就是那種共同成長的感覺,這是一輩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