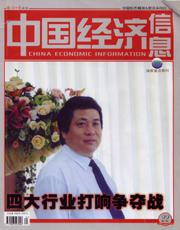紡織業遭遇“設限”
2005年中國紡織業進入了后配額時代,與其他各國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它或許成為一些企業的“入場券”,或許成為一些企業“最后的謝幕”——
“什么能賺錢?”“上紡織生產線。”
分布在上海、廣州、福建、山東的眾多棉花紡織企業近一段時期又掀起了一輪擴建生產規模的大潮。他們的這一舉動,為的是迎接2005年1月1日紡織品和服裝的進口配額的全面取消。按照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紡織品和服裝協議》(ATC)的規定,從明年1月1日起,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將不能使用進口配額限制我國紡織品進入其市場。從理論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大門向我們敞開。然而,“后配額時代”的到來,西方市場的大門真的是“敞開”了呢?還是關的更緊了呢?從目前種種跡象來看,中國紡織企業再闖 “后配額時代”的西方市場并不容易。
“中國威脅論”緣何而起?
“中國紡織品占領了我們的市場”,“他們的產品已導致我們30多萬工人的失業”——這些指責不絕于耳,在這些輿論的烘托下,“中國威脅論”出籠了。
日前,美國紡織業制造協會(ATMI)推出一份題為《中國威脅世界紡織品和服裝貿易》的報告。報告認為,配額取消之后,中國這類產品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到2005年時會達到44%,2006年將達到71%。報告還進一步推斷,中國的市場份額提高,也意味著美國的貿易伙伴的訂單會轉移到中國,而中國大約能從其他國家手中一共搶得至少420億美元。
美國的這份報告遭到了世貿組織的質疑。世貿組織濟研究部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中指出, 2005年后中國占世界紡織服裝市場的份額并不像有些人評論的那樣。根據世貿組織預測,配額取消后,中國占據美國紡織品市場份額將從11%提升到18%,占據歐盟紡織品市場的份額將從10%提升到12%。
中國的紡織業近幾年一直紅紅火火,在“配額”時代,中國紡織品的出口勢頭非常強勁。據海關統計,2003年中國紡織品出口額為788.7億美元,貿易順差632.4億美元。今年1~6月,紡織品出口額為416.3億美元,同期增長23.4%,估計全年的出口額在800億美元到850億美元之間。商務部的統計資料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據統計,中國紡織行業60%以上的收入來自出口。中國服裝及衣著附件的出口總值連續兩年維持20%以上的穩定增長,而2004年前三個季度,全國紡織品服裝貿易順差保持在26%左右。
2005年,中國進入“后配額時代”,西方發達國家認為我國是最大的“受惠”國,我國權威機構及專家學者也認為,在沒有新的“設限”情況下,我國的出口前景依然樂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供的分析報告顯示,配額取消后,只要各主要進口國認真執行紡織與成衣協定,中國原受限類別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額可能從2002年的78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50億美元。到2008年,中國紡織品服裝占全球的份額將比2002年提高6至7個百分點,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估計可達1000億至1200億美元,約占全球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的30%左右。
解讀以上數字讓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紡織品的“強勢”,但數字背后反映的卻是這個產業的“脆弱”。有關人士指出,中國紡織品的出口利潤靠的一是原料便宜,二是勞動力便宜。據世界貿易組織公布的世界紡織工人小時工資表明,中國紡織品勞務工資僅為0.69美元,是美國的4.85%,英國的5.42%,墨西哥的31.36%,土耳其的25.65%;在與鄰國的產業工人的工資比較一下,馬來西亞為1.13美元/小時,泰國為1.18美元/小時,我國勞動力成本比馬來西亞和泰國分別低63.77%、70.01%。
新的“設限”影響有多大?
山雨欲來風滿樓。2004年注定成為中國紡織品的“設限年”。
如果說,2004年初美國宣布對來自中國的針織布、胸罩及睡袍三類紡織品實施7.5%的配額限制,該限制維持一年時間成為“設限”的開端的話,那么,其后一連串的“設限”接踵跟來。6月,美國紡織制造商再次要求政府對明年來自中國襪子數量進行限制,將中國的襪子進口增幅限制在7.5%。他們的理由是,2001年來自中國的進口襪子不到100萬雙,而2003年則激增至2200萬雙,對美國襪子業造成很大沖擊。目前,美國政府已受理此案,但未作出最后裁決。10月,美國紡織品制造商,包括美國國家棉花總會在內的美國纖維生產商,以及美國勞工聯盟又發動“設限”攻勢,再次向美國商務部提交限制中國紡織品進口的13項申請,要求美國商務部在明年采取保護性限制措施,以強力阻止中國紡織品大量涌入美國市場。被申請的產品包括純棉和人造纖維褲子、羊毛褲子、純棉和人造纖維針織衫、純棉床單、棉紗、襯衫和內衣等,涉及金額近20億美元,占中國對美紡織品和服裝出口的近一成四。該申請還要求政府將去年對中國另外三類紡織品(針織布、胸罩、袍服)采取的“保障措施”限制再延長一年。
在美國的率先垂范下,今年3月,美國、墨西哥、土耳其等47個國家的90個紡織工業組織結盟發布《伊斯坦布爾宣言》,要求世貿組織將紡織品配額延長至2007年底。因理由不充分被世貿組織貨物貿易理事會否決。但由次帶來的負面影響仍在擴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國第二大紡織品和服裝的出口地——歐盟,今年6月中旬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第35類紡織品展開反傾銷,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紡織品遭遇到的案值最大的一次反傾銷調查,其涉案金額高達5.8億美元左右,被調查涉及中國企業近1000家。10月22日,歐盟貿易委員帕斯卡.拉米明確表示,鑒于中國紡織品和服裝在歐盟市場上的競爭力已經足夠強大,歐盟決定取消對中國紡織品和服裝的普惠制待遇。拉米解釋說,中國紡織品和服裝在歐盟的市場份額正迅速擴大,繼續享受這一優惠已“不公平”。據悉,歐盟普惠制每10年調整一次,現行普惠制將于2005年年底到期。目前,歐盟紡織品和服裝的平均關稅為9%,而中國相關產品享受比正常關稅低20%的優惠。
不僅如此,美國及歐盟即將再啟動“特保”條例,以“市場擾亂”為由,對中國紡織品進行“設限”。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文件(《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中國加入WTO工作組報告》)中,中國政府對“特保”作出過承諾。兩項“特保”的具體規定大致是這樣的:即一項是針對原產于我國的紡織品被稱為“紡織品特別保障措施”,另一項是針對原產于我國的特定產品被稱為“過渡期特定產品特別保障措施”。此兩項“特保措施”的含義大體相同,即若我國產品出口增長過快,對進口國的相應產業產生影響,進口國可采取單方面措施限制我國產品的進口。兩者不同之處,一是有效期限不同,紡織品特保措施將在2008年失效,而過渡期特定產品特保措施要到2013年才失效;二是最長限制期限不同,紡織品特保措施最長限制期限為12個月,而另一項措施則是4年。國家發改委研究部門的一位專家認為,中國紡織品真正貿易自由化的時間不是今年年底而是2008年,特殊保障措施條款的存在,為西方一些發達國家隨意“設限”大開方便之門,為中國的產品打入國際市場設置了壁壘。
紡織企業的“出路”在哪?
用“憂”大于“喜”形容2005年的紡織業,可能更恰當。
應該看到,中國紡織企業的“憂”在于“內功”不強。在出口增長的背后掩蓋著這樣的事實:企業生產規模小,產品技術含量低,時裝缺乏品牌,總體競爭力差等。
一位業內人士認為,進入后配額時代,中國紡織品仍將以低規模、低價格占有相當大的部分國際市場,招致受損國家實施反傾銷和設置種種貿易壁壘,但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紡織服裝企業至今仍沒有樹立起來打造品牌、提高品質和進一步完善職工安全健康保障等方面觀念,這些如果不改變,完全有可能直接影響到我們紡織服裝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喪失市場份額也再所難免。
還有業內人士指出,價格戰是國內最常用的競爭手段,也是慣用的招數,如果明年企業間繼續使用價格戰而沒有別的改變的話,只會導致兩敗俱傷,惡性競爭,進入無休無止的惡性循環,那么吃虧的不是他人而是我們自身。取消無配額后的“蜂擁而上”,帶來的可能會是一場“劫難”。
企業的“憂患”正是政府的“心病”,應對后配額時代的到來,政府開出一個又一個“藥方”。在剛剛結束的廣交會上舉辦的“紡織品‘后配額時代的發展與挑戰”論壇會上,中國商務部負責人明確表示,將最遲在今年12月10日前,出臺有關紡織品配額取消后的管理法規,以適應新的貿易形勢需要。10月13日,中國紡織行業在全國紡織科技技術大會上發布了《紡織工業科技進步發展綱要》,并提出要將行業發展重點戰略性地轉移到科技進步上來。《綱要》提出,到2010年中國紡織工業將重點突破28項關鍵技術,力爭在2020年使中國初步實現紡織強國的目標。
對此,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會長杜鈺洲認為,紡織裝備技術進步是后配額時代紡織業發展的源動力,只有全面提升紡織服裝業的裝備技術,中國才能從紡織大國向紡織強國邁進。杜鈺洲分析說,由于我國紡織行業發展的數量和規模已經很大,上升空間有限,產業需要尋求新的增長點。這個增長點就是提高產品附加值,而要提高產品附加值就必須依靠技術進步。從國外市場來看,我國紡織服裝產品出口數量持續增加,這種狀況不改變的話,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都將對我國紡織品服裝進行限制。這也逼迫我國不得不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使紡織行業朝著高技術型產業方向發展。杜鈺洲表示,進入后配額時代,中國紡織業只要加強管理、提高產品質量、著力打造知名品牌,就會有望在2020年成為現代化紡織業強國,使我國紡織工業的纖維材料、裝備技術、工藝與環保技術、信息化水平、骨干企業開發和管理水平以及品牌實力達到同期世界先進水平。
從以上政府傳遞的信息中不難得出:苦練“內功”是企業唯一的出路。正如中國服裝協會常務副會長蔣衡杰指出,紡織服裝行業的這種數量擴張型道路已被證明越來越難走,我們必須要改變增長方式,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