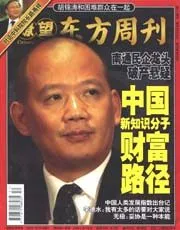國產品牌應將公關納入戰略管理范疇
屈紅林
此前很多跨國公司習慣性地認為,在中國出了問題,政府一錘定音就解決了。
2005年是很多在華跨國公司的多事之秋。從3月初“亨氏蘇丹紅事件”持續到近期的索尼“問題相機”,這些曾經是中國人偶像的跨國公司紛紛“走下神壇”。
在接連不斷的品牌危機中,跨國公司的危機管理為什么顯得如此脆弱?這些危機事件對日益國際化的中國企業有什么樣的啟示呢?
重新審視全球品牌
長期以來,跨國公司和跨國公司品牌在新興市場處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們不但是先進技術工藝(品質的保證)的代表,還是先進生活方式(個性與主張)的代表。與之相應,多數中國的消費者對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西方審美與消費流行思潮推崇備至。年輕的感性消費者對代表西方文化元素的商品趨之若鶩,理性的消費者對全球品牌的質量堅信不移,渠道對全球品牌不遺余力支持,政府和市場監管機構也對全球品牌信任有加……
這種文化上的絕對強勢讓跨國公司一度輕易地征服了新興市場的思想界、傳媒、監管部門和消費者,掩蓋了它們可能出現的諸多問題。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公眾的自我意識和文化信心逐步得到恢復。伴隨著“偶然事件”的發生,輿論從極度的推崇變為失望,最終變成對這個群體行為的整體關注和反思。這讓公眾更多地看到了“偶像們”早已隱藏的諸多問題,跨國公司開始支付企業聲譽被透支的代價,甚至出現對這個群落的集體批評。
跨國公司擁有科學的危機管理體系是一個傳說
“危機管理”一詞原本來自跨國公司,這個領域的引經據典原來幾乎都來自跨國公司。但在現實中,多數跨國公司的危機應對都顯得如此脆弱,難有作為。
從杜邦特富龍到寶潔的SK-II,皆凸現了系列缺陷:跨國公司的危機公關反應速度遲鈍、推卸責任、媒介輿論幾近失控、專家意見人士管理缺位、權威支持運用不當、社會心態判斷錯誤等等。
反觀中國一些本土大企業的危機處理,則不乏精彩之筆。如蒙牛針對競爭對手的對抗公關危機、創維的陸強華事件與最近的黃宏生被傳訊事件、海爾、TCL對質疑的反應等。他們的反應速度、媒介預警能力、輿論議題和方向的把控能力都已經遠在跨國公司之上,扁平快速實效的危機處理架構也超過了跨國公司的組織保障。
事實上,跨國公司擁有科學的危機管理體系僅僅是一個傳說。和本土企業相比,不少跨國公司一直是中國市場的寵兒,沒有面臨過這些企業經常面臨的惡劣生存環境和復雜的發展局面。很多國際大品牌和知名企業高層頭腦里,防微杜漸的風險意識越來越薄弱。
直到這次大面積危機之前,很多跨國公司負責危機管理的高層都是分管政府關系背景的,而不是媒體關系專員。因為,此前很多跨國公司習慣性地認為,在中國出了問題,政府一錘定音就解決了。
這樣的思維模式,10年前也許在中國行得通,但今天已經不是這樣。
建立高端公信力
但是,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同樣在提醒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本土企業一如果在全球其他地區的中國企業面對同樣的危機我們的表現能更出色嗎?
一種觀點認為,今年跨國公司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搞雙重標準,不尊重中國的消費者造成的,而中國企業在走向西方時不會存在這方面的潛在危機。
但事實上,盡管本土企業走向全球市場時可能“更加尊重”西方的消費者,但依然會因為雙重標準面臨更多的危機。
對大多數西方人而言,中國市場是不成熟的經濟體,不但消費者不成熟,連技術、標準、檢測方法甚至企業的公信力都不如西方。WTO談判時,美國代表甚至提出經過美國監測的肉制品在進入中國時不需要監測,理由是中國的監測肯定沒有美國嚴格。
在今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很多跨國公司一再宣稱他們執行的是“國際標準”,不少公司的聲明透露出這樣的言下之意:我們的產品在歐洲、美國、日本都沒有問題,在中國有什么不放心的。這種心態下,自認為自己代表先進,代表潮流才是關鍵,不尊重當地消費者導致危機只是表象。這樣的心態同樣會讓走出國門的中國企業面臨諸多的潛在危機。
所以,進入全球市場的中國品牌必須做好準備,必須為贏得認同付出更大的溝通成本和時間。
以輿論為中心
如果說跨國公司以政府為中心的危機公關已經落后于社會發展的步伐,那么中國企業在進入西方市場時更應該建立多重溝通的組織保障,尤其是與媒介輿論相關的溝通能力。盡管聯想、海爾、中海油等公司已經開始了建立海外媒介關系的嘗試,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家中國公司在海外成功地大規模運用輿論支持來獲得自己商業計劃成功,更不用說將公關納入戰略管理的范疇,全面建立起全球的媒介預警能力、疏導能力、議題引導能力等關鍵公關能力。
中國公司在西方市場遇到問題時,絕大部分精力依然用于政府主管部門的公關,比較忽視影響政府決策的輿論力量。韓國的三星電子曾經和中國企業處于同樣的位勢,但三星在美國輿論對自己不利時,大規模開展了和美國主流財經雜志的靈活合作,包括《財富》、《商業周刊》等媒體的封面文章不遺余力地大力傳播三星變革戰略的成就,成功地將三星塑造成為一家令美國主流商界尊重的企業。
進入全球市場的中國企業也應該開始著手設計讓全球財經界認同和尊重的策略,應該開始與國外的傳媒、專家、公關專業機構、企業信息發布機構等開展更多的聯系和交流。
(作者系GSA國際公關聯盟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