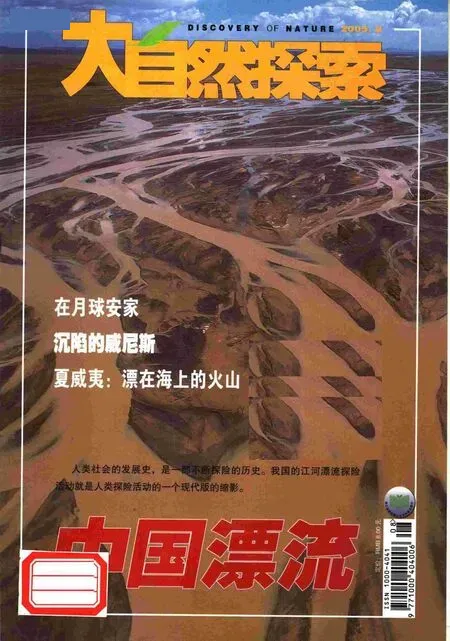喜馬拉雅雪豹
佛教信徒心中的神物
在中國西藏地區,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11世紀,有一位圣僧徒步穿越現在的珠穆朗瑪自然保護區,往來于偏僻的山村之間傳教修行。有一天,他不顧眾人的勸說獨自前往村莊附近一座山上的一個山洞閉門修行。那一年的冬天異常寒冷,連續下了整整18天大雪,通往山洞的小路被大雪封閉達6個月之久。村民們猜想圣僧可能已經遭遇不測,于是在來年春天到來的時候,結伙上山去搜尋圣僧的尸首。當他們離山洞還很遠時,就看到洞口有一只雪豹在吼叫,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消失。村民們心想,圣僧一定已經成為雪豹的腹中之物了。但是,當他們終于來到圣僧修行的山洞口時,卻聽到圣僧在歌唱。村民們大為詫異,問圣僧:“你看到雪豹了嗎?”不料圣僧回答說,“我就是那只雪豹。”原來圣僧已經修成正果,可以任意改變外形了,剛才眾人看到的那只雪豹就是他的化身。從此以后,生活在喜馬拉雅山區的雪豹就被當地的佛教信徒們尊為了神物。
在尼泊爾北部地區,也有許多關于雪豹的傳說。比如大喇嘛化身為雪豹前往西藏尋找珍稀草藥;放牧者被禁止在野外烤肉,否則山神可會派他的“護法神”(雪豹)加以懲戒。還有一些傳說中把雪豹稱為莊稼的“天然柵欄”,如果沒有雪豹牲畜就會肆無忌憚地覓食,甚至可能跑進莊稼地里。尼泊爾人還相信,投生為雪豹(以及家貓)是為了帶走前世的罪孽,因此誰要是傷害了這些動物,就會把它們前世的罪孽全數接收。在一些地方的村民的眼中,殺死一只雪豹所招致的報應遠比殺死像藍山羊這樣的動物要嚴重得多,因為雪豹終身捕殺獵物所累積的罪惡都會轉移到獵殺雪豹的人身上。
寂靜山林里的咆哮
關于雪豹的傳說令人著迷,但更令人著迷的,是這種美麗的貓科動物神秘難測的行蹤。
喜馬拉雅山脈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脈,綿延2400多公里,穿越印度北部、尼泊爾、不丹以及中國西藏地區等。“喜馬拉雅”這個詞是梵語,意為“雪屋”。在喜馬拉雅山冰雪覆蓋的山坡和峽谷地帶并非樂土——在高海拔地區,山上終年積雪,氣溫基本維持在零攝氏度以下;在海拔略低的地方,即使是夏天也非常寒冷,一片荒蕪,土地貧瘠且多為巖塊。由于山勢阻擋導致成雨云被阻滯,在許多地方形成高原沙漠。然而在環境如此惡劣的地方,許多韌性極強的民族世代繁衍。雪豹出沒的地區恰巧是喜馬拉雅地區三大主要信仰(佛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交匯的地方。
喜馬拉雅地區的印度部分是經幡飛舞的佛教信仰區域,這里的民眾對生命有著天然的敬畏,因此很樂意參與雪豹的保護行動。這里的人過著且耕且牧的生活:農耕時節他們在地里種植大麥、小麥和豆類植物,并在海拔相對較低的地區栽種果樹;同時他們在牧場放牧牦牛、綿羊和山羊等牲畜,并利用特有的羊絨進行紡織。平常男士大都穿著黑色長袍,女士則穿著色彩鮮艷的服飾。而每逢結婚這類的喜慶場合,所有人都會盛裝打扮,載歌載舞聚集一堂,暢飲青稞酒以示慶祝。千百年來,這樣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續著,沒有太大的變化,所有生活在這里的人們都把“雪屋”視為自己真正的歸宿之地。
人們對這個與世隔絕之地的了解得益于20世紀70年代拍攝的一部記錄片《寂靜的咆哮》,而這部片子也間接影響了來自巴哈馬群島的攝影師米歇爾·科尼。科尼偶然在一本書上看到追蹤雪豹行跡的種種艱難,于是很想親自試試。恰巧不久他收到前往喜馬拉雅地區拍攝一部電影的邀請,于是他來到這里并嘗試將一些前衛的拍攝手段應用到雪域地帶的實地拍攝,特別是運用紅外線遠程攝像機拍攝雪豹夜間活動。
1999年平安夜,科尼的攝制小組拍到一只野生雪豹的活動片斷,這令大家頗為興奮。盡管拍攝效果不佳,但說明只需稍加調整,這一技術能夠得以運用。此后。這個攝制小組對野生雪豹的活動進行了累計長達28小時的實地拍攝,獲取了豐富的影像素材,同時吸引了充足的制片資金。
在科尼的跟蹤拍攝經歷中,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雪豹求偶和交配的場景。這種場景在此之前不曾有人拍到過。當地流傳的說法是,雌性雪豹跳到河里與雄性水獺交配并產下幼崽。為了求證,科尼查閱各種資料,了解大型貓科動物特別是擅長單獨行動的大型貓科動物的所有求偶習性,又組織了一個專業團隊對雪豹進行追蹤。
一天下午接近黃昏時分,攝制小組在距離營地數小時步程的懸崖峭壁處看到一只吼叫的雌性雪豹。次日凌晨小組摸黑趕到那里,卻發現這只雪豹已經吼叫著爬到半山腰處。直到距離天亮還有大約20分鐘時,它才停止了吼叫。此時借助拂曉的微弱光亮,人們看到雌豹躍身跳入溪谷地帶消失了。在隨后幾天當中,雌豹每天早晨都會吼叫數小時。到第五天早晨,攝制小組發現這只雌豹突然不叫了。正當人們不知是福是禍之時(雪豹不叫可能是已經離開,也可能是已經找到伴侶),科尼看到高處微暗的天空背景上映出的剪影——兩只雪豹緊挨在一起,說明它們正在求愛。通過攝制小組的通力協作,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野外拍攝到雪豹交配的實況,從而破解了雪豹繁衍之謎。
大山不可或缺的裝飾
目前,雪豹已成為瀕危物種,這主要與非法獵殺和皮毛交易等緊密關聯,由于雪豹的骨頭、身體各部分可作為傳統醫藥的珍貴藥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非法盜獵活動的猖獗。此外,獵物數量的減少、牧區過度放牧、當地村民缺乏保護雪豹的自覺意識、雪豹棲息地退化或遭到人為分割等也無一例外地逐漸將雪豹逼上了絕路。雪豹的保護迫在眉睫。
羅德利·杰克遜,當今世界頂尖級雪豹專家,出生在非洲津巴布韋,20世紀60年代到美國攻讀學位,希望學成以后回家鄉為野生動物保護事業奉獻終身,直到有一天他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第一次看到雪豹的圖片,從此他暗下決心有朝一日一定要親眼看看雪豹。
1975年,杰克遜來到尼泊爾境內一個非常偏遠的雪豹棲息地。當他第一次看到棲息地留下雪豹捕食的行跡時,就意識到必須采取恰當的挽救措施避免雪豹滅絕,盡管當時還沒人明確知道該如何開展拯救行動。上世紀80年代初,杰克遜率領一個專家小組花費4年半的時間初步建立起雪豹的無線電追蹤系統,為日后研究奠定了基礎。
專家小組發現,雪豹可以通過若干有趣的方式與伙伴共享同一片草場,同伴間甚至不必見面。為了交流,它們會在巖石或地上留下刮痕,以便讓同伴了解自己的行跡,便于輪換相應的活動區域實現共享。杰克遜小組發現,雪豹數量最集中的地區可能達到每100平方公里范圍內有10-12只雪豹。令科學家著迷的是,在密度如此大的情況下研究者仍然極少看到兩只雪豹在同一區域同時出現的場景。
在多年雪豹保護工作中,杰克遜認識到,生活在這片棲息地的各種物種的未來在一定程度上與當地民眾息息相關,只有喚醒當地民眾的保護意識才能真正實現對雪豹等動物的持續保護。
要使當地民眾自覺加入保護雪豹的行列,首先要改變雪豹給他們的不良印象。一般情況下,雪豹被普遍視為神物,但有時它們也可能闖入牧區構成危害。牧場圍欄可以把牲畜圈起來,卻無法抵擋野獸的襲擊,因此一旦雪豹在夜間闖進圍欄,就可能使牧場主人損失30—100只牲畜,這對他們而言無疑是一場災難。眼下動物保護組織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雪豹與當地居民之間的沖突局面轉化為某種共存局面。首先,他們計劃幫助當地牧民修建不易被野獸破壞的畜欄。一旦新畜欄搭建好了,牧人就可以放心回家,無需在夜里睡在圍欄外冰冷的地上。據統計每一處新型圍欄的修筑至少可以拯救5只雪豹的性命。
當然,新型圍欄無法解決全部的問題,因為雪豹在野外還是會捕殺牲畜。因此動物保護組織的工作人員還要盡力幫助當地居民增加收入,比如開拓自然觀光的旅游業務,通過組織游人到老鄉家留宿,或培訓當地人充當向導帶游客一起追尋雪豹行蹤等。由此獲得的經濟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勵當地居民自覺保護雪豹。
事實證明,這樣做的結果極大地改變了當地居民對雪豹的態度。最初,雪豹在印度被村民們視為兇殘的肉食動物,而現在更多人發自內心地認同:野生動物的確是“大山不可或缺的裝飾!”科學家驚喜地發現近年來雪豹數量在保護區得到穩定增長,平均每100平方公里范圍內已經有大約8只雪豹活動。
但總的說來,目前雪豹的情況仍令專家們喜憂參半,畢竟局部好轉不代表整體轉變。目前雪豹的行跡遍布12個國家,它們大多分布在人煙稀疏的偏遠地區。而在那些地方,貧窮的人們為了獲取珍貴藥物不惜獵殺雪豹獲取豹骨等,因此雪豹的數量正逐漸減少。但雪豹保護工作者們相信,通過努力雪豹一定會受到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