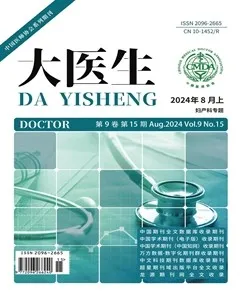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聯(lián)合獨(dú)活寄生湯治療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的效果及對患者膝關(guān)節(jié)功能的影響




【摘要】目的 探討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患者接受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聯(lián)合獨(dú)活寄生湯治療的效果,為臨床提供參考。方法 選取2020年6月至2023年6月宜章縣中醫(yī)醫(yī)院收治的100例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患者的臨床資料進(jìn)行回顧性分析,根據(jù)治療方法不同分為對照組(行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治療)和觀察組(行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聯(lián)合獨(dú)活寄生湯治療),各50例。比較兩組患者治療效果、膝關(guān)節(jié)功能、炎癥因子水平和生活質(zhì)量。結(jié)果 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患者整體療效更優(yōu)(Plt;0.05)。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C反應(yīng)蛋白(CRP)、白細(xì)胞介素-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水平均低于術(shù)前,且觀察組均更低(均Plt;0.05)。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美國特種外科醫(yī)院(HSS)膝關(guān)節(jié)評分和Lysholm膝關(guān)節(jié)評分量表(LKSS)評分高于術(shù)前,且觀察組均更高(均Plt;0.05)。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關(guān)節(jié)炎生活質(zhì)量測量量表2- 短卷(AIMS2-SF)評分均高于術(shù)前,且觀察組更高(均Plt;0.05)。結(jié)論 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聯(lián)合獨(dú)活寄生湯治療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能獲得滿意效果,能改善患者局部炎癥反應(yīng),提高關(guān)節(jié)功能和生活質(zhì)量。
【關(guān)鍵詞】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獨(dú)活寄生湯;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膝關(guān)節(jié)功能
【中圖分類號】R68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2096-2665.2024.15.0101.03
DOI:10.3969/j.issn.2096-2665.2024.15.034
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以膝關(guān)節(jié)軟骨退行性改變和骨質(zhì)增生為主要特點(diǎn),可引起患者關(guān)節(jié)疼痛腫脹,隨著病情進(jìn)展,可導(dǎo)致關(guān)節(jié)功能障礙,嚴(yán)重影響患者生活質(zhì)量[1]。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作為一種新型微創(chuàng)手術(shù),具有切口小、創(chuàng)傷小、恢復(fù)時(shí)間短的優(yōu)點(diǎn),可對已發(fā)生磨損和炎癥病變的膝關(guān)節(jié)進(jìn)行替代治療,同時(shí)盡量保留關(guān)節(jié)組織和膝關(guān)節(jié)的本體感覺,因而備受臨床關(guān)注[2]。但隨著臨床應(yīng)用增多,有研究顯示,部分患者存在術(shù)后疼痛和關(guān)節(jié)功能恢復(fù)不佳的問題[3]。因此,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后疼痛與關(guān)節(jié)功能恢復(fù)問題逐漸引起臨床重視。中醫(yī)認(rèn)為,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屬“膝痹”范疇,多因肝腎陰虛、氣血不足所致,多為肝腎陰虛證。獨(dú)活寄生湯是中醫(yī)經(jīng)典方劑,具有補(bǔ)益氣血、通絡(luò)止痛的作用[4]。基于此,本研究探討給予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患者接受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聯(lián)合獨(dú)活寄生湯治療的效果,現(xiàn)報(bào)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0年6月至2023年6月宜章縣中醫(yī)醫(yī)院收治的100例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患者的臨床資料進(jìn)行回顧性分析,根據(jù)治療方法不同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50例。對照組患者中男性25例,女性25例;年齡26~70歲,平均年齡(50.16±14.38)歲;BMI 18.00~27.50 kg/m2,平均BMI(20.64±2.30)kg/m2;病程1~8年,平均病程(4.49±1.60)年。觀察組患者中男性28例,女性22例;年齡24~68歲,平均年齡(49.82±15.79)歲;BMI 17.50~28.00 kg/m2,平均BMI(21.08±2.19)kg/m2;病程1~8年,平均病程(4.52±1.74)年。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均Pgt;0.05),組間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jīng)宜章縣中醫(yī)醫(yī)院醫(yī)學(xué)倫理委員會批準(zhǔn)。納入標(biāo)準(zhǔn):⑴符合膝骨關(guān)節(jié)炎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5]和肝腎陰虛證的辨證標(biāo)準(zhǔn)[6];⑵年齡gt;18歲,且臨床資料完整。排除標(biāo)準(zhǔn):⑴合并精神分裂癥、抑郁癥等精神性疾病者或未按計(jì)劃完成治療者;⑵合并肺源性心臟病、呼吸衰竭、心力衰竭、肝腎綜合征、腦出血和心肌梗死者;⑶妊娠期或哺乳期、備孕期婦女;⑷合并惡性腫瘤者;⑸合并類風(fēng)濕性關(guān)節(jié)炎、強(qiáng)直性脊柱炎和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者;⑹合并急性外傷或既往已接受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者。
1.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接受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患者取平臥位,患肢放在托架上,屈曲90°,行常規(guī)全身麻醉。在髕旁內(nèi)側(cè)作長6~8 cm縱向切口,切除髕腱下脂肪,對軟組織進(jìn)行松解。進(jìn)入內(nèi)側(cè)關(guān)節(jié)腔后,清除股骨內(nèi)髁與髁間窩的骨贅、內(nèi)側(cè)半月板。行脛骨近端截骨,取出截骨塊,選擇大小適宜的脛骨假體試模,行髓外定位,進(jìn)行截骨,選擇大小適宜的股骨假體試模,進(jìn)行試模安裝,脛骨和假體試模覆蓋良好,拆開與假體試模同號的假體(沃爾德馬林克有限兩合公司),調(diào)骨水泥(Heraeus Medical GmbH,國械注進(jìn)20143136033,型號:Palacos R+G)固定。觀察組患者在術(shù)后給予獨(dú)活寄生湯干預(yù)。獨(dú)活寄生湯組方:獨(dú)活、桑寄生各15 g,秦艽、防風(fēng)、杜仲、牛膝各12 g,細(xì)辛、茯苓、肉桂、川芎、黨參、熟地、當(dāng)歸各10 g,甘草、白芍各8 g。隨證加減:疼痛嚴(yán)重者加地龍、川烏、白花蛇各10 g;關(guān)節(jié)浮腫、酸脹者加薏仁、蒼術(shù)各10 g;關(guān)節(jié)腫痛、屈伸不利者加干姜、威靈仙各10 g。中藥均由宜章縣中醫(yī)醫(yī)院煎藥房煎制,1劑/d,煎制后取湯汁300 mL,150 mL/次,2次/次。每周調(diào)整1次用藥處方,連續(xù)用藥4周。
1.3 觀察指標(biāo) ⑴比較兩組患者臨床療效。記錄患者術(shù)前和術(shù)后4周臨床癥狀評分[6]。顯效:臨床癥狀減分率≥70%,關(guān)節(jié)活動正常;有效:30%≤臨床癥狀減分率lt;70%,關(guān)節(jié)活動輕度受限,但不影響工作和生活;無效:臨床癥狀減分率lt;30%,關(guān)節(jié)活動較術(shù)前無顯著改善。臨床癥狀減分率=[(治療前癥狀評分-治療后癥狀評分)/治療前癥狀評分]×100%。⑵比較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于術(shù)前和術(shù)后4周常規(guī)穿刺抽取患肢膝關(guān)節(jié)液3 mL,采用離心機(jī)以3 000 r/min的轉(zhuǎn)速離心15 min(半徑8.5 cm),留取上清液,以酶聯(lián)免疫吸附法檢測關(guān)節(jié)液中C反應(yīng)蛋白(CRP)、白細(xì)胞介素-6(IL-6)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水平。⑶比較兩組患者膝關(guān)節(jié)功能。記錄患者術(shù)前和術(shù)后4周時(shí)美國特種外科醫(yī)院(HSS)膝關(guān)節(jié)評分和Lysholm膝關(guān)節(jié)評分量表(LKSS)評分。其中,HSS膝關(guān)節(jié)評分范圍0~100分,評分越高表示膝關(guān)節(jié)功能越好[7]。LKSS評分范圍0~100分,評分越高表示膝關(guān)節(jié)功能越好[8]。⑷比較兩組患者生活質(zhì)量。分別在術(shù)前和術(shù)后4周時(shí)采用關(guān)節(jié)炎生活質(zhì)量測量量表2-短卷(AIMS2-SF)進(jìn)行問卷調(diào)查,記錄患者生活質(zhì)量。該量表Cronbach’α系數(shù)=0.895,包含軀體、癥狀、情緒、社會及工作5個(gè)維度,共21個(gè)條目,每個(gè)條目按Likert 1~5分計(jì)分,總分最高105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質(zhì)量越好[9]。
1.4 統(tǒng)計(jì)學(xué)分析 采用SPSS 20.0統(tǒng)計(jì)學(xué)軟件進(jìn)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計(jì)數(shù)資料以[例(%)]表示,行秩和檢驗(yàn);計(jì)量資料以(x)表示,行t檢驗(yàn)。以Plt;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
2 結(jié)果
2.1 兩組患者療效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患者整體療效更優(yōu),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lt;0.05),見表1。
2.2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比較 術(shù)前,兩組患者CRP、IL-6和TNF-α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均Pgt;0.05);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CRP、IL-6和TNF-α水平均低于術(shù)前,且觀察組均更低,差異均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均Plt;0.05),見表2。
2.3 兩組患者HSS膝關(guān)節(jié)評分和LKSS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術(shù)前HSS膝關(guān)節(jié)評分和LKS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均Pgt;0.05);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HSS膝關(guān)節(jié)評分和LKSS評分高于術(shù)前,且觀察組均更高,差異均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均Plt;0.05),見表3。
2.4 兩組患者AIMS2-SF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術(shù)前AIMS2-SF評分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gt;0.05);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AIMS2-SF評分均高于術(shù)前,且觀察組更高,差異均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均Plt;0.05),見表4。
3 討論
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為慢性退行性、進(jìn)行性骨關(guān)節(jié)疾病,可引起關(guān)節(jié)軟骨和半月板損傷,關(guān)節(jié)周圍軟組織變性、病損,在關(guān)節(jié)邊緣形成骨贅,嚴(yán)重者可發(fā)生跛行、上下樓和蹲起困難、關(guān)節(jié)屈伸功能障礙及關(guān)節(jié)畸形,嚴(yán)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zhì)量。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作為骨科臨床微創(chuàng)手術(shù),利用關(guān)節(jié)假體替代已經(jīng)磨損的關(guān)節(jié)軟骨組織,其具有創(chuàng)傷小、術(shù)后康復(fù)快、關(guān)節(jié)功能好的優(yōu)勢,且技術(shù)較為成熟,在臨床得到廣泛應(yīng)用[10]。但有部分患者術(shù)后持續(xù)疼痛、關(guān)節(jié)粘連僵硬、關(guān)節(jié)活動受限[11]。因此,術(shù)后鞏固治療備受關(guān)注。中醫(yī)認(rèn)為,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多因風(fēng)、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且患者多存在氣血不足、肝腎虧虛證候,導(dǎo)致筋骨不強(qiáng)、氣血凝滯所致。獨(dú)活寄生湯出自《備急千金要方》,該方能補(bǔ)肝益腎,進(jìn)而緩解關(guān)節(jié)疼痛。
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患者整體療效更優(yōu),提示獨(dú)活寄生湯用于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后,有利于改善療效。分析原因?yàn)椋?dú)活寄生湯具有祛風(fēng)濕、補(bǔ)氣血、益肝腎功效。其中,獨(dú)活、細(xì)辛祛風(fēng)散寒,牛膝、干地黃、桑寄生強(qiáng)筋、補(bǔ)益肝腎,當(dāng)歸、白芍、川芎補(bǔ)益氣血。另外,本研究對方劑進(jìn)行辨證加減,使全方達(dá)到補(bǔ)益氣血、標(biāo)本兼治的目的,同時(shí)實(shí)現(xiàn)治療的個(gè)體化,減輕臨床癥狀,提高療效。
有研究顯示,IL-6、TNF-α 在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病理進(jìn)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IL-6 可誘導(dǎo) B 細(xì)胞分化,并促進(jìn) T細(xì)胞活化增殖,誘導(dǎo)和加速軟骨損傷,而TNF-α在關(guān)節(jié)炎癥早期即可出現(xiàn)異常增高現(xiàn)象,對于評估病情具有重要價(jià)值[12]。本研究結(jié)果還顯示,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CRP、IL-6和TNF-α水平均低于術(shù)前,且觀察組均更低,提示獨(dú)活寄生湯用于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后有利于減輕局部炎癥,促進(jìn)關(guān)節(jié)軟組織修復(fù)。這可能是因獨(dú)活寄生湯具有活血化瘀,改善局部血液循環(huán)的功效。獨(dú)活寄生湯可通過調(diào)節(jié)IL-6、TNF-α等炎癥細(xì)胞因子,抑制軟骨細(xì)胞凋亡,提高療效。
本研究結(jié)果還顯示,與對照組比較,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HSS膝關(guān)節(jié)評分和LKSS評分均升高,且觀察組均更高,提示獨(dú)活寄生湯用于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后有利于改善關(guān)節(jié)功能,促進(jìn)術(shù)后早期康復(fù)。這可能是因獨(dú)活寄生湯通過祛風(fēng)除濕、補(bǔ)益肝腎、活血通絡(luò)的綜合作用,達(dá)到舒筋健骨的效果,改善關(guān)節(jié)功能[13]。
此外,本研究結(jié)果還顯示,術(shù)后4周,兩組患者AIMS2-SF評分均高于術(shù)前,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提示獨(dú)活寄生湯有利于改善患者術(shù)后生活質(zhì)量。這可能是因獨(dú)活寄生湯可通過調(diào)節(jié)炎癥細(xì)胞因子,抑制關(guān)節(jié)炎癥,保護(hù)關(guān)節(jié)軟組織,減輕局部疼痛癥狀,緩解病情,提高患者生活質(zhì)量[14]。
綜上所述,單髁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聯(lián)合獨(dú)活寄生湯用于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效果顯著,有利于抑制術(shù)后炎癥反應(yīng),改善關(guān)節(jié)功能,提高術(shù)后生活質(zhì)量,具有較高臨床應(yīng)用價(jià)值。
參考文獻(xiàn)
趙昌盛,鐘群杰,林劍浩.中國膝關(guān)節(jié)骨關(guān)節(jié)炎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現(xiàn)狀[J].廣東醫(yī)學(xué), 2016, 37(13): 2050-2052.
田少奇,王斌,劉江俊,等.微創(chuàng)單髁置換治療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及骨壞死的中期臨床療效[J].中華創(chuàng)傷雜志, 2016, 32(7): 632-637.
馬路遙,郭萬首,程立明.單髁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后膝關(guān)節(jié)運(yùn)動學(xué)研究現(xiàn)狀[J].中華骨與關(guān)節(jié)外科雜志, 2015, 8(1): 97-100.
周杰,任江波,溫潔.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采用獨(dú)活寄生湯治療的臨床效果研究[J].世界臨床醫(yī)學(xué), 2018, 12(3): 84-85.
中國中醫(yī)藥研究促進(jìn)會骨科專業(yè)委員會,中國中西醫(yī)結(jié)合學(xué)會骨傷科專業(yè)委員會關(guān)節(jié)工作委員會.膝骨關(guān)節(jié)炎中醫(yī)診療專家共識(2015年版)[J].中醫(yī)正骨, 2015, 27(7): 4-5.
國家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dǎo)原則[M].北京:中國醫(yī)藥科技出版社, 2002: 241-242.
陳文婷. 人工全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術(shù)中護(hù)理效果及HSS評分、并發(fā)癥情況的分析[J]. 國際護(hù)理學(xué)雜志, 2018, 37(19): 2596-2601.
林建寧,孫笑非,阮狄克.膝關(guān)節(jié)lysholms評分等級評價(jià)膝關(guān)節(jié)功能[J].中國骨與關(guān)節(jié)損傷雜志, 2008, 23(3): 230-231.
朱建林,章亞萍,龐連智,等.關(guān)節(jié)炎生活質(zhì)量測量量表2-短卷的信度與效度研究[J].中國慢性病預(yù)防與控制, 2006, 14(2): 75-77.
史開宇,趙其純.單髁置換術(shù)治療膝關(guān)節(jié)內(nèi)側(cè)間室骨性關(guān)節(jié)炎的療效分析[J].中國骨與關(guān)節(jié)損傷雜志, 2018, 33(10): 1076-1078.
高晨鑫,丁浩源,姚捷,等.單髁置換術(shù)與全膝關(guān)節(jié)置換術(shù)在治療膝內(nèi)側(cè)單間室骨性關(guān)節(jié)炎術(shù)后早期關(guān)節(jié)遺忘度中的比較[J].生物骨科材料與臨床研究, 2023, 20(6): 14-19.
鄔波,馬旭,柳椰,等.膝關(guān)節(jié)骨關(guān)節(jié)炎患者軟骨炎癥因子表達(dá)與病變程度的相關(guān)性[J].中國組織工程研究, 2020, 24(2): 236-241.
夏皖心,熊余余.獨(dú)活寄生湯配合中醫(yī)康復(fù)治療膝關(guān)節(jié)骨性關(guān)節(jié)炎臨床觀察[J].中國中醫(yī)藥現(xiàn)代遠(yuǎn)程教育, 2023, 21(19): 67-69.
侯成志,李秋月,魏戌,等.獨(dú)活寄生湯治療膝骨關(guān)節(jié)炎的研究[J].中國中醫(yī)基礎(chǔ)醫(yī)學(xué)雜志, 2021, 27(11): 1843-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