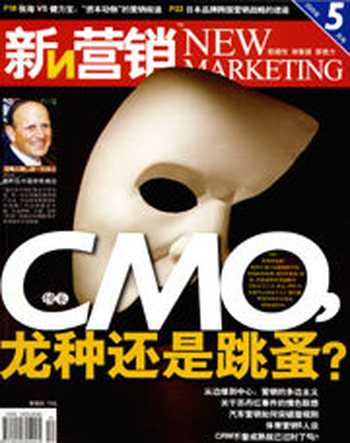屈云波:3年思“過”有心得
任 之 向 華
自從2002年2月離開廣東順德,屈云波再也沒有在那塊讓自己的職業生涯急升陡降的土地上出現過。在科龍擔任營銷副總裁的23個月,無疑是屈云波的人生作加速度奔跑最為辛苦的日子。離開科龍后,屈云波極少露面。也許,在他離任時的一些“墻倒眾人推”的媒體言論讓他不得不學會警惕。
2005年3月底,沉默3年的屈云波如約出現在《新營銷》記者面前。盡管他聲稱自己分不清“營銷副總裁”與所謂CMO定義的真正區別,但在他自稱“不在工作狀態”的近3年時間里,他顯然對自己當年的經歷,以及出任企業營銷副總裁同行的命運,沒有停止過思考。
稱職的CMO從何誕生
話題從2004年年底原TCL移動通信總經理萬明堅下課說起。屈云波抱怨某刊物編輯不久前把他寫的一篇文章《淡然論成敗》標題改為《輕狂的代價》。“第一,我是那種位置上的過來人;第二,我從來沒有與萬明堅直接打過交道,怎么可能說人家輕狂?”屈云波苦笑著說。
不過,屈云波也向記者透露了這篇文章刊發后的一個花絮。某電信部門官員看到這篇文章后打電話給他,說《輕狂的代價》這標題已經很客氣了,萬明堅的一些行為確實太過了,就是“造神運動”。屈云波說,不管他當時在科龍任上還是離任,自以為是的事,他很少干。
事實上,像孫陶然、萬明堅這些企業內部培養、跨專業成長起來的本土營銷梟雄的最終下課,與何經華等一批曾在世界500強企業擔任高管的職業經理人高調轉投民營企業的鎩羽而歸,已然表明,要在CMO這個位置上長久撐下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國企業內部,僅僅是人事協調工作,譬如平息市場部與銷售部的爭端,新人與舊人的相互攀比等,就夠CMO勞神費力的了。不知什么環節出了問題,CMO就會出局,獨自舔傷。
一些專家指斥說,中國企業最多只有CSO(首席銷售官),而沒有CMO。因為多數營銷副總出身于做銷售,面臨的任務和壓力都與銷售業績緊密相關,他們怎么會考慮兩三年后的市場規劃和品牌戰略?
對于這種說法,屈云波表示認同。在他看來,在中國企業,不僅是CMO這個職位,其他CXO也同樣面臨銷售壓力。從中國企業的發展史來看,都是從銷售開始,再加上廣告,然后才設立市場部,開始學營銷,這是一條必然的成長之路。并且,只是近5年來中國企業才逐步建立了營銷概念。所以,做銷售出身的人主導營銷部門也就是一種必然現象。“西方企業也一樣,中國企業不過是在重復這一歷史。”
正因為這樣,屈云波認為,要誕生稱職的CMO,要么是現有的CSO,通過學習專業營銷知識,變成CMO;要么是有MBA高學歷的人,學習了系統的營銷知識后,在企業的銷售部門鍛煉一些時日,然后成為CMO。
那么,在CMO必備的素質中,如人格、個性、權力欲、專業能力、執行力和協調能力等,如果要按重要性排序,該怎么排呢?“在我看來,研究生意怎么做,落實各項措施,把市場做起來,肯定是頭等大事。至于怎么跟上司配合好,跟同僚怎么合作,是第二位的。但我必須承認,在中國做營銷副總,要想多做幾年,50%以上的營銷副總首先必須研究老板。”屈云波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說。
以科學的考評體系保護所有的人
完美的CMO在中國很少,屈云波說。這似乎是句多余的話,因為如果沒有完美的CEO,大概也不會有完美的CMO。
在現實世界中,即使是西方企業,同樣是聘請CMO,有的CEO用專業能力作標準,讓CMO參與重大決策;有的CEO則授權CMO負責品牌建設和推廣,使其成為營銷活動的推動者,而不讓其涉及銷售事務;有的CEO則會把銷售系統一并交付給CMO,讓其負責營銷預算、人員調度。
但是不同的授權肯定會導致不同的考核評價體系,問題是,如果CEO的授權是含混而模糊的,CMO怎么控制自己命運的不確定性?
按照菲利浦·科特勒的理論,一個CMO下邊應該管一個市場總監、一個銷售總監、一個物流(成品物流)總監和一個售后服務總監。但在中國,CMO的職權通常有三種劃分方法:第一種,營銷是配角,銷售是老大;第二種,兩者勢均力敵,但業績吃緊時,仍會偏向銷售,而把營銷預算削減;第三種,營銷最重要,銷售是營銷的組成部分,營銷部門主導銷售部門。事實上,不僅是中國企業,即使是跨國公司,這種授權情況也是各不相同的。屈云波說,他發現外資公司人員的名片上,有的寫著“Sale manager”,有的是“Marketing manager”,有的則是“Sale and marketing manager”,尤以后者居多。屈云波由此感慨說,美國企業的營銷水平也不均衡,授權也不清晰,有的企業營銷甚至做得不如中國企業,“當然總體水平比中國好”。
既然授權上難以縝密嚴謹,CMO豈不最容易成為企業業績下滑時的替罪羊?屈云波寄望于企業根據授權建立相應的營銷系統考評體系。在他看來,有了這套科學的評價體系,就可以保護所有的人,當然也包括CMO。
恪守價值觀讓自己落了個壞名聲
盡管3年來不談自己在科龍的經歷,但從屈云波零碎的敘述里,我們仍可以看出他作為CMO的代表性人物,在一個大型企業里變革、營銷的不平坦心路歷程。
據屈云波介紹,當時他的幾個重要幕僚特意告誡他要多考慮任期內的現實問題,至于前任的歷史遺留問題則能避就避。屈云波的態度卻相當明確:“第一,我不是高尚,但人形成的價值觀非一夜可以改變。第二,我并不認為抓現在和抓未來兩者是矛盾。我認為自己不會厚此薄彼。第三,我有委屈不可能向外傾訴,前任的一些‘水分我不可能說。第四,也許別人很珍惜這個職位,認為很光彩、很風光、很有權威感,但我真的感覺到了壓力和責任。我不喜歡前呼后擁,不喜歡天天見記者、上報紙,我出差就是為了解決市場問題,分公司經理到機場接我讓我感到很惡心。我自己不會打的去嗎?最多派個司機接我就可以了。”
“只要你的業績不能馬上上來,那些盯著你的位置、想象你有多風光的人就會把你的點滴失誤放大無數倍;而以媒體為代表的外界也會認為你沒能力,本事不大。至于究竟是誰造成的虧損,企業內部出了什么問題,他們不關心,他們也調查不到。所以,從現實主義者的角度來說,肯定就沒有誰去做打基礎的事,做登高望遠的事。但是反正我的價值觀就是這樣。我把前任的責任扛了下來,做了很多消滅‘水分的工作。但我落了壞名聲。1999年科龍盈利最高,為6億多元。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恢復那個數字。但顧雛軍接手科龍后,就又盈利了……我在任時巨虧,這在邏輯上成立嗎?”
反思三大教訓
據屈云波說,蟄伏的這3年間,大概有6次有價值的重新出山的機會。這種機會是指“與科龍同等規模甚至更大的企業”邀請屈云波做營銷副總、常務副總或總裁,但因為覺得自己不在工作狀態,只想休息,所以他都推辭了。盡管如此,不排除有一天,他還會再去做職業經理人,而且一旦再去企業,“肯定會比過去成熟”。
這種說法成立的前提是,冷靜思考了3年,屈云波總結了三大教訓:“最大的教訓,是不知根知底就到企業里去了。第二個教訓,當時的科龍是真正誠心想變革,但我不懂企業變革,所以在技術上我也做得不好,我沒學好就干了起來。第三個教訓,用人方面是我的一個弱項。今后再有機會,一定會汲取這三大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