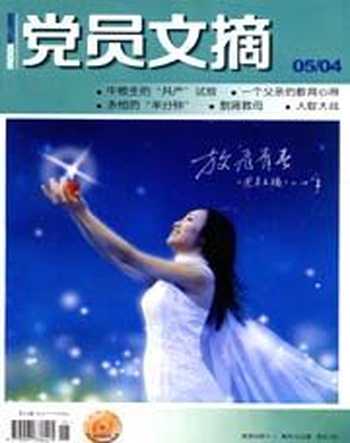徐本禹感動中國的大學生
彭光芒 李海波

“別人幫助了我,我一定要幫助別人”
徐本禹出生在山東聊城一個貧困農民家庭里。1999年,他考入華中農業大學。那年冬天,天氣很冷,他卻穿著一件單薄的軍訓服。一位同學的母親送給他兩件冬裝,并關切地說:“天冷了,別凍著。今后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難就告訴阿姨。”第一次遠離家鄉和親人,第一次在他鄉得到好心人的幫助,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覺,讓徐本禹至今不能忘記:“當時我知道無論說什么都是蒼白無力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愛心傳遞下去,用自己的行動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別人幫助了我,我一定要幫助別人。”這就是徐本禹作出到貧困山區義務支教決定最充足的理由,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支撐著他堅持下去的原動力。
他作出了讓所有人驚異的決定
在許多人眼中,徐本禹這個22歲的大學畢業生有著令人羨慕的前程。2003年,他以372分的高分考取了本校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然而,徐本禹卻作出了讓所有人驚異的決定:放棄攻讀研究生的機會,去貴州省大方縣為民小學教書。當他打電話把這個決定告訴父親時,電話那端的父親哭了。長久的啜泣之后,父親用發顫的聲音說:“全家尊重你的選擇,孩子,你去吧……”
上大三時,徐本禹在《中國少年報》上讀到了一篇題為《當陽光灑進山洞里……》的文章:“陽光灑進山洞,清脆的讀書聲響起,穿越雜亂的巖石,回蕩在貴州大方縣貓場鎮這個名叫狗吊巖的地方。這里至今水電不通,全村只有一條泥濘的小道通往18公里外的鎮子。1997年,這里有了自己的小學——建在山上的巖洞里,5個年級146名學生,3個老師……”讀著讀著,徐本禹哭了,他決定要用自己的方式來幫助這些巖洞里的孩子。徐本禹在校園里開始為這些從未謀過面的孩子們募捐,呼吁大家和他一起利用暑假時間到貴州支教。
當年暑假,徐本禹和4個同學帶著3箱衣服、1口袋書及500元錢坐上火車前往貴州。幾經輾轉,他們終于到達目的地——貓場鎮狗吊巖村。當徐本禹一行走進巖洞里的為民小學時,被眼前的一切驚呆了:“巖洞里的教室是用兩堵僅一人多高的墻隔開的,中間是過道。南邊是個四年級復式班,北邊是六年級。四年級的黑板搭在巖洞上,是用兩根棍子支撐著一塊木板做成的。如果我不是親眼看到這種情形,無論怎么想也想不到這里的條件會如此差。”
當暑假結束返校時,狗吊巖的孩子們流著眼淚,一直把徐本禹一行送到好幾公里外,他們拿著自制的小紅旗簇擁在徐本禹身旁,硬把幾個煮熟的雞蛋塞進他的背包。
一個孩子仰著頭問道:“徐老師,你還會回來嗎?”徐本禹噙著眼淚,點了點頭。他沒有告訴孩子們,他正在準備考研究生。
2003年4月16日晚上,徐本禹徹夜未眠,狗吊巖村孩子們期待的眼光一直在他腦海中閃現。就在這個夜晚,徐本禹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放棄攻讀研究生的機會,回到狗吊巖村去幫助那些孩子。
為了山區的孩子,他忍受孤獨和寂寞
2003年7月16日,徐本禹帶著3000冊圖書和7位志愿追隨的同學一起來到狗吊巖村。這里好像一個信息封閉的孤島,不通公路、電話,物質文化生活極度匱乏,晚上只能點油燈照明,寄一封信也要在周末走18公里崎嶇的山路到鎮上。每天吃的是玉米面、土豆和酸菜湯,晚上,滿身亂爬的跳蚤幾乎讓他們無法入睡。沒過多久,志愿者一個又一個地離開了。
8月1日,最后一個同來的志愿者也坐上了返回武漢的長途車。車窗內外,去送行的徐本禹同他無語對視:“真的堅持不下去,就回學校吧。”同學的一番話讓他有些觸動,經過一番思考,徐本禹還是留了下來。
徐本禹和村委會主任一家吃住在一起。原來徐本禹是不吃辣椒的,可是來到這里以后,每天都要吃辣椒,讓他有一種想吐的感覺。這里的衛生條件很差,蒼蠅到處亂飛,在吃飯的時候經常發現蒼蠅在里面。“當地情況就是這樣,剛開始很惡心。我對自己說,就當沒看見罷了。現在我已經可以吃玉米面和酸湯了。餓的時候,一頓可以吃三碗玉米飯。只有吃飽了,身體才有保障,才能在這里支教下去。”
徐本禹住在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間里很少見到陽光,這個小空間成了他學習的樂園——一張桌子上擺滿了書籍,有專業書、文學書、英語書、數學書等,還有一些書放在床上,地上擺放著生活用品和好心人捐的物品,原本狹小的房間變得更加狹小。
徐本禹在這里一周要上6天課,每天上課時間達8個小時。他自己負責五年級1個班,除了教語文、數學外,還要教英語、體育、音樂等。由于信息閉塞,學生對外界了解極少。徐本禹問全班40名學生,有多少人聽說過雷鋒的名字,結果只有4個人知道。徐本禹說:“這里的學生記憶力和理解力都很差,有時講了10遍、20遍的東西,學生還是聽不懂。有時,我氣得把書一丟,走出教室,可最后還是得回來。這讓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誨人不倦!”
2003年12月7日夜里下了一夜的雨,崎嶇不平的小路變得更加泥濘。12月8日,當徐本禹走進教室的時候,發現有5名學生沒有來上課,他問同學知不知道他們為什么沒有來上課,有的說天氣太冷,路不好走,走到半路又回去了。當天上午,徐本禹沒有上課,來到了沒有上學的學生黃紹超家,在家玩的還有黃紹超的弟弟,這個孩子也已經半個月沒有去上學了。徐本禹后來得知,黃紹超的爸媽都外出務工了,家中只有爺爺奶奶,老人很少過問孩子的學習,像這樣的家庭在這里還有很多。這樣一來,督促學生學習的任務全都落在了老師的身上。
也是12月8日那天,由于何福洋和弟弟何偉都沒有來上課,徐本禹來到他們家。當問他倆為什么沒有去上學時,何偉說:“沒有鞋穿!”說完,兄弟倆都哭了。當徐本禹把目光投向兄弟倆那沾滿泥巴的小腳時,心里一陣刺痛:自己穿著皮鞋腳還冷,而他們卻打著赤腳,他們怎么能夠受得了?在回校的路上,徐本禹心里越想越痛……回到學校后,他拿出50元錢托人給何福洋家送去。
通過這些點點滴滴的努力,學校的學生增多了,現在,這里的學生從140人上升到了250人左右。慢慢地,孩子們可以聽懂普通話了,與人交流也不害羞了。
而徐本禹心里的孤寂,卻只有向學友、師長傾訴。2004年4月,徐本禹回到母校作報告時,第一句話是:“我很孤獨,很寂寞,內心十分痛苦,有幾次在深夜醒來,淚水打濕了枕頭,我快堅持不住了……”本以為會聽到豪言壯語的師生們驚呆了,沉默了,許多人的眼淚奪眶而出。
報告會后,徐本禹又返回了狗吊巖村,依然每天沿著那崎嶇的山路,去給孩子們上課。
因為徐本禹而感動,因為感動而行動
徐本禹在狗吊巖村為民小學支教半年后,學校從巖洞搬出來,修建了新的校舍,辦學條件有了很大改善。
2004年春夏之交,大方縣大水鄉黨委書記沈義勇邀請徐本禹去作報告。在開往大水鄉的車上,沈書記希望徐本禹能到大水鄉支教。
大水鄉大石小學的校舍是一座有幾十年歷史的兩層木樓,上面一層搖搖欲墜,其中一間是四年級教室,另一間門口掛著“危險,不要靠近”的牌子。還有一間教室是用紅白藍相間條紋的塑料布圍成的,木板和磚頭搭就的課桌和凳子隨時可能傾覆,但孩子們似乎早就習以為常,趴在“課桌”上,眼神那么專注。
這一切深深震撼著徐本禹。他在決定到大石小學的同時,給華中農業大學團委書記寫了三封信,談了自己的困難、處境和想法。這三封信引起了學校的極大關注。學校黨委書記李忠云說:“要去人看看,要支持徐本禹,把小學的校舍修一修。我們應該為西部基礎教育做點事,這是大學的社會責任。”2004年6月26日,華中農業大學的兩位老師來到了貴州省大方縣。他們看望了徐本禹,考察了貓場鎮狗吊巖村的為民小學和大水鄉大石村小學,深受震動。就在兩位老師在大方縣的山路上顛簸的時候,他們接到了華中農業大學校長張端品教授打來的電話。張校長說:“學校決定捐助8萬元幫助徐本禹,用來為當地小學修建新校舍。”
2004年7月,華中農業大學一些老師和學生放棄休假,將在貴州大方縣拍的照片選出100幅,配上簡要文字,以《兩所鄉村小學和一個支教者》為題發到網上。短短9天,這篇帖子的點擊率就超過了百萬,很多網友是流著淚讀完這篇帖子的。緊接著,從祖國內地到港澳臺,從亞洲到歐洲,從北美到澳洲,要求捐款捐物的電子郵件雪片般地飛來,網友們表達了一個共同的意愿:因為徐本禹的故事而感動,因為感動而行動……13個國家的熱心人士要求資助大石小學的貧困學生。美籍華人陳旭昭女士還在美國進行募捐,為大石小學的學生寄來2000美元。2004年7月初,54歲的王昌茹從武漢趕到了大方縣:“我是沖著徐本禹來的,徐本禹走到哪兒,我就跟到哪兒。”她決定與徐本禹一起支教。
本刊補述:2005年2月17日晚,在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2004年年度人物評選”頒獎晚會上,當主持人宣讀完評委會對徐本禹的頒獎辭后,徐本禹哭了,在場的很多觀眾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
(包玉祥薦自《中國民族報》原標題為《一個支教者和兩所山村小學》 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