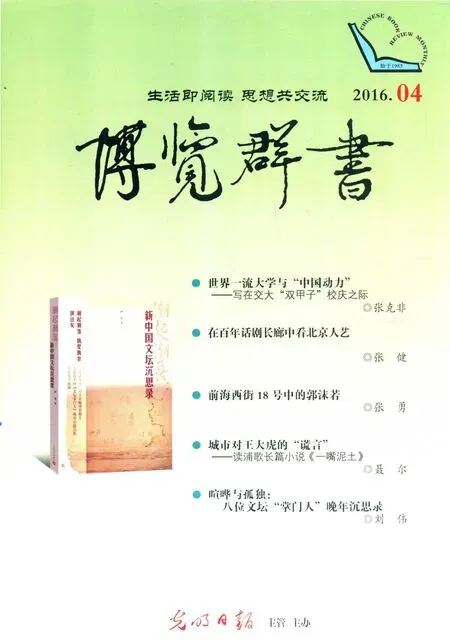茅以升作并書《北洋今勝昔二十韻》
左 森
每當我看到著名科學家、教育家,現代橋梁事業的先驅者茅以升先生(1896~1989)八十七歲高齡時,為天津大學(前身北洋大學)九十周年校慶自作自書的《北洋今勝昔二十韻》,都會深深為他的藝術修養所折服。
茅以升曾任北洋大學(天津大學的前身)校長,對天津大學有獨特深情。多年來,他一直十分關心天津大學的發展。茅老對天津大學的來人甚為熱情。我曾受學校委托請他題寫校訓:實事求是。茅老的題字每字一尺見方,其筆力和神韻為師生和校友稱頌。
天津大學九十周年校慶前夕,我接到茅老來信,約我到他家中面敘。我剛進家門,茅老便從書房取出很寬大的一卷宣紙。打開一看,只見一米多長的冰雪宣紙上寫的是一首二十韻的“長詩”,行行對稱、結構嚴謹,讓我看呆了。
回校后,我們展開茅老“二十韻”長詩,仿佛是在展開一幅飄逸的山水畫海。下筆逆人、行筆平出的書墨,沒有一帶而過的輕飄,也沒有撇尾敗露的“虛尖”,一點、一撇、一捺都嚴謹有力,得體巧妙,堪稱書法之佳品。很難想象,這紙寬大綿長嚴謹的書法佳作,出自八十七歲高齡的科學家。
茅老的文學修養和書法功力,決非一朝一夕的功夫。他年輕時,要定時在祖父的指導下默寫古文,臨摹過柳公權的《玄秘塔》和王羲之的爛亭序》等字帖。為了練筆力,練腕力,他在手腕上掛一串銅錢。茅老的字集王、柳之長,結構嚴謹,穩健蘊藉,‘清秀而不飄浮,活潑而不疏散,遒勁而不失法度。
茅老的“二十韻”,可說是對北洋大學歷史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在北洋大學執政任教的歷史寫照。“二十韻”宛如茅老的為人治學,精湛、完整、優美。1895年,北洋大學在西洋新學的影響下成立,即茅老詩中所云“新學既東漸”。1924年,劉仙洲(劉振華)任北洋大學校長,懷抱擴充建設北洋大學之志。1926年,聘茅以升到北洋大學主講結構工程等課程。1928年,北洋大學易名北平大學第二工學院(后更名北洋工學院),任茅以升為院長。當時,茅以升才三十二歲,學識淵博,執教有方,頗受同學歡迎。1929年,北洋大學鐘樓失火,工礦大部及地質全部設備盡付一炬。茅以升為此四處奔波,爭得庚款撥出的十萬元資助,才得以重建大樓。這就是詩中所云“魔火不為災,新廈俄頃竟”。
1933年8月初,茅以升結束北洋工學院的課程,赴浙江建設廳上任,興建錢塘江大橋。哪知由于日寇的侵犯,大橋建成三個月以后又要炸毀。這如同挖茅以升的心,他寫了七言詩《灑淚別錢塘》,立志“不復原橋不丈夫”,亦即“二十韻”中“面對驚濤不抽身,力驅鼉梁浮萬鈞。”1937年以后,北洋大學輾轉于西安、城固、西康、泰順、永嘉等地,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可說是北洋大學顛沛流離的時期,有人稱之為中斷時期。1941年,工程界學會在貴陽舉行會議,借此機會,北洋校友集會,主張恢復北洋大學。然而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北洋大學才得以恢復,茅以升任校長。對北洋大學的復校,茅以升在“二十韻”中唱道:“煌煌三十載,重開日月光。崇實遵校訓,時隆道乃昌。”
北洋大學誕生在祖國的艱危時期,輾轉于國家與民族的磨難之中,但仍為祖國培養了許多碩學鴻儒。“濟濟夸多士,嘉木矗千章”,是茅老對北洋大學業績的贊頌!
茅老的“二十韻”,是一幅絕妙的難得的美的書法,是北洋大學——天津大學的歷史寫照,是一位科學家、教育家的心志抒懷,含意深沉,興味無窮;其書法之優美,更令人驚嘆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