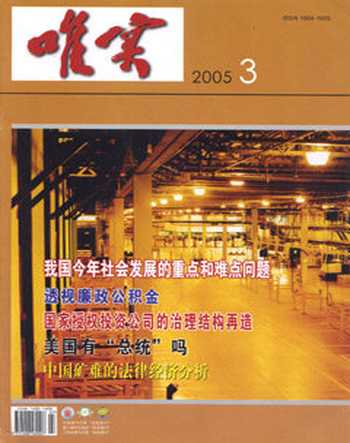國家授權投資公司的治理結構再造
黃群財
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中,國家授權投資機構的公司治理問題是關系改革成敗的重要環節。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必須擺脫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影響,圍繞國有資產安全與效益的目標,調整董事會職能,重構董事會與董事長、總經理和監事會之間的關系。
一、國家授權投資機構的性質與地位
我國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經過多年的改革,在上海、深圳的經驗基礎上形成了現階段的“同有資產監督委員會——國家授權投資機構(以下簡稱投資機構)——國有企業”的三層架構管理模式。投資機構又稱“中間層公司”或“國有資產經營公司”,主要指負責國有資產運營、行使國有資產的日常管理職能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我國《公司法》統稱為“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投資機構的外在形式有以下幾種:一是由原來行業管理部門或行業總公司改造而成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二是在原來國有集團公司的基礎上組建的控股母公司;三是南政府直接設立的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在1998年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和實行政企脫鉤、企業重組時,有些大型企業也承擔中間層的功能,接管了一些企業。投資機構在性質和地位上與第三層國有企業有重要區別:第一,投資機構行使的是出資人權利,是公司制國有企業的股東,其權力性質屬于所有權范疇,而普通國有企業行使的是經營權,權力性質是法人財產權。第二,投資機構實現其經營目標的主要手段是開展產權經營和管理,以產權關系為紐帶通過控股參股等方式對國有企業進行產權經營和管理,負有貫徹實施國家經濟政策的功能。第三,投資機構在法律地位上有相當的特殊性。在投資權限上,它的對外投資可以超過其凈資產的50%,也可以出資設立國有獨資公司;在性質上它是國有獨資企業但卻不受《企業法》調整,在組織形式上它以公司的名義參與經濟活動,但《公司法》關于它的約束規范幾近于零。在三層架構管理模式下,投資機構是政府經營管理國有資產的中介,根據政府股東的授權或指示,投資機構代表政府對其控股或參股的國有企業行使出資人權利。基于這樣的特殊地位,人們對投資機構寄托了這樣的希望:防止政府對同有企業的行政干預;促使產權明確化;提高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然而,由于投資機構在歷史上和性質上與政府的特殊關系,我國當前的投資機構在運作上普遍受到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影響,從而嚴重地干擾了既定目標的實現。
二、國家授權投資公司治理結構的重構
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法律角色具有多重性,一是為國家機關,二是為所有者或投資者,三是為一般法人。第一種法律角色與第三種法律角色是容易分清的,但在第二種角色中,由于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缺乏有效規范,政府的社會經濟管理職能與固有資產所有者職能這雙重角色往往發生混同。這種混同是政府對投資機構行政化管理和投資機構內部運行行政化的主要根源。行政化管理的直接后果就是把投資機構等同于第三層國有企業或忽視其企業法人性質把它當作政府下屬機構對待。它對建立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的消極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結合公司治理的理念和投資機構自身性質特點改善其公司治理狀況,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
1.投資機構的公司治理必須符合國有資產安全和效益的目標
經濟學上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與公司法人并存。正是在求利意識支配下,財產的所有者將自己的財產交給專門的經營者經營,以彌補自己在經營能力上的不足,使有限的資源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利潤。這不可避免地產生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象,埋下了不安全的隱患。法律意義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作為這種安全控制機制便應運而生。求安與求利是推動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委托,世界銀行對瑞典、新西蘭等十二個國家的國有資產管理的一些做法和經驗進行了總結,并就中國國資體制改革提出了專門報告,報告直言:“世界上最好的國有企業都專注于資本的有效利用。政府有許多社會和政治目標,但在行使其在大型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時,國家股東應專注于資本回報的最大化。”政府給投資機構確定的目標只能是實現國有資產價值的最大化,惟此,投資機構才會成為融入世界市場的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商業化經營實體。在單一的商業目標下,追求資本回報的最大化,來自資本的有效約束也許就可以阻止如今慣常出現的行政干預下的合并和收購交易,那種強迫盈利國有企業接管虧損企業的事將不再重演。
2.董事會的職能必須定位于戰略決策和監督控制
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核心。在世界各國的不同公司制度中,出資人都是通過董事會來實現公司治理的目標的。實踐中,除了所有者與經營者合一的中小型公司外,大型公司的董事會均不介入公司具體業務的執行與管理活動,董事會一般只負責戰略決策和監督控制。我國《公司法》第46條和第112條均將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公司董事會的職責界定為10項。這種列舉不可謂不具體細致,但從整體來看,它把業務執行權和監督權混為一體,董事會既不像一個戰略決策和監督控制機關,又不像一個純粹業務執行機關,顯得不倫不類。投資機構大多由原國有企業或國有企業的行業管理部門改造而來,董事會主要是由原來的政府官員和企業內部管理人員組成,企業的組織形式改了,但公司治理的理念卻未深入人心。所以,董事會更看重的是公司的經營管理,董事不僅直接介入業務執行而且在身份上也不區別于經理人員。董事會與經理層在職能和身份上的混同直接導致了監管功能的弱化,使得治理結構失效而“內部人控制”層出不窮。投資機構運營的資產相當龐大,面對著瞬息萬變且極具風險的資奪市場,董事會的職能必須明確定位為戰略決策和監督控制方能有效地實現公司治理的目標。
3.董事的產生方式必須行政化
良好的公司治理必須通過高素質的董事來實現,而優秀的管理人才必須經過市場競爭的方式以市場化的辦法選任進入董事會。然而,“企業改革,特別是最近幾年來,國有企業的改革在某些方面明顯后退了。后退的主要表現,不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治理,形成好的公司運作機制,而是在某些方面強化了政府的直接干預,強化了公司管理層的行政任免。”公司制度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管理人才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不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就無法達到資源優化配置的效果。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之一,新加坡的淡馬錫(TEMASEK)控股公司的重要經驗就是,企業管理班子和國際經理人市場公開并軌,管理人員從國際市場公開招聘,以一流的薪酬聘請一流的人才組建世界一流的管理團隊。作為投資機構
的股東,各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在內部設立專門的“董事提名任命委員會”,按照市場化的方式和薪金標準面向國內外公開招攬董事人才,經審核合格后派往中間層公司。透明公開的市場選拔機制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外部激勵和約束,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董事在經營管理的過程中更能勤勉盡責,而政府對企業的政治干預和干預所帶來的扭曲影響也可以相應減少。
4.董事會與董事長之間關系的民主化
我國的公司制度基本上是借鑒而來的,公司法對董事會與董事長、總經理之間的關系的規定是比較明晰的。但是,實踐中董事會集體與董事長個人之間的權限與責任之爭是屢見不鮮的,董事會與經理層特別是總經理的關系處理也不盡規范。國外運行良好的制度在我國不盡理想的適用效果促使我們從我國的傳統文化和傳統管理體制的角度來考察問題。首先從董事長的問題談起。我國《公司法》并沒有給予董事長特別的權力,從《公司法》第114條對董事長職能的規定來看,董事長并沒有實際的權力而更像為滿足公司活動的儀式需要而設立的職位。然而,董事長在實際生活中一手遮天、一言九鼎的權力,卻往往使公司治理陷入一片混亂。這其中就有著傳統文化意識的原因。我國傳統文化向來缺乏民主監督意識,長官意志可以決定一切是非而不受其它力量的制約。在國有企業中這種傳統的官本位文化尤為深厚,許多管理人員至今還保留著行政級別,由政府官員或原來國企中的廠長經理轉化而來的管理人員也傾向于保留和擴張既有的行政性權力。在缺乏民主監督的整體氛圍之下,董事長和總經理等重要位置的人選由上級黨政領導直接任命更使得董事會集體的民主監督缺乏力度。投資機構的董事會肩負著制定國有資產運營戰略的重大使命,在董事會不能發揮集體智慧而由董事長一手操縱的情況下,國有資產的命運是相當危險的。董事長現有的職能必須弱化并做合理的劃分,屬于宏觀決策和監控的職能交由董事會集體執行,屬于微觀事務管理的下放到經理層行使,屬于會議召集等行政性職能可以由董事會辦公室或專職的公司秘書管理。
5.董事會與總經理之間關系的規范化
無論是以信托理論還是以委托一代理學說作為理論基石,各國公司法都認為董事會是公司的代表機關并以公司的名義聘用總經理,總經理應在董事會領導下開展經營活動。總經理作為董事會的下位組織是明確無疑的。然而,現實中卻經常出現總經理與董事長位次之爭等不可思議的事情。問題可以追溯到上文所提及的選拔機制與官本位文化。南于總經理是同董事會成員一起由政府部門或國資委任命的,所以董事會一開始就對總經理缺乏任命權這一重要的制約手段。而且總經理在行政級別上可以平行或高于一般董事,這一點在官本位的同有企業中往往要比法律的規定更具實際影響力。顯然,這并不是良性的公司治理所愿意面對的。董事會的存在意義除了戰略決策之外,還包括對經理層的監督控制。董事會對總經理的任免權不僅是董事會的戰略決策得到有效執行的重要保障,對總經理的選拔與罷免還是其重要的監控手段。任免權作為一種人事權與總經理個人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對于制約總經理行為具有長期、穩定、深入的作用。董事會對總經理的選任還有助于監督者理解和把握被監督者的情況,更便利地獲取經營信息從而使監督行為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從而提高董事會的權威性。另外,強調董事會對總經理的任免權是防止政企不分的必要措施。政府主管部門直接任命總經理的結果就是,總經理對該上級部門惟命是從,政府意志可以不經過董事會而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管理,總經理就有可能在不顧企業的盈利目標而一味地迎合上級的政治需要。如果任免權歸屬董事會,就可以在政府意志和總經理的經營活動之間產生一個隔離帶,減緩不正當行政干涉的影響。任免權是董事會職能真正到位的重要基礎。
6.取消監事會在投資機構的設置
取消監事會并不是對英美公司制度的感情偏好,而在于監事會本身有一系列的先天性缺陷。首先,制度設計者生硬地引用了政治學的權力制衡理論,人為地造成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中監事會與董事會、經理層的“三權分立”。這種思想是有一定理論背景的,“權力分立和制衡的政治學理論是整個資本主義政權建立的理論基石……現代公司以現代國家為縮影。”美國學者貝利在《公司制度的現代職能》中說道:“大公司是不靜止的政治制度的一個別種”。然而,公司權力結構是線性的組合而不是三權分立式的等邊三角形,公司不同于國家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的營利性以及營利性所決定的效率和成本要求。公司作為一個營利性組織,其組織機構的設置亦應符合效率的原則,從提高監督效率、減少監督成本的角度出發,公司內部監督權力不應被分割,換言之.公司內部監督權力應集中行使。監事會作為與董事會并立的監督權行使者,它的存在增加了國資委對中間層公司的監控成本,由于監督權力的分割同時也造成了監督效率低下。而且,中間層公司并不從事物質生產和服務性經營活動,這就使得其客觀上必須保持人員的精簡。經營著一百多億新元資產的淡馬錫公司,全部管理人員加上輔助性工作人員也不過四十多人。監事會的存在無疑使得冗員問題突出的國有企業更為臃腫。第二,監事會獨立性的欠缺使得其無法有效地行使監督權。有效監督的基礎在于:監督者在行使監督權時,應該擁有獨立的地位,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用公平正義的理念權衡雙方的利益,制止強勢一方的越軌行為,保護弱勢一方的正當利益。但是,無論是在“股東本位”的治理模式還是在“董事會中心主義”模式下,監事會勢必依附于其中的一方力量來行使監督權,作為監督前提的獨立性蕩然無存。何況,監事會本身就是弱勢一方,要讓它監督強勢一方實在是勉為其難。最后,按“三權分立”原理組建的公司治理結構一般是建立在股東多元化的股權結構之上的,所有者利益沖突催生了中立性的監督機關。投資機構是國有的獨資企業,國資委是它的唯一股東,這就使得它不必像普通股份公司一樣擁有監事會。實際上,國資委通過選拔機制約束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在民主決策過程中也可以互相制約監督,而總經理等高層管理人員則要受到董事會的監控。在規范的投資機構線性權力結構中監督權力是不會缺位的。
三、國家授權投資機構公司治理結構的目標模式
政府作為體現公共權力的國家機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以及作為民事關系中的機關法人,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須嚴格區分、正確適用,否則就會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導致管理秩序混亂。投資機構治理結構的行政化就是這種管理失序的表現形式。從設立投資機構的目的和投資機構的性質出發,對投資機構的內部權力關系進行調整后的公司治理模式可以概括為“董事會集體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具體的治理結構模式都應和具體的公司情況相匹配,任何公司治理的狀況都必須經過不斷的磨合才能發揮最佳效果,立法應留下合理的空間由公司章程自主決定。從整體而言,全部國企的治理結構問題的解決也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國家授權投資機構作為企業體系中最高層次的企業法人,其治理結構問題的有效解決將對國企改革進程起著重大的推進作用。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法學院)
[責任編輯: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