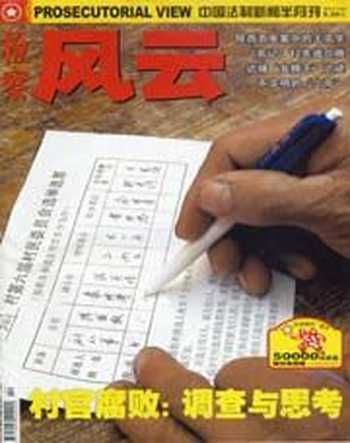摸底“村官”腐敗
習 文

編者按:
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三聯村,這個全國知名的先進村的村官劉宏球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在三聯,我就是皇帝”。
這一想法在中國不少的村官中甚為流行。這一心態也凸現了中國五千年農業文明所滋養的封建官僚文化仍然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有相當的影響力。
“村官”是生活在中國農村最基層的一個“官員”群體,“村官”甚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官”,但其中一些人在“官帽”和地方宗族力量的蔭蔽下,在“小廟”里干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大腐敗”來。近年屢屢爆出的許多農村兩委干部制造的數百萬、乃至數千萬的貪污大案,令各界震驚。“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村官”——一個最貼近老百姓的領導群體,他的腐敗將直接關系民心的向背。
但是,更應該引起關注的是,從九十年代開始的中國基層民主建設高潮中確立的村民直選,村務公開等等一系列制度已經初見成效。日前閉幕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因此,有必要深入調查目前村級干部的腐敗現狀,以利于完善現行基層民主制度的缺漏和不足。
一場大規模圍剿村官腐敗的行動已箭在弦上。
2005年6月下旬,根據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紀委副書記何勇的批示精神,由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發起,中紀委、中組部、中農辦、農業部等10個部門組成的村干部廉潔自律建設督查調研組成立。7月初,督查調研組分成4組奔赴青海、湖南、遼寧等9個省份,對村干部的違法違紀行為進行了深入調研,為期近兩個月。隨行的還有由29名記者組成的新聞宣傳督導團和由13名著名學者組成的專家咨詢團。
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農村處處長王金華表示,如此陣容強大的督查調研行動近年來在國內尚屬首次。
王金華,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聯絡員。這一次,他的身份又多了一重:村干部廉潔自律建設督查調研組成員。這意味著,他又多了一份責任。
10月8日,《關于村干部廉潔自律建設情況的調研報告》初稿經王金華之手匯總出臺,它對懲防村干部腐敗政策的制訂,無疑將作為決策依據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村官”腐敗不容小覷
金明池,河南省鄭州市高新區大里村原村主任。他利用職務之便貪污上級財政撥給村里的財政資金達88萬余元,挪用公款53萬余元,侵占各項工程款67萬元。2004年10月,金明池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劉宏球,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三聯村原黨支部書記。今年4月,這個曾帶領大家致富的“領頭羊”卻因侵吞507萬余元公款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徐寶文,遼寧省沈陽市東陵區前進鄉望花村原黨委書記、村委會主任、望花集團公司總經理。他借所承包的村辦集體企業望花啤酒廠轉制之機,非法占有國有和集體資金1393萬元。此外,還有多起貪污受賄行為,違法違紀所得高達3124萬元人民幣和8800美元。徐寶文現已被移送司法機關。
這只是村干部違法違紀的部分典型案例。
2000年以來,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查處鎮村級黨員干部違法違紀案件135起135人,今年上半年全區查辦的16起違紀案件中,就有15起涉及村級干部;2003年以來,湖南省共立案查處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2996件;2004年以來,遼寧省共立案查處村干部違紀違法案件2975件。

近年來,隨著土地轉讓開發的加速與村辦企業的活躍,村干部手中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因此,村干部的腐敗現象愈演愈烈,已成為農村社會肌體上的一大“毒瘤”。
村干部腐敗在農村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大。農村生活條件較為艱苦,村官有一點貪污,村民都會盯在眼里、反映強烈,有的甚至造成村民集體上訪、越級上訪,影響農村生產、生活秩序。徐寶文的貪污受賄行為就曾致使村民到省級機關上訪近百次,進京上訪20多次。
“村官腐敗”四大特點
督查調研組身負重任。兩個多月來,他們走鄉串戶,深入調查,總結出村干部違法違紀的顯著特點。
特點一:村干部違法違紀“一把手”占比重較大,串案、窩案比較多
主要表現為有的是村兩委班子成員集體作案,少數村干部合伙作案;有的是村與村之間的村干部合伙作案,村干部與國家工作人員合伙作案;有的是以村干部為主的家族成員合伙作案。
1998年以來,青海省檢察院在全省查處的56件77人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中,村書記29人,村主任24人,兩者占所查處人數的56%,會計、出納15人,占31%。
2004年,山東威海市紀委共受理反映村干部問題的信訪612件,查處214件,查處違法違紀黨員124名,占58%,其中涉及村支書、村主任34名,占查處黨員的27%。
在湖南、遼寧很多地方,黨支書大多兼村主任,違法違紀占案件總數的90%以上,民怨極大。
特點二:在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中,經濟問題較為突出,作案手段復雜多樣。
據調研統計,湖南省查處村干部貪污受賄、挪用公款案件占立案數的30%以上,遼寧占28%,均居首位。
2003年以來,牡丹江市共立案查處村黨員干部違法違紀案件388起,其中侵占、挪用集體財物的案件77起,占查辦案件的20%。
其表現形式主要有:貪占、截留、私分、虛報冒領土地補償款和救災救濟、扶貧優扶等資金和物資;在工程建設發包、企業和集體山林土地承包時收受賄賂;有的公款私存或轉借他人以獲取利息,或借給親友使用;在集體資產處置如企業改制、資產轉讓等過程中非法占有集體資產;財務管理混亂,吃喝揮霍,隨意開支等,其作案手段復雜多樣。在一些經濟發達的村,貪污數額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幾千萬,不容小覷。
特點三:村干部作風問題較為普遍,有的情節較為嚴重。
近年來,黑龍江省民政廳受理的群眾來信來訪,反映村干部作風不民主,違背民主決策程序的,占信訪總量的10%左右。
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三聯村,劉宏球遇有重大事情,基本上不與其他黨支委和村委商量,獨斷專行,作風霸道。
一些村干部借宗族勢力,恃強凌弱,發展為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的“村霸”。有的濫用職權,在土地轉讓、處理糾紛、審批宅基地和計劃生育指標等工作中索拿卡要,撈取好處;有的在換屆選舉中,違反有關法律法規,弄虛作假,采取不正當的手段競爭甚至賄選;有的村干部參與賭博、違反計劃生育政策。
特點四:村干部違法違紀區域分布相對集中,地區特征明顯。
村干部違法違紀多發生在經濟發達的城鄉結合部、城鎮化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和封閉的欠發達村。
經濟發達的村,違紀違法行為主要表現在土地、企業改制、集體資產處置等方面,干部作風問題雖然也占一定比例,但不突出。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或較封閉的貧困村,那些亂砍亂伐、作風霸道、賭博和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等問題則相對集中。
如:黑龍江省與土地有關的問題占反映村干部問題的80%。四川省成都市近期查處的村干部涉嫌經濟違法違紀案件中,100%都與土地問題有關。而湖南省衡陽市村干部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問題占村干部違法違紀案件總數的40%。
立法不明監管乏力
1998年,是中國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里程碑上值得銘記的一年。這年的11月,全國人大正式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由具有選舉權的村民直選產生。這項稱為“海選”的制度,被認為是對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
然而,多年過去,潛在問題開始浮現。不少寄托了村民厚望的民選村官們,在掌握權力不久就走上了以權謀私的道路。
選舉僅僅是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如果沒有相應的約束和制衡機制,民選出來的掌權者依然可以不對選民負責。這種“重選舉,輕管理”的局面被群眾稱為“半拉子”民主。
探索的步伐始終沒有停止。2004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健全和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見》,俗稱17號文件。其核心是落實農民群眾“四權”:知情權、決策權、參與權、監督權。并對設立村務公開監督小組、村干部民主評議和財務審計等方面提出了明確的措施,為農民群眾依法維護自己的民主權利提供了依據和保障。
但是,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道路還任重而道遠。在青海的調查中,當督導組成員詢問當地村民知不知道17號文件時,村民大多搖頭。17號文件發下來,村干部把文件鎖在抽屜里,根本不讓老百姓知道。有的地方村黨組織、村委會、村集體經濟組織“三合一”,書記、主任“一肩挑”,權力高度集中,“一言堂”現象相當嚴重。村民的知情權、監督權根本沒有保障。
一些地方村務公開、民主管理流于形式,民主監督機制尚未形成。各地統計的村務公開率雖然很高,但公開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存在半公開、假公開的現象;有的地方村務公開監督小組和村民理財小組成了“擺設”,起不到監督的作用;有的地方甚至從來沒有開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各種民主制度雖然上了墻,印成了小冊子,但村干部不落實、不執行的現象較突出。
在2000年之前,司法界對村官的身份認定存在爭議。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教育、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既不是國家一級行政機構,也算不上“公司、企業等其他單位”,所以刑法規定的一系列懲處“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犯罪”對村官違法違紀的行為認定并不適用,一旦案發,到底是由公安機關還是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存在意見分歧。
這種狀況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出臺,才算有了結論。這個立法解釋,把村官定義為從事公務的人員,把他們的七種行為的腐敗定性為“貪污、受賄和挪用公款等犯罪”。這些行為主要是:管理救災、搶救、防汛、優撫、扶貧、移民等救濟款物,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土地征用補償費用,還有國有土地的經營管理,代征、代繳稅款,以及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征兵工作。
但這種立法形式,并沒有完全堵嚴村官腐敗的“大堤”,因為村委會還有很多自治管理的職能,比如出售集體財產,籌辦村企業,建設村里農貿批發市場等,這些可為村官們產生額外的“效益”,現行法律對此還是無能為力。按照現行法律規定,村干部只有在協助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過程中的貪污、挪用、受賄行為才屬于檢察機關管轄范圍,至于在管理村莊內部事務中產生的其他違法違紀行為,司法機關往往很難介入。
在廣西和河北的調研中發現。在土地征用、補償中,征用和補償國家都有明確的規定,但錢撥到村里后,多少發給農民?多少留給集體?怎么管理怎么使用?相應的政策卻沒有明確規定,這就滋生了村干部腐敗的空間。
從書面制度設計上看,屬于村黨組織成員,黨內有批評、撤銷職務、開除黨籍等一系列監督制約措施;屬于村委會成員,有民主評議、罷免等措施,但是村干部不同于國家公務員和國企工作人員,他們的身份還是農民,有些人對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等處分根本不在乎。民選的村干部必須啟動罷免程序,但即使今天被罷免明天還可能被選上。
一些鄉鎮干部出于人情、利益的考慮,對村干部監管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說情包庇,查處時也是給個不痛不癢的處分了事。一些群眾反映多、意見大、長期久拖不決的違法違紀案件,往往都和縣、鄉領導干部的袒護有關。
村務財務管理國家規定有一套流程,但多數地方還是村干部“一支筆”,幾個干部說了算。一些縣、鄉根本沒有建立對農村集體財務的審計監督制度。由于村里財務管理混亂、財務制度形同虛設,一些村支書和會計、出納聯手做假賬,偽造單據,中飽私囊。
在違法違紀的村干部中,多數政治、文化素質不高,法律知識嚴重匱乏。一位村支書把公款借給朋友做生意,朋友還錢后,他干脆留下據為己有。當檢察院因其涉嫌貪污犯罪立案偵查時,他竟理直氣壯地問:“錢我都還上了,你們怎么還不讓我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