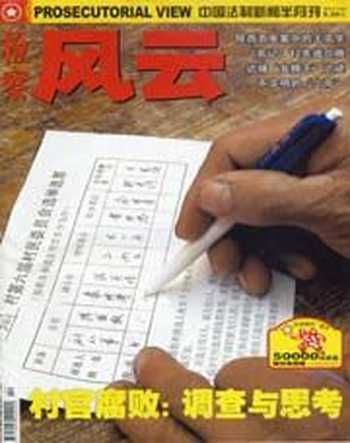開征遺產稅時機成熟了嗎?

有兩個經濟指數讓“是否該在我國開征遺產稅”的爭論變得愈來愈激烈,一是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大關,一是我國貧富收入差距已突破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的0.40警戒線而達0.447。“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貧富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法學家們認為,這是征收“遺產稅”所需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需求。基于此,我們選擇這樣一個話題:開征遺產稅時機成熟了嗎?希望通過討論得出一個答案。
更應關注個人財產法律制度的完善
文/汪世虎
遺產稅是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開征的一個稅種,目前約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征此稅。在我國,盡管當前對是否應開征遺產稅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看法和擔心,但不可否認,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具有重大財政、政治和社會意義的遺產稅的開征勢在必行。實際上,早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國民黨政府就曾于1940年7月1日開征了遺產稅。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種種原因,遺產稅一直未能開征。
從法律上講,要有效開征遺產稅,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實行財產實名制度,二是建立財產登記和申報制度,三是正確進行資產評估。財產實名制是財產登記和申報的基礎,只有實行財產實名制,才能準確界定個人的金融資產和其他財產,否則,遺產稅的征收將會落空;而財產登記和申報制度則是開征遺產稅的前提,只有實行財產登記和申報制度,個人財產才能明晰化,否則,遺產稅的征收就會流于形式;此外,開征遺產稅必須核實遺產的價值,因而建立公正、高效的個人財產評估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長期以來,我國個人財產十分隱蔽,客觀上為遺產稅的開征造成了障礙,也為逃稅提供了土壤。雖然自2000年4月1日起開始實行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但其他許多財產還未完全實行實名制,且這種實名制的效果不佳。至于個人收入申報登記制度則只在很有限的范圍內(國家工作人員家庭財產)實行,存在嚴重缺陷和不足。對個人財產的評估機制則無從談起,完全是一片空白。因此,在目前情況下,我們不應過多關注遺產稅的開征本身,而應更多地關注個人財產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就是說,如何在我國建立較完善的個人財產登記申報制度、個人財產評估制度和個人財產監控體系應該是當前的首要任務。具體地說,首先應當盡快制定和健全有關個人收入申報和財產登記、處理的法律法規,盡快建立個人資產檔案管理,明確個人產權;其次,應盡快建立專門性的具有較高權威和公正性的個人財產評估中介機構,定期對個人財產進行科學的動態評估;最后,還應制定有效防止個人財產向國外轉移的約束機制,以堵漏洞。
在完善個人財產法律制度的同時,還必須對現行有關私人財產權界定和保護的法律進行修正,以使之與遺產稅法相銜接。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對現行《繼承法》的完善,完善的主要內容包括:(1)遺產的范圍,應包括動產、不動產、無形財產權和其他財產權益,以便稅務機關認定和評估遺產;(2)遺產稅納稅義務人的確定,有遺囑執行人的為遺囑執行人,無遺囑執行人的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無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的為依法選定的遺產管理人;(3)被繼承人死亡后,遺囑執行人或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納稅人順序)應于法定期限內通知稅務機關,依法繳納遺產稅。未繳納遺產稅先行分配遺產的,有關當事人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西南政法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教授、法學博士

該是讓千年古稅有所作為的時候了
文/和靜鈞
遺產稅并不是新稅種,早在幾千年以前,古埃及人就用遺產稅來充實龐大的軍費開支,歐洲人也是五六百年之前就普遍啟用遺產稅來調節社會財產的分配。從法理層面來看,征收遺產稅彰顯了社會的公平,占有較多社會資源的富裕階層所繳納的稅金通過國家轉移支付以社會福利的方式使廣大窮人受益;從經濟層面上看,遺產稅除了具備財政收入籌措功能外,還有調節社會投資和消費功能,著名經濟學家拉弗所揭示的“拉弗曲線”,形象地告訴決策者們當稅基和稅率不超過其臨界點時,社會效率和社會公平可以和諧并存,相得益彰。
縱覽世界各國和各地征收遺產稅的成敗經驗,可以總結出,一個社會征收遺產稅的合理時機一般都具備四種條件:相當的GDP水平、較高的儲蓄率、一定的社會貧富分化度及社會成員的較高的公民意識。不可否認,以上條件都是基于完善的個人財產保障體制的前提條件上所得出的指標,財產原始權利的清晰界定,保證了遺產稅所針對的應稅財產有明確的產權歸屬。
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已經突破1000美元大關,按國際通行的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人均GDP已經有4000多美元之巨,早已經為全面征收財產稅創造了物質基礎。中國的財產稅框架中,除了個人所得稅之外,其他諸如房地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重要財產稅都沒有正式開始征收,這會拖累政府建設福利化社會的步伐。從國民儲蓄率上看,中國幾乎是一個“人人有儲蓄”的節儉型大國,幾十年的財富積累使其中近百分之二十的儲戶成為持有相當可觀資產的富人,以此為對象征收一定比例的財產稅并不會導致富裕人們生活水平的明顯下降。
雖然我們依然對社會上流行的中國貧富分化指標基尼系數的準確度心存懷疑,但社會貧富大分化卻是實實在在地客觀存在,而且還有不斷加重的趨勢。過分的社會貧富分化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們也欣喜地看到,經過十幾年來的市場經濟建設,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已經逐漸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回饋社會的意愿,這樣的社會公民意識奠定了以富裕人士為目標的遺產稅的社會親和力,不至于讓富裕人士落入“殺富濟貧”的心理疙瘩而對遺產稅大翻白眼。
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我國可以用“高稅基、低稅率、寬抵扣”的方式讓遺產稅融入我國的財產稅體系中。高稅基指的是征收起點高,以100萬人民幣的遺產為征收起點;低稅率是指所征遺產稅的稅率在20%水平,與目前我們的個人所得稅率相持平,留給納稅人心理平衡空間;“寬抵扣”是指原遺產所有人在世時所捐贈社會的部分及繼承人所繼承的遺產中所捐贈給社會的部分可以直接抵扣應納的遺產稅,這會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導向。
人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或重于泰山”。這句記載于《論語》,傳于《史記》,并經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一文而家喻戶曉的千古名言,給我國遺產稅制度建設充滿了啟迪。繼承了龐大的遺產的親屬及關系人,“割讓”出一小部分遺產回報社會,既是對死者的尊重,也是對逝者社會價值進一步肯定,更是對建設和諧的公民社會的貢獻。現在該是讓千年古稅遺產稅步入社會舞臺的時候了。
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

開征遺產稅的“必要”與“可能”
文/石峰
遺產稅這個國人曾經十分陌生的概念現已引起普遍關注,有消息稱:我國不久將開征遺產稅,專家的建議稿已上呈有關部門云云。對此,各種意見紛至沓來,其中反對者居多。主要理由是,目前,我國尚未具備與之相配套的個人收入申報、財產登記、財產評估、個人信用等制度;也有人擔心會出現被繼承人生前轉移財產,過度消費等負面效應。依我之見,根據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現狀,開征這一新的稅種并非不切實際。
目前世界上約有三分之二的國家和地區征收遺產稅,從國外經驗看,征收遺產稅一般是在社會財富積累到一定階段,貧富差距達到一定程度時推出的,設立的目的是限制財富過分積聚于個人,縮小貧富差距。我國目前的情形與之非常相像,市場經濟體制在推動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貧富差異的加劇,不僅在城鄉之間,而且反映于城鎮居民之間。因此,以“劫富濟貧”為主要目的的遺產稅的適時推出,在立法角度的必要性毋庸置疑。遺產稅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社會的福利事業及其他社會保障項目,其資金流向的專一性減輕了國家財政的相關負擔,在經濟層面的積極效應也是可以期待的。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遺產稅的開征需要具備相配套的個人財產監管制度,正如一些專家所言,在這方面我們還是比較欠缺。但是,制度不完善不等于不存在,我國現行的不動產(房屋等)、部分動產(汽車等)的物權變動登記制度,以及2000年起用的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均可對所指財產的所有權轉移進行監控,即當繼承人要將被繼承人名下的這些財產變更至自己名下時必須經過有關機構的“準許”。再者,配套制度的不完善也不意味著無實際操作的可能,如,個人所得稅已在我國實行多年,不也同樣存在個人收入申報,財產登記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問題嗎。因此,以配套制度有瑕疵作為否決遺產稅推出的理由并不完全讓人信服。
另有一些對遺產稅征收持懷疑或否定態度的觀點,我們在此亦做些探討。其一,稅法需要與其他法律的相互協調。我國民法和繼承法均沒有規定公民死后要繳納遺產稅,如果需要開征此稅,先要確定它的法源基礎。該說法其實是對稅法和民法性質的誤解,稅法是經濟(行政)法的組成部分之一,屬公法性質,立法的宗旨是保護公共利益,法律規范表現呈強制性;而民法和繼承法屬私法性質,主要目的是保護民事主體的私權利,因此他們不可能規定公民的納稅義務。其二,開征遺產稅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國的長輩們習慣自己艱苦奮斗,但總希望給后代留下更多的財富,因此大多數人會不贊同遺產稅。納稅本是公民應盡的法律義務,這不是愿意與否的問題,從被迫到自覺,從義務到意識實際是一種客觀的規律,西方國家亦是如此,我們不必過于擔憂。其三,國外不少國家現已取消或調整遺產稅,我們何必零點起步。世界上確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已取消或準備取消遺產稅,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香港等,但是國情有異,人家定有各自的理由,如,社會保障機制已較成熟或其他原因,市場經濟鼓勵競爭,也刺激貧富分化,這樣的路程我們恐怕難以跳越和避讓。
總之,在我國開征遺產稅的必要性是客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具體步驟上,可依國情先頒布遺產稅法,對遺產稅的起征點、納稅遺產的范圍、監管機構及相關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在公布日與正式實施日之間給出適當的過渡期,便于制訂配套法規和對法律內容的廣為宣傳等。
上海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