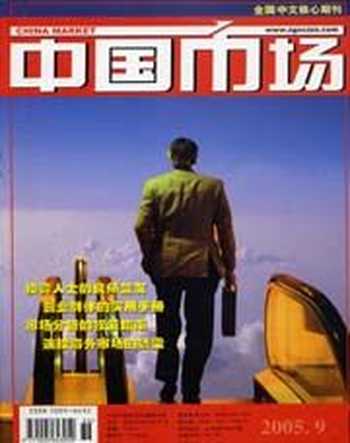理性看中國農民“愚昧、保守”行為
陳巧玲
一提起農民,人們馬上會想到“愚昧、保守”等詞匯。在現實中,當某些政策、部分官員的意圖在農民那里得不到響應時,農民就會遭受“素質低下”、“目光短淺”的責怪;當農民的種種行為與城里人的行為異樣時,農民就被戴上“愚昧無知”、“缺乏理性”的帽子。其實,這些都是偏見。農民是充滿理性的。
一、理性的概念
什么是理性?經濟學有一條近乎公理性質的命題:“人是有理性的。”這里,理性的含義簡單地說就是人的行為準則以追求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為標準。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認為,理性是人能夠根據自己面對的約束來做出反映一系列欲望與偏好的選擇,且所做出的選擇寧愿更多,而不是更少。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老師在與學生進行“經濟學方法論”對話時指出,經濟學的理性是指“一個人在做決策的時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選擇方案中,總是會做出他認為是最佳的選擇。”受貝克、林毅夫及其他中外經濟學家關于理性觀點的啟發,我們認為對于理性可以從下面四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理性不是追求財富最大化,也不是追求名氣最大化,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是指心靈的感受。有無效用,效用大小, 評價主體只能是行為主體自己。所以,農民在家種地是理性的,進城打工也是理性的,只是他們的理性偏好不同罷了。
第二,這個效用最大化不是抽象的、無條件的,而是具體的、有條件的。人的行為所以表現不同,是由于環境和條件不同,不同的環境和條件導致了不同的預期和行為,從這點來看,理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城里人送孩子學這練那,農民不讓孩子上學讀書,都是理性的,只是理性的約束條件不同罷了。
第三,雖然理性要求講條件,但這個條件是受行為主體主觀認識約束的條件,與行為主體的判斷力密切相關,理性的實質不在于能否正確地認識客觀環境并擁有正確的信息結構,而在于是否根據自身所認識到的約束條件和所擁有的信息結構尋求該約束條件下效用的最大化。這才是真正理性約束的定義,自我認為而已。如,二十年前老李放棄上大學的機會,當了一名紡織工人,今天卻下崗在家;下午小王澆了麥田,晚上就是一場大雨,這都不否定老李、小王的理性。以老李二十年前所擁有的信息結構來看,她的理性預期是讀書無用,小王沒想到晚上要來一場大雨。所以,這些失誤判斷不是說不是理性的判斷,而是由于客觀未來的不可知性才出現的。
第四,正因為判斷“理性”與否是從做出選擇的當事人的角度來衡量的,而不是從他人或社會的角度來看的,所以,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差異。
二、“愚昧、保守”恰是農民理性的表現
根據上述理性的知識,結合中國農民的實際,我們發現中國農民的行為是理性的。而農民的所謂“愚昧、保守”恰恰是農民理性的智慧。
計劃生育被形容為中國農村的“第一難”,難在何處?大多歸咎于農民的低素質與“多子多福”的愚昧觀念。然而,如果我們從農民的效用最大化與所受約束條件的角度來看農民的生育行為,卻發現農民是理性的。在二元社會結構中,農民的生存環境非常嚴酷,農民缺乏社會化福利保障,沒有多少權利、資本和技術,他們可以選擇的范圍很小,而受約束條件卻很多,因而他們的奢望不敢太多太大,豐衣足食就是農民追求的最大化目標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農民在可選擇的范圍內,選擇了多生孩子。在缺資金、少技術的情況下,多生一個孩子就等于多添一份勞動力,就多了一線增加產值的希望;同時,在缺乏國家提供的醫療、失業和養老等社會保障的農村,農民養育孩子的一個重要動機是“養兒防老”。孩子越多,孩子們人均承擔的養老成本就越低,從而養老的可靠性越高;孩子越多,父母面臨的風險成本如夭折、不孝等就越少,從而養老的安全性越大。可見,被看作是農民愚昧、不理性的超生、多生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恰是農民理性思維下的理性行為。
農民不僅在經濟上常常作效益和風險分析,也在政治上不斷算計。“草根民主”中的賄選現象,在中國引起了政府與各界的廣泛關注。農民為什么要把自己那神圣的一票以幾百元的價格出賣,甚至以幾盒香煙、幾塊肥皂來做交易?有人說這是農民“愚昧和素質低下”的體現。其實不然,這種看似愚昧、落后的做法,又是農民理性的行為,因為農民認為不論誰當選都不能取消農村計劃生育,不決定農產品價格,也不決定農民在城里打工的機會和待遇,還不會解決農村生老病死、衛生醫療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問題。一句話,選誰都差不多,與自己關系不大。這一點類似于城里專家學者不參加居委會選舉,因為選出來的“主任”不管給自己漲工資、發獎金、分住房、提職稱。因而,選居委會主任的“權利”沒什么“神圣”的。所以,高素質的城里人如果要以農民出賣自己那“神圣”的一票的行為來認定農民是愚昧無知、素質低下,那等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還有不少的人認為農民是保守的、封閉的,每一次農業工具和生產方式的改進,先進品種、技術的推廣,他們也要思慮再三,沒有見到實際的利益之前,他們是萬萬不敢碰的。似乎有太多的證據證明農民是保守的。但這種認識同樣是膚淺的,對農民也是不公正的。從理性知識的角度來看,農民的所謂“保守”行為,根本原因還是其受約束條件――沒權利、短資金、少技術、缺關愛所致。農民為什么“保守”?因為懼怕風險。農民面臨的風險非常多,他們既是決策者,又是實施者,還是決策后果的承擔者。他們不僅面臨自然風險,也面臨經營風險,還面臨政治風險。對于新鮮事物,城里人以所謂付“學費”來挑戰風險;但對于貧窮的農民,風險是下月的食物、來年的活命。農民承擔的風險多,致使農民在做出一個抉擇前不得不左思右想、權衡利弊,其行為就帶有小心、謹慎甚至保守的色彩。此外,農民的“保守”、“封閉”與其外界環境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觀地來講,在我國,無數“大蓋帽”圍著一頂“破草帽”,農民負擔很重;同時,“聰明人”坑農害農事件也時有發生。農民的保守、封閉實際上是內心世界恐懼的表露,他們的恐懼與他們所受到的排擠成正比。
總之,農民的“保守”,不過是農民自我保護心態的一種外部表現,農民的“愚昧”是理性的智慧。那種認為農民是愚昧、保守的觀點真是片面之言。
三、關于農民理性的兩點啟示
1、認可個體理性,提倡集體理性,有利于代表農民的利益和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
理性人假定伴隨經濟學已存在了幾百年,其內在的逐利要求即追求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作為理性人的根本特征卻從未改變過。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把最大化行為當作“人類行為的基本邏輯”來看待,認為這一邏輯是不言自明的理論前提。英國前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則把最大化行為假設看作對普遍經驗事實的概括。而且,各種各樣的利益要求、無數個體追求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行為成為經濟系統運轉發展的原動力。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客觀地說,這一體制排斥個人理性,強調集體理性,當時我們以為通過不斷的教育就可以使人們、特別是黨的各級干部做到行為準則以“社會、全體人民利益最大化為標準”。然而,現實中的低效和浪費卻使人們看到了這種理性的局限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行的各項改革、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是對個人理性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積極作用的肯定。當然,毫無疑問,集體理性也不應完全否定,它作為一個美好的理想應該提倡和追求,正如學習雷鋒應該發揚,星期六義務勞動需要光大一樣。但倘若光憑學習雷鋒來改變服務質量、只靠義務勞動來建成小康社會,恐怕就理想浪漫得有點近乎癡人說夢了。所以,我們思考、探討理性的目的之一應是如何形成一個能使個人理性的選擇與社會理性相一致的社會制度環境。這樣既能代表農民的利益,又能有效推動現代化進程。
2、轉變思維方式,有利于我們理解農民、正確對待農民。
如前所述,由于體制的約束與政策的限制,中國農民行為的選擇空間非常有限。農民常常會在有限的選擇范圍內做出最佳的選擇,以實現其效用最大化。這樣,難免會出現農民個人的行為和社會的最優選擇不相符合的情況,如前文提到的農民“超生行為”、“賄選現象”就屬這種情況。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行為者“愚昧、保守、落后、無知”等暗含行為非理性的詞語來概括。相反地,我們應該轉變思維方式,在評價農民行為時應該關注于農民為什么要抵制政府的計劃生育政策、出賣自己的神圣權利,而不是關注于這樣的行為是不是合理。或者,換句話來說,如果我們發現農民的行為不合理,那我們首先應該檢討制度安排是否恰當,體制政策是否合理,政府行為是否規范。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是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一項國策,多年來這一政策在農村的實行非常艱難。但是,要想改變農民“多子多福”的觀念,恐怕僅僅靠懲罰超生行為還遠遠不夠,該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了。農村基層政權民主選舉是農村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雖然一些農民最終將這一寶貴的權利出賣了,但這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我們基層政權的公信力不高。所以,改變不合理的政策、取消不合理的制度、規范政府不合理的行為,應是我們解決問題的重中之重,只有這樣,才能理解農民的行為、正確對待農民。否則,立意再佳的政策也必將是徒勞無功的。
作者單位:陜西科技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