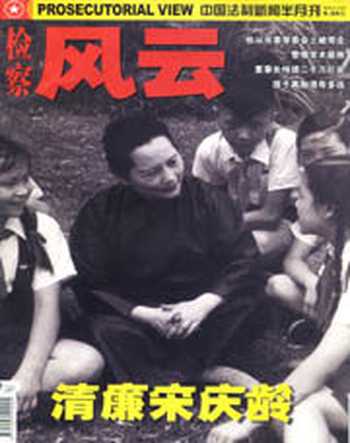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支撐力量等
王立民等

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支撐力量
王立民
司法是國家的重要職能,在法治國家尤其如此。它的魅力在于用公正裁判的方式來化解矛盾,保持社會的和諧。它常被作為和諧社會的穩定劑,也被看成是解決社會矛盾的最后防線。和諧社會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只是它們都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以不打破和諧為限。這就需要加強對它們進行有效的控制。
用司法來控制矛盾,有其自己的優越性。首先,具有規范性。司法是一種通過規范手段來化解矛盾的途徑,其中包括規范的法律內容、司法程序等。這些都由國家公布,人們應該知曉,易于學習和掌握,也應該貫徹和執行,違犯后還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也就有了可預測性,明知后果及其相應的責任。其次,具有權威性。司法是用一種公正裁判的方法來明辨違法與不違法,這符合社會的公共價值觀和合法的個人權益,會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同時,這種裁判的執行有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后盾,能夠得到切實的落實,有足夠的權威性。最后,具有反復適用性。司法是一種依法裁判的行為,只要出現法律規定的矛盾,都可使用司法途徑來解決。而且它還可以反復使用這一途徑,最后的判定結果又與法律規定相吻合,是在法治軌道上反復運作,不斷生效,不會中斷、失效。這些優越性決定了司法在保持社會和諧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法治國家把法治作為治國方略,都重視通過司法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正義,求得社會和諧。這些國家都有較為完善的立法,較為公正的司法和較高的司法權威,以致由司法來解決的矛盾一般會因這種權威迎刃而解,社會的矛盾不僅不再激化,而且還往往會被解決在萌芽階段。這樣,社會就不會出現大起大落,始終處在一個平穩的發展階段,保持一種相對和諧狀態。
我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的地位越來越高。為了更好地發揮它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支撐作用,有必要進一步提高司法水平。首先,要提高司法人員的法律素質。其中,包括要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法律知識和適用法律的能力,使他們在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等諸方面都能逐步適用司法獨立,特別是法官獨立審判的需求。其次,要進行司法改革。要通過這一改革實現司法公正,增強司法的公信力。目前,這一改革應該既包括司法體制改革,也包括司法程序等的改革。要使這一改革緊跟中國法治建設的步伐,不能滯后。最后,要樹立司法權威。司法機關要通過自己的司法活動,逐步樹立司法權威,讓社會正義真正得到體現,使社會的各矛盾,特別是那些比較棘手的矛盾最終在司法救濟中得到妥善解決。中國長期處在人治狀態,現在要樹立司法權威困難不小,不能期望一蹴而就,需要經過一定時期的努力。當然,要盡可能縮短這個時期,使中國的司法權威能早日達到法治國家的水平。
司法公正與法治
謝佑平

法治國家必須有完備的法制。必須政治民主,法律至上,權利本位,司法公正。一方面,司法公正是法治的表現和要求,另一方面,法治建設需要公正的司法作保障,司法不公或司法腐敗會從根本上破壞法治。司法公正既是司法的最本質要求,也是司法贏得公信力的根本依據。因此,研究司法公正與法治的關系,對于正確認識司法在法治社會中的角色定位,具有重要意義。
法治與人治是兩種相互對立的治國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幾人)之治(君主專制或貴族政治),法治是眾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據的是領導人個人的意志,法治依據的則是體現人民大眾意志的法律。人治與法治的分界線是:當法律與當權者的個人意志發生沖突時,是個人意志凌駕于法律之上,還是法律高于個人意志。或者說,是“法依人”還是“人依法”。
作為一種社會調控方式,法治的基本意義是依法辦事,依法辦事是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法治中,法律規定是社會管理的根據和手段,法律實現是社會管理的目標和要求,法律實施是連接法律規定和法律實現的橋梁。法律在人們心目中至上至尊,人們在法律里充滿有自由和秩序。在法治中,社會被法律連接構建成一個既有自由又有紀律,既有集體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內在有機聯系的整體。
在法治社會中,司法裁判的結果和狀況是法治的實踐狀態的重要反映,公民與法律的接觸途徑主要通過司法部門的活動,因為大多數社會公眾對法治的認識常常不是通過自身對法律條文的研究和學習而獲得的,而主要是從司法的實際操作中獲得的直接的感受。相當數量的社會公眾,甚至把司法理解為法治的全部內容。美國學者范德比特指出,“在法院而不是在立法部門,我們的公民最初接觸到了冷峻的法律邊緣,假如他們尊重法院的工作,他們對法律的尊重將可以克服其他政府部門的缺陷,但是如果他們失去了對法院工作的尊重,則他們對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將會消失,從而會對社會構成極大的危害”。公民對法律的公正的信任需要通過司法機關的公正裁判、平等保護訴訟當事人的權益、嚴格執行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行為而得以建立,所以,阿伯拉漢姆指出,“只有當法律完全被法院公正地作出解釋后適用時,法律才會被社會的大多數成員所接受”,法律的至高無上性必須深深植根于人們的心中,嚴格守法成為社會成員的生活的基本信念和準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法律的執行,司法者真正作為法律的守護神,嚴格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使法律平等適用于一切人,司法者所從事的裁判活動要嚴格依循法律的一切規則,執法者良好的執法行為,才能為民眾的普遍守法樹立真正的榜樣,并使人們真正相信只有依靠正當的法律途徑,才能尋求公平和正義并能獲得可靠安全的保障。
從“理性的輿論監督”談司法公正
肖中華

司法公正是人們對司法活動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應具有的品質。司法正義是社會正義的最后防線。一個社會,如果連司法都達不到公正,法治根本就無從談起了。輿論監督的作用就是實現司法公正尤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輿論監督對司法公正所發揮的積極和促進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成績也是斐然的。許多案件在輿論監督之下,得到了公正的判決。
但是正如矛盾是對立統一的,事物都是雙方面的。輿論的作用如同一柄“雙刃劍”,用之得當,則兩利;用之不當,則兩害。我們在看到輿論積極的一面,仍然不能忽視其存在的消極影響的一面。輿論有時表現為一種非理性的社會情緒。其特點是從眾,表現形式是激情,輿論的產生是以某類事情真實存在為前提的。“從眾”的輿論主體并沒有義務對事情的情節細節及其真實性予以甄別,輿論可以無節制,可以無尺度。沸沸揚揚的“寶馬車撞人案”、“聶樹斌一案”以及最近的“佘祥林案”,都為我們說明了一點:輿論無節制的發表言論,某種程度上正在左右著司法,司法公正性正受到嚴重的挑戰。
我們并不能期待輿論都能夠從容冷靜、理智、嚴密地報道每一社會事件和案件,但司法機關能考慮的只是:證據所支持的事實及其法律規定。如果在事實與法律之外再有另外的因素影響和左右司法機關司法活動,出現所謂的“輿論量刑”和“輿論殺人”,那不是司法的進步,而是違背了獨立司法和司法公正的精神,如果司法在輿論面前經常“變臉”,那對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是一種極大的破壞,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司法無權威的社會,我們不能想像能夠保持社會的穩定,每一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護。
輿論在司法中合理作用的發揮是有其限度和邊界的。公眾對司法領域的影響主要在于對案件事實真實性的反映以及對司法行為的監督,在這些場景中,普通公眾較之專業人士更具備感同身受的能力,但不可越俎代庖對案件定性或做出判決。輿論的表達應該是一個理性的程序,要求的是一種形式理性,而理性正是法治的內在要求。法治是人民通過法律的治理,而并不是輿論直接對司法施加影響。對于普通公眾來說,應尊重司法部門依照事實和法律所作的專業判斷,百姓如果認為司法不公,應該依照法律程序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而不是采取過激的行動干擾司法。
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背景下,我們應該認真地思考,輿論與司法公正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既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媒體監督對司法公正的促進作用,同時又要盡可能地消除媒體大量覆蓋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這就需要探索建立理性的輿論監督模式,需要將輿論監督納入法制的軌道。建立合理的媒體監督模式,重要的是要尋求法律所保護的各種權益之間的平衡。正如前文所言,輿論如果過多地干預司法獨立,就會造成司法的不能公正。因此,在面臨這種選擇時,我們必須首先把握基本的法律價值判斷和思維邏輯,樹立理性的輿論監督。顯然,要取得二者之間的平衡,不僅是司法人員,普通民眾也需要這樣一種智慧和知識來平衡情和理、法律和道義、事實與輿論之間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