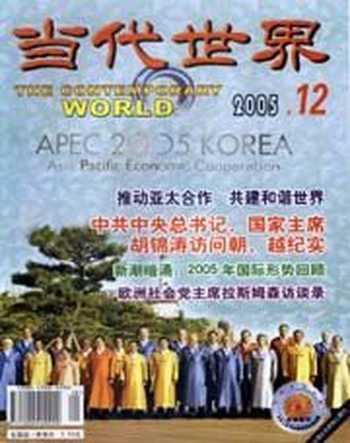印度人民黨沉浮的警示
季 平
2004年5月13日是印度近代政黨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普遍被人看好的印度人民黨(簡稱印人黨)在印度第十四屆人民院大選中意外出局,連續執政六年之久的瓦杰帕伊政府黯然下臺。這一變故使印度國內無數觀察家大跌眼鏡,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印人黨為什么會在如日中天的時候失去政權?這在過去的500天里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
印人黨傳奇般地崛起
印人黨成立于1980年4月,當時只是偏隅印度北部一個地方性小黨,在1984年的大選中,該黨只獲2席,而到1996年該黨席位猛增至161席,一躍成為印議會第一大黨。在短短的12年間席位增加了159席,席位數連年翻番,這是印度獨立以來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奇跡。
應該說,印人黨的崛起占盡了天時、地利與人和。
80年代末開始,由于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在大選中獲得單獨組閣所需的席位,印度進入了一個或是由少數派執政,或是由多黨聯合執政的時期,其結果是政局動蕩不定,政府更迭頻繁。在1989年12月至1999年4月的10年中,印度共組織了8屆中央政府,其中6屆只執政了一年左右,最短的只有13天。造成這種局面的客觀原因是長期在印執政的國大黨衰弱了,特別是在“三化”浪潮,即經濟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沖擊下,作為國大黨三大意識形態支柱的世俗民族主義、甘地主義和尼赫魯社會主義思想體系開始垮塌。這為印度政壇留下了政治真空,直接導致80年代末印度政黨政治多元化、地方化和種姓化趨勢的加劇,從而為印人黨的崛起提供了契機。
其次,隨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中心的東移,從80年代中后期開始,南亞國家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風暴中心外圍的影響越來越大,教派矛盾日趨激烈,尤其是1992年12月6日位于印度北方邦阿約迪亞市的巴布里清真寺被毀成為一個標志性事件。印度地處南亞次大陸的中心位置,“北背雪山、三垂大海”,西邊是伊斯蘭世界,石油國家與之隔海相望,東邊緊鄰的是穆斯林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孟加拉國,置身其間的印度教徒的自我意識不斷加強,另一方面作為少數民族的印度穆斯林群眾對其生存空間的狹小也感到恐慌,所以任何一點外部刺激都會重新點燃“印度教至上主義”的死灰,激化宗教矛盾。
第三,從印度的人文環境來看,印度教徒占印度總人口的82%。印人黨成立之時就已經成為了“印度教同盟大家庭”的當然成員,把自己與世界印度教大會(VHP)、國民志愿服務團(RSS)等印度教教派組織捆綁在一起,共同發起了“恢復羅摩盛世”、“重建羅摩神廟”等運動。隨著印度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對外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傳統的印度教徒對現代化所造成的緊張狀態和異質文化產生了強烈的反彈,印度教教派主義得到了主張捍衛印度教傳統文化和經濟民族主義思想人士的支持。以印度商人、律師、工程師、文官和知識分子為代表的“成功人士”于是紛紛加入到印度教復興主義者的行列中來了。
印人黨看到了這些有利條件,所以先期打出了“一種文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印度教理念,之后又宣揚“建(印度教大神羅摩)廟、修憲(廢除憲法中有關賦予克什米爾特殊地位的370條款)和實施統一民法”。這些政策主張具有一定的文化張力,尤其能得到城市中產階級選民的支持。加上一些所謂的世俗政黨,為謀自身利益,向“權利邏輯”投降,因而就不難理解印人黨發展如此迅速的原委了。
印人黨失利的三大原因
印人黨執政時間之長僅次于國大黨。6年間,印度政局基本穩定,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綜合國力有所增強,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印人黨敗北的結果就連反對黨也沒有想到。現在看來,印人黨失利的原因大致有三個方面:
首先,印人黨偏面追求高增長,忽視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因而未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與發展的理解和配合。印人黨執政期間,印國內生產總值實現了年均6.1%的增長率,尤其是執政后期,印經濟增長速度接近,甚至一度超過我國。印人黨提出在下一個“五年計劃”中,要實現年均8%至10%的增長速度,達到“使印在2020年成為發達國家”的目標。盡管印人黨也注意到要保持政治發展與經濟改革的良性互動,口頭上表示要維護社會政治的“平衡發展”,但印人黨并未真正重視一些社會經濟的老大難問題,特別是農業“靠天吃飯”、農村基礎設施落后造成發展瓶頸,以及農民收入偏低等的問題。印度經濟改革的受益面狹窄使既得利益者越來越富,社會兩極分化愈加明顯,過早地出現了社會轉型期的綜合癥。印人黨因而被指責為是一個“反農民、反窮人和反群眾”的政黨。
其次,印人黨的教派主義色彩尚未完全收斂,選民擔心教派主義思潮的抬頭會影響社會穩定。印人黨上臺后為盡快實現從反對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變,以總理瓦杰帕伊為代表的溫和派主張淡化教派主義色彩,承諾擱置三大教派主張,并努力與“印度教同盟大家庭”的其它成員保持距離,以此來重塑自身形象,傳承國大黨作為全國性政黨的責任感。但事實上,印人黨黨內強硬派守拙耐心不夠,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與溫和派的控制與反控制之爭接連不斷。尤其是2002年2月發生在古吉拉特邦的教派沖突讓選民進一步感到印人黨還有一個可怕的“隱藏著的行動綱領”。
第三,印人黨盲目樂觀,缺乏憂患意識,在戰術上輕敵,導致政策的取向性失誤。2004年2月,印人黨決定把原定于9月舉行的大選提前,主要原因是由于印人黨認為其政績驕人,“感覺良好”。2002-2003財年,印經濟有較好表現,GDP增長率為8.1%,尤其是第四季度GDP的增長率高達10.3%。外交領域也出現了多年來少有的和平景象,不僅理順了與美、俄、歐、日等大國或大國集團的關系,而且還改善了與中國和巴基斯坦等鄰國的關系。印人黨自信地認為,反對黨尚不具備扳倒它的實力,因而打出了“閃亮印度”的競選口號。印人黨內有人聲稱,這次大選已經不是誰輸誰贏的問題,而是印人黨贏多贏少的問題。黨內甚至一度還討論過,得到簡單多數議席后還要不要聯合其他小黨組閣的問題。
國大黨雖然倉促應戰,且內政外交政策主張與印人黨嚴重雷同,但卻因樹立了“親民”、“世俗”和“開放”的形象,得到選民的認可。
印人黨代表性的啟迪
印人黨沉浮的經歷應驗了“其興亦勃焉,其亡亦忽焉”那句老話,其經驗與教訓無論對于印人黨還是對于其它政黨都是值得借鑒的。
從印人黨的階級屬性來看,印人黨代表的是印度教中、高種姓階層的利益。盡管印人黨也曾與低種姓政黨結盟,推選賤民出任黨的高級領導人,還大量吸收非印度教徒入黨,但這種舉動往往被看作是印人黨的政治作秀。退一步講,即使印人黨不能贏得非印度教徒的支持,理論上也應能夠得到占人口絕大部分的印度教徒的支持,但是印人黨建黨25年來,得票率一直徘徊在25%左右,在本次大選中的得票率僅為22.2%。這一事實說明,印人黨并沒有真正成為印度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政治代表。
從印人黨的意識形態來看,印人黨借以發家的印度教教派主義思想并不是當今印度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印度教教派主義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固然可以成為凝聚印度教徒的強大思想武器,但這種主張“只有印度教徒的價值才是醫治印度政治弊病的靈丹妙藥”的宗教多數人主義思想,它忽視了印度社會多元化的現實,同時也嚴重地阻礙了宗教力量與世俗政權之間在真正意義上進行對話與理解。顯然,當今印度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教派之間或者是教派內部的矛盾,人們關注更多的是國計民生問題,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已經變得十分理性和現實。當兩億印度中產階級仰望天空的時候,他們看到的并不是印度教大神梵天、濕婆和毗濕奴,他們看到的是人造衛星和太陽能。因此,印人黨堅持的“印度教至上主義”思想和文化理念與當今印度的世俗化進程是格格不入的。
(本文責任編輯:劉萬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