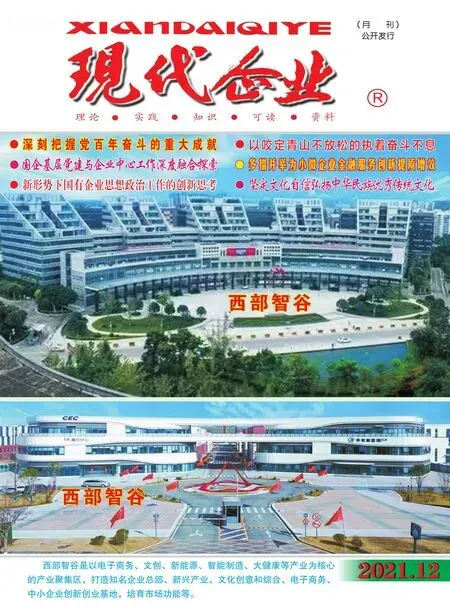公共部門改革注重人的因
尹宏禎 朱 宇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等都對政府管理進行大規模改革,其目標是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這就是盛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實踐中又被稱為“政府再造運動”。進入21世紀以后,新公共管理運動主張的“小政府”模式逐漸暴露出問題,特別是不能適應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求,從而遭到修正。一種新的理論模式應運而生,就是“新公共服務”。新公共服務這種模式的核心觀點是,政府應注重服務、關注社區、以人為本:如政府要服務而非掌舵、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新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對政府在社會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進行了全新的闡釋,對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大啟發作用。但是,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公共部門的改革,套用公共服務型政府模式的最大障礙不是機構和規章制度,而是人的因素。
一、來自公共服務部門的矛盾——人性的理性與非理性
薩繆爾森曾經指出:“市場經濟是我們駕馭的一匹好馬。但馬無論怎么好,其能量總有個極限……如果超過這個極限,市場機制的作用必然會蹣跚不前。”由于市場本身的缺陷,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務領域出現了市場失靈。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即一個人對某一公共物品的消費并不妨礙或者影響他人對該物品的同時消費,因為向一個或向多個人提供該物品的成本是相同的;同時具有非排他性,即一旦公共物品被生產出來就無法阻止他人對其消費,也就是說,排斥任何潛在的消費者從這些物品上獲益通常都是不可能的。公共物品的這些特征,與私人物品所具有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而在公共物品領域常常出現“搭便車”行為——即一部分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費用,而大多數人免費享用。在這種情況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就會紛紛采取不付費而搭便車的行為,私人因提供公共物品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損失而不愿投資,最終會導致公共物品的嚴重短缺。因此,在公共服務領域中,單純依靠市場機制是難以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的。從而政府理所當然地承擔起公共服務職能,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這樣既可以大大節約交易費用,克服經濟的外部性,又可以較好地解決公共物品消費中的公正性問題。
由上述可知,市場失靈是在一個前提下產生的:就是人是具有理性的,并且是不可改變的。正因為市場失靈,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才會出現。那么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下,政府就不會失靈嗎?政府在克服公共服務領域中的市場失靈時,也會出現政府活動的非市場缺陷——政府失靈:當政府政策或者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出現了。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組織和政府官員是理性自私的經濟人,他們以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為出發點,追求預算最大化,并不斷擴張組織規模。這勢必出現借社會公共利益之名行政府組織或官員私利之實的行為。另外由于沒有競爭對手,政府內部缺少降低成本、提高質量的激勵機制,從而導致提供公共物品上的高成本、低效率。因此。政府也很難通過“有形的手”來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出現了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或供給過度的問題。
現代社會中的人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復合體。從這點說,理性與非理性都是人的本性,它們不僅在人的實踐和認識中,而且在人的存在和發展中都有重要作用。在現實生活中,人需要理智地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組織的關系,不能為所欲為,而要按一定的“游戲規則”來行動。同時,社會活動正是因為有了個人感情意志的參與,才顯示出差異,才豐富多彩;也正是非理性因素,才使人顯示出激情,并在一定情況下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如忘我的工作精神、昂揚的斗志、高度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由此可見,理性與非理性在人的生存和發展中都起著重要作用,二者相輔相成。理性約束引導非理性,使人的生存和發展成為一個自覺的、有意識的過程,非理性在理性的指導下發揮作用,使人保持活力和積極性,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動力。只有兩者恰到好處地結合在一起發揮作用,才能推動工作進步和社會發展,才能開發人的潛能,展現人的能力,從而使人成為高度個性化的完整的人。而作為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的公共部門尤其需要公務人員高度的積極性,從這一點上說公共服務的質量取決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有效結合。
二、公共服務部門的關系型心理契約
既然在公共服務部門公務員都是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方面,如何利用這種人性更好的提供公共服務產品呢?人們在工作中具有非理性和理性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們在工作活動中表現出一種心理契約(心理學家謝恩Schein在1980年提出)。謝恩提出心理契約就是在組織中每個成員和不同的管理者以及其他人之間,在任何時候都存在的沒有明文規定的一整套期望。正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期望,有的人重視心理期望中的交易型成分,更多關注具體的、短期的和經濟型的交互關系(如組織因為員工提供的服務而支付報酬)。有的人重視心理契約中關系型成分,更多關注廣泛的、長期的、社會情感型的交互關系(如奉獻、信任等等)。當員工認為心理契約破裂時,以生氣、憤怒為主要特征的心理契約違背是否出現,取決于員工對心理契約破裂的解釋。這個解釋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歸因和對公平性認識的過程。影響員工解釋過程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員工對心理契約破裂或違背的歸因,另一個是員工所感受的公平性。如果員工歸因于公共部門故意違反契約,那么隨之的反應就會是負面的、激烈的,員工會對公共部門所為進行譴責,并降低自己的工作表現甚至離職。而如果歸因于雙方理解上的不一致,這種反應就會弱得多。如果員工把破裂的原因歸結于外部或者公共部門(代理人)的主觀不公,就更容易造成心理契約違背的感受。
1、決策程序不符合規范的。員工往往認定心理契約的破裂是不合規范的。如果員工認為導致該決策的程序是公平的,比如分配過程符合規定程序,對不同員工、在不同時間是一致的,并沒有受到個人私利和偏見的影響,那么員工會認為契約破裂是可以接受的。否則,心里契約違背的體驗就會發生。
2、溝通機制不通暢。員工關于公共部門義務的理解可能與公共部門整體的認識不完全相同。如果由于公共部門未對心理契約中的義務項目進行清楚的界定而導致員工的誤解,或者當公共部門代理人在傳達消極結果時,未給予充分的、清楚的解釋,會使員工認為自身的價值未得到足夠重視,因而將心理契約破裂解釋為不合理,從而產生心理契約違背。
3、補償機制不及時。在員工知覺到某項義務公共部門沒有履行或充分履行時,如果公共部門能及時在其他方面給予補償,員工對該補償項目的接受程
度可以抵償未履行的項目,心理契約破裂就越不會演化成契約違背。公共部門如果故意忽略或沒有及時做出反應,員工的情緒就會較為強烈。
4、較高估計自我價值。員工如果認為自己擁有不可替代的資源,如高的績效水平,與重要顧客的社會關系等,并且有能力獲得滿意的其它工作時,則會傾向于將心里契約破裂解釋成不能接受的,產生憤怒、受挫等情緒。
公共服務部門中的心理契約破裂會導致公共部門服務質量低下,影響正常的工作。同時,公共服務部門面對的服務對象是人民群眾,低劣的態度勢必影響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為以后公務員開展工作造成障礙。
三、如何改善公共服務部門
首先,注重提高員工在心理契約上的滿意度。員工的工作都是有一定目標、需求。比如獲得相應的報酬,擁有一份富有挑戰性且常干常新的職位,自身的工作得到賞識而被給予進修和發展的機會,在工作中能夠參與決策,希望有一個和諧的工作氛圍和一個幽雅舒適的工作環境等等。需求的滿足程度直接影響工作積極性與主動性的發揮。
其次,積極加強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部門內部的人才激勵機制。面對民營企業和合資企業“高薪挖人”的強大攻勢,公共服務部門要想吸引和留住高素質人才,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讓他們為公共部門的發展貢獻聰明才智。一方面,公共部門必須徹底改革其現行的呆板的、平均主義很濃的工資分配制度,要多角度,全方位建立具有部門自身特色的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應包括分配傾斜、機會傾斜、公正用人、全面關心等內容。
再次,幫助員工設計科學的職業生涯規劃。良好心理契約的構建,有利于公共部門對員工追求良好職業發展前景權利的尊重。公共部門的管理人員要善于誘導,讓員工在企業發展的同時自己也能得到良好的發展-因此,必須對員工進行科學的職業生源規劃,讓員工能在其所服務的企業中看到自己的未來和希望,以把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入到企業的發展中。同時,又要及時發現和處理員工工作和生活中所產生的實際問題,這些問題如不加以妥善處理,就可能產生思想問題,進而影響員工的精神狀態。
第四,樹立“做人民公仆”高度的責任感和榮譽感,把這種責任感和榮譽感納入人們心理契約的一部分。縱觀人類社會文明史的發展,人的社會行為總是要受某種理念的推動或引導,這種理念會影響人的行為和思想。因此,提高做人民公仆的責任感和榮譽感可以引導人們心理契約上的平衡感,從而提高為人民服務的質量。
第五,公共服務部門應該關注心理契約的變化,及時調整公共服務管理部門的人事政策。公共服務部門中的心理契約并不是一直不變的。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人們更重視安全、持續、忠誠,所以期望公共部門為個人提供公平升遷的環境、內部職業生涯規劃等。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人才的流動更強了,人們更重視對未來職業的適應能力,所以期望工作單位對個人附加價值公平報酬、提供應用廣泛的技能培訓。現在我國的公共服務部門的人事政策還停留在90年代以前的狀況,這不適應人才高度流動的今天,嚴重阻礙了公共服務部門的發展。因此,我國的公共服務部門應該改變對人的政策思路,這樣才能充分利用心理契約改革公共服務部門效率。
綜上所述,從人的需求層面看,人性有“好生、好樂、好智、好善、好美”的特性;從人的關系層面透視,人性具有道義性,而公共服務部門就是由這些不同人性的人構成的。可以說如何洞悉人性、尊重人性、利用心理契約改革我國的公共服務部門是徹底改變我國公共服務部門現狀的鑰匙。
(作者單位:四川省委黨校西南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