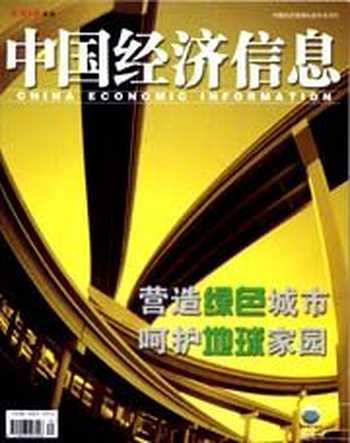從湖南“技工斷層”透視“民工荒”
馮 發(fā)
湖南省是全國第二大勞務輸出省,每年到外地務工的人員有數百萬人,2004年,更是高達880萬人。然而最近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公布的《關于湖南省用工緊缺的情況調查》卻顯示,湖南省局部地區(qū)已開始悄然鬧起了“技工荒”,尤其是加工制造業(yè)聚集的地區(qū),而出現(xiàn)在湖南的“技工荒”對目前沿海地區(qū)的“民工荒”似乎做出了注解。
“技工荒”蔓延
一個縣缺工6000余人。
自2005年1月以來,“紡織之城”永州市藍山縣的大小數百家毛織廠負責人便為招收毛織熟練工人感到頭疼。“這個月,我5次帶人到各個鄉(xiāng)鎮(zhèn)招人,但每次都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藍山縣第一家崛起的紡織廠——合利毛織廠廠長黃樹新眉頭緊鎖著說,每招聘一回,就把基本工資提高一成,直到月工資900元,才“挖來”12個熟練毛織工,但用工缺口還有25人。藍山縣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一相關人員介紹,截至今年2月,藍山縣缺工數已達到6025人,其中缺熟練毛織工人近5500人,占總缺口的90%。
藍山縣用工緊缺只是湖南湘南地區(qū)缺工的一個縮影。據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公布的數據顯示,湘南地區(qū)已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技工荒”,其缺口數分別為永州1.45萬人、郴州1萬人、衡陽2萬人,長沙市寧鄉(xiāng)縣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也缺各類技能人才2600余人。
有“麓谷”之稱的長沙河西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yè)開發(fā)區(qū)的眾多企業(yè)也正在被“技工荒”所困擾。一家生產點鈔機的企業(yè)就曾經向前來視察的政協(xié)委員們抱怨:企業(yè)擁有一流的技術,產品卻成了三四流的,問題就在于缺少高水平的技術工人。
在長沙河東的另一個國家級開發(fā)區(qū)——長沙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內,幾家工程機械企業(yè)也有類似的抱怨,而且他們招聘技術工人的廣告在一年之中基本上沒有中斷過。同行業(yè)間相互挖墻角的現(xiàn)象成了公開的秘密,一些高水平的技術工人甚至頻繁地在同行業(yè)的企業(yè)間流動。
今年4月,記者在邵東縣工業(yè)園采訪時也遇到類似情況,一些打火機企業(yè)由于無法在當地招收到工人。一家名叫順發(fā)打火機制造有限公司的企業(yè)去年底增加了幾條生產線,可直到目前才招到1/3的技工,主管生產的廠長羅肆軍還特意委托記者為他們招收工人。
為何會鬧“技工荒”
技能人才出現(xiàn)“斷層”。
有關專家在對長沙市技能人才現(xiàn)狀調研時曾有過這樣的基本判斷,長沙制造業(yè)用工需求較大,技能人才總量不足。
去年下半年,長沙市勞動力市場第三季度的制造業(yè)用工需求比第二季度增長33.59%。受地域性“民工荒”影響,沿海地區(qū)用人單位將招聘拓展到內地勞動力市場,吸引了部分勞動力向外移動,特別是中技類畢業(yè)生大幅“南下北上”,導致長沙企業(yè)用人需求得不到及時補充,空缺崗位增長近3成。
有數據表明,長沙高技能工人由原來占職工總數的21%下降到19.22%,其中,高級技師由0.4%下降到0.27%,技師由4.1%下降到3.26%,高級工由17%下降到15.69%。2003年,長沙市有3.28萬人參加職業(yè)技能鑒定,獲得高級技工資格證書的僅占1%。
過去,技術工人特別是擁有職稱的高級技術工人主要在國有企業(yè)當中。但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不容樂觀。
長沙思均達泵業(yè)有限公司總經理唐復健說,現(xiàn)在國有企業(yè)的技術工人主要來自以下幾批:上世紀70年末、80年代初,一批年輕人頂職進入企業(yè),并逐漸成長為具有一定水平的技術工人,但現(xiàn)在他們的年齡基本上超過40歲,在一線工作的也越來越少;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批技校生進入企業(yè),他們的年齡到了35歲以上;隨后企業(yè)面向社會招工,這批工人也成為主要技術力量。
唐復健說,當前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是,十七八歲進入企業(yè)當工人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斷層,工人梯隊青黃不接。而國有企業(yè)經過精減、下崗、改制等多輪改革,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形式,以50歲或55歲為界,“切”走了大量具有豐富經驗的技術工人,技術“傳幫帶”受到極大影響。
“培養(yǎng)一名高水平的技術工人需要漫長的時間,年輕人不愿意當工人,都往大學擠,技術工人從何而來?”唐復健說。
三大硬傷“趕走”技工
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就業(yè)處在對湘南地區(qū)用工情況進行調查時,發(fā)現(xiàn)“三大硬傷”制約著企業(yè)的招工、用工。
硬傷一:損害員工利益。2004年,永州市寧遠縣香港真雅毛織廠一口氣招了1000多名技工,而到了年底,欠下員工30多萬元的血汗錢,最后還是在政府幫助下,借款20多萬元“了難”。“像這種無視勞動者權益的情況,在湖南不少用工緊缺的企業(yè)中都存在。”
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就業(yè)處處長陳范勛說,湘南地區(qū)部分企業(yè)實行計件工資,員工工作時間每天超過12個小時,且一個月內只許休假一天;還有些企業(yè)拖欠員工工資,這都導致技工大量流失。
硬傷二:供需結構、產業(yè)結構失衡。調查表明,湘南地區(qū)就業(yè)市場內,18~25歲的青年技工就業(yè)最容易,男性即使沒有任何技能,三天內也能找到工作;女性幾乎來了就能就業(yè);而40歲以上的技工就業(yè)則非常困難。
制鞋、玩具、制衣等勞動密集型崗位,由于勞動強度大、報酬低,選擇的人越來越少,尤其是對青年技工越來越沒有吸引力;而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崗位,如焊工、車工等,月薪即使開到了2000元,也招不到合適的工人。
硬傷三:技工的無序流動。該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表示,農村勞動力基本上是靠親友介紹外出務工的,而湘南地區(qū)的勞動力需求信息無法通暢傳遞。同時,這里的一些企業(yè)靠壓低工資、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投入以實現(xiàn)低成本發(fā)展,也使技工逐漸“逃離”。
技工培訓亟待改革
教育體制制約技工培養(yǎng)。
業(yè)內人士認為,從教育管理體制來看,中等職業(yè)教育在普高教育中處于末位,高等職業(yè)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也處于末位,技校又處于職業(yè)教育中的末位,嚴重影響著高素質、高技能工人群體的培養(yǎng)。
此外,在技術工人的培養(yǎng)體系中,近年來,一些地方雖然出臺了一些激勵高技能人才培養(yǎng)和成長的政策措施,但這種政府發(fā)文、企業(yè)出錢的高技能人才激勵模式,由于尚未形成相互配套和銜接的機制,企業(yè)技能人才培養(yǎng)、評價、晉升、使用和待遇方面的政策難以落實,監(jiān)督實施的力度也不夠,影響了高技能人才隊伍的培養(yǎng)。
九三學社長沙市委在一份專題調研報告中指出,多頭管理、政出多門,職業(yè)教育標準不一,同樣也影響著技術工人的培養(yǎng)與成長。
九三學社長沙市委副主委劉曼曼說,目前職業(yè)教育管理體系,職業(yè)中專、職業(yè)高中、高職等屬于教育部門管理,技工學校和職業(yè)培訓與技能鑒定屬于勞動部門管理。由于政府統(tǒng)籌力度不夠,缺乏宏觀上的統(tǒng)一管理,質量要求和經費投入缺乏基本的統(tǒng)一標準,造成了職業(yè)教育體系內部的混亂狀況,名稱亂、性質亂,同樣是中職教育,有中專、職業(yè)高中、成人中專和中等技工學校;同樣是高職教育,有高專、高職、職業(yè)大學與高級技工學校等。它們在職業(yè)教育、勞動準入、就業(yè)培訓、畢業(yè)生待遇等方面的政策規(guī)定,出自多門且不配套。
目前,長沙市多數行業(yè)部門和大中型企業(yè)不再保留指導和舉辦行業(yè)、企業(yè)職業(yè)教育的職能,相繼停辦職業(yè)學校或大幅度減少招生規(guī)模。劉曼曼說,一些企業(yè)在改制過程中,將所辦職業(yè)學校改作培訓中心或與企業(yè)分離,導致職業(yè)教育資源嚴重流失。另一方面,資金的缺乏和市場人才流動,使企業(yè)缺乏抓職業(yè)教育和培訓的積極性。大多數企業(yè)沒有員工的培養(yǎng)機制和規(guī)劃,更多的是把眼睛盯著人才市場,重引進,輕培養(yǎng)。
低技術陷阱問題
去年開始席卷珠三角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勞動力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xiàn)在市場對技能型人才的供求矛盾上。
“低工資,最先跑掉的當然是有技術的工人。”這是勞動部門的說法。相對于普通工人,有技術的工人更有條件尋求報酬更高、環(huán)境更好的工作崗位。
“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低工資高競爭力”,正陷入一個低技術的陷阱。由于勞動力太便宜,廠家不愿意投資更新技術、提高工人的素質,因為新技術雖然節(jié)省人力,卻需要投資。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買設備的錢還不如用來多雇幾個工人合算。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術的外商,在中國設廠也寧愿多雇些廉價工人,少用昂貴的先進設備,大大影響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低工資、低教育、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高勞工淘汰率,已成為我國現(xiàn)有經濟發(fā)展模式附帶出來的問題。
“這有點像飲鴆止渴。”一位人力資源專家分析說,勞動力越便宜,企業(yè)越不愿意投資新技術、新設備。另一方面,為了保證產品競爭力,工人工資就不會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無限供給”以及“低勞動力成本”的優(yōu)勢,將會成為制約企業(yè)發(fā)展的一大瓶頸。
有關人士警告,低工資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huán)的開始。盡管許多員工已經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和能力需要提高,但幾乎沒有可能進行學習“充電”,因為自己微薄的工資僅能維持城市的高成本生活。同時,高昂的教育收費提高了進城務工人員和貧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門檻,形成這一龐大人群的“教育荒”,進而導致“技工荒”的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