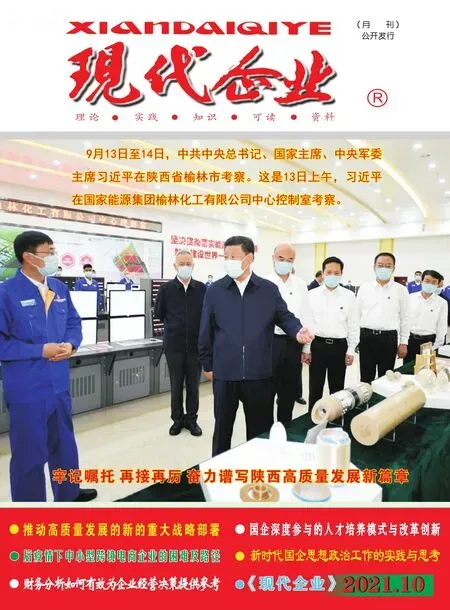企業和諧發展的博弈探析
劉建勇 王火欣 陳贊贊 魏 明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和諧社會”新理念。胡錦濤總書記最近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作了進一步闡述:“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是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的新突破,也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認識的新發展。因此,企業的發展也必須建立和諧的發展理念。
企業、自然環境、政府三者之間存在不和諧
什么樣的企業是和諧企業?目前對此并沒有什么權威的定義。但可以肯定的是,和諧企業的最基本特征是企業的和諧發展必須建立在企業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企業價值與員工個人價值之間的和諧、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和諧、企業與社會公眾、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和諧關系之上。然而,當前企業與自然環境和政府之間存在不和諧之處。對于企業來講,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其目標,所以企業為了追求價值最大化而不考慮對環境的污染和危害,隨意排放廢水、廢氣等污染物,對自然環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不利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違背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然而,環境是一類重要的公共物品,包括空氣、水等。由于環境資源的公共性和“搭便車”現象的存在,使得人們“委托”政府來保障環境公共物品的供給。政府的目標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為保證其供給的產品—環境公共物品的質量,需要對企業排污進行管制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實現企業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那么,對于企業的排污行為,政府到底該不該監管,監管力度多大才能達到企業、自然與政府的和諧發展。故企業的排污行為與政府的監管行為二者之間存在博弈,以下將通過建立博弈模型進行分析。
博弈模型
一、模型假設
第一,企業和政府是該博弈的兩個參與人,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價值最大化,政府的目標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第二,企業和政府雙方進行動態博弈,一方先行動,另一方觀測到前者的行動后相機行動。第三,博弈雙方都知道自己在每種狀況下的支付函數,而且可以觀察到對方在自己選擇行動前的行動。
二、模型博弈次序和戰略選擇
政企博弈是有先后順序的,我們根據現實生活中的常識來決定政企動態博弈的次序。首先,企業在是否排污問題上做出選擇,接下來政府做出監管與不監管的選擇,然后企業選擇對污染物進行凈化和不凈化(即接受罰款)的選擇。行動具體順序如下:企業首先決定排污還是不排污,若不排污,則博弈終止。如果排污,第二個階段由政府做出選擇,如果政府不管制,則博弈終止;第三階段是個單人博弈,由企業做出選擇,企業選擇對污染物進行凈化還是不凈化(即接受政府罰款),此時博弈完全終止。政企動態博弈的博弈樹如圖所示。圖中向量的第一個數字是政府的支付,第二個數字是企業的支付。
政企動態博弈的博弈樹
三、博弈雙方的效用函數
1、博弈樹中支付向量中各個變量表示涵義。①假定企業不排污時,企業的收益為r,政府的收益即社會福利值為f。②企業排放的污染物數量為w,因排污而多生產的產品數量為x,政府的監管概率為t。③企業排污后,企業增加的收益為A(w),導致的社會福利損失為B(w);假定A(w)和B(w)都是w的增函數,即排污數量越大,增加的收益越多,同時對社會福利造成的損失越大。④企業因為排污而增加的產量給社會帶來的收益為C(x),x代表因排污而增加的產量。⑤政府的監管成本為D。⑥企業若對污染物進行凈化,其發生的凈化成本為P(w),P(w)為w的增函數,即排污數量越大,所花費的凈化成本越多。⑦若企業不對污染物進行凈化,政府對其罰款額為E。
2、博弈樹中各支付向量的涵義。①企業不排污時,政府也不需要對其進行監管,企業的收益為r,此時社會福利價值為f,雙方支付函數為(f,r)。②企業排污,政府不管時,企業的收益為r+A(w),社會福利價值為f+C(x)-B(w),雙方的支付函數為[f+C(x)-B(w),r+A(w)]。③企業排污,政府管制;若企業接受對污染物進行凈化,凈化支出為P(w),因此企業獲益r+A(w)-P(w),政府的監管成本為D,此時社會福利值為f+C(x)-D,雙方的支付函數為[f+C(x)-D,r+A(w)-P(w)]。④企業排污,政府管制:若企業不對污染物進行凈化,政府對其罰款額為E,此時企業的收益為r+A(w)-E,政府的社會福利值為f+C(x)-D-B(w)+E,雙方的支付函數為[f+C(x)-D-B(w)+E,r+A(w)-E]。
四、政企動態模型的Nash均衡
研究圖1可以發現,政企博弈是一個有限完美信息的動態博弈,該博弈的過程包括三個決策結,每個決策結都是單獨的信息集,每一個決策結都開始一個子博弈;因此,原博弈包括兩個子博弈。最后階段,企業選擇凈化與否是一個單人博弈。對于這種含有子博弈的動態博弈問題,我們采用逆向歸納法來求解。
在博弈的最后階段,企業選擇凈化還是不凈化取決于企業的收益,若r+A(w)-P(w)≥r+A(w)-E,即P(w)?芨E,則企業會選擇凈化;否則,企業將會選擇接受罰款,這將不利于企業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所以,要想使企業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政府應加大罰款力度,使罰款支出大于對污染物進行凈化的支出。這時的納什均衡為,政府將選擇監管,企業將選擇凈化,即(凈化,監管),這將有利于企業和環境的和諧共處及可持續發展。
在博弈的第二階段,假設企業選擇凈化,并且政府監管的概率為t。若[f+C(x)-D]×t+[f+C(x)-B(w)]×(1-t)=f+C(x)-B(w)+t×[B?穴w?雪-D]。因為t>0,所以,當B(w)-D>0,即B(w)>D,也即監督成本小于因排污而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時,政府選擇監管,此時的納什均衡為(凈化,監管)。反之,當D>B(w),即監管成本大于因排污而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時,因為存在r+A(w)-P(w)?芨r+A(w)或者r+A(w)-E?芨r+A(w),此時政府不管,則企業會肆無忌憚地排污。所以,當監管成本小于因排污而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時,政府將選擇監管;若監管成本大于因排污而導致的社會福利損失時,此時政府不予監管,這樣企業將會肆無忌憚地排污,這將不利于企業與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
對于排污量比較小的企業,因排污而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小于政府的監管成本時,政府將不予監管;當排污量大到一定程度,即因排污而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大于政府的監管成本時,政府將會選擇管制。政府要想對企業的所有排污行為進行監管,必須采取恰當的對策降低監管成本。
在博弈的第一階段,對于污染量比較小的企業,因為此時監管成本大于因污染而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企業知道政府將不會監管,又有A(w)>0,即r+A(w)>r,企業將會選擇排污。對于污染量比較大的企業,此時監管成本小于因污染而給社會造成的損失。企業是否排污將取決于監管力度的大小。仍然假定政府監管的概率為t,則企業排污時的收益為[r+A(w)-P(w)]×t+[r+A(w)]×(1-t)=r+A(w)-t×P(w),若r+A(w)-t×P(w)>r,即t<A(w)/P(w),又有0<t<1,所以只要A(w)/P(w)>1,即A(w)>P(w),也就是說企業因排污而增加的收益大于因此而發生的凈化支出(或罰款支出)時,企業將會選擇排污。若r+A(w)-t×P(w)<r,則t>A(w)/P(w);又有0<t<1,則A(w)/P(w)<1,即A(w)<P(w);所以,當A(w)<P(w)并且t>A(w)/P(w)時,企業將會選擇不排污。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明確三點:第一,政府對企業的排污行為是否進行監管,與政府監管成本的大小有關。若政府的監管成本大于因企業排污而給社會造成的損失,政府對于企業的排污行為將會不予監管,這時企業將會選擇排污。第二,若政府的監管成本小于因企業排污而給社會造成的損失,政府對于企業的排污行為將進行管制;此時,企業選擇排污與否與因排污而增加的收益和因排污而發生的凈化支出(或罰款支出)有關。若企業因排污而增加的收益大于因排污而發生的凈化支出(或遭受的罰款支出)時,企業將會選擇排污。若企業因排污而增加的收益小于因排污而發生的凈化支出(或遭受的罰款支出),并且t>A(w)/P(w)時,企業將會選擇不排污。第三,若政府的監管成本小于因企業排污而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并且企業因排污而增加的收益大于因排污而發生的凈化支出(或遭受的罰款支出)時,此時企業將會選擇排污并且政府也將對其進行監管。此時政府對企業的排污行為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要求企業對污染物進行凈化,另一種是對企業的排污行為進行罰款。企業選擇何種方式取決于罰款支出與凈化支出的大小,若罰款支出大于凈化支出,企業將選擇對污染物進行凈化,反之將選擇接受罰款。
(作者單位: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