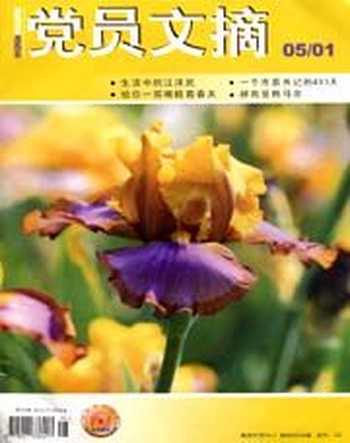一個市委書記的493天
高 浪
好問的“乘客”
2003年4月,非典期間,呼和浩特市街上出租車生意很差。一天,一位中年人上了出租車司機王玉海的車。
這位乘客很好問,一會兒問呼和浩特的道路建設怎么樣,路燈亮不亮,一會兒問出租車停靠點的設置如何。王師傅如實地說:“呼市的路,就像一條大拉鎖,挖了修,修了挖,路總是不平坦,苦了我們司機。”
快下車時,這位中年人說:“請你相信,以后市區不會出現這種現象了。”王師傅覺得這位乘客很神秘,便笑著問:“你是干啥的,夸這樣的海口?”
這位乘客說:“我叫牛玉儒,是新來的市委書記。”
4月10日,剛過50歲的牛玉儒從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職位上,調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書記。
2003年6月25日,牛玉儒通過電視,莊嚴向全市人民承諾:用4年半的時間,辦成三件事。一是經濟總量在現在基礎上再翻一番;二是把首府城市建設得更美麗、更有魅力;三是使城市居民和農民的收入實現跨越式增長。
就這樣,市民們從電視上認識了新來的牛書記。
牛書記第二次打車,就被出租車司機楊樹林認出來:“您這么大的官兒還坐我們出租車?”牛書記笑了笑,問楊師傅:“您對政府的工作有什么意見?”楊師傅向牛書記反映了上公廁難的問題。
牛書記臨下車時說:“放心吧,你說的事很快就會解決。”
果然,在很短的時間里,呼市各主要街道和一些小街巷的廁所多了起來,而且一律免費。后來,楊樹林逢人就說:“沒想到,我一個出租車司機的話,牛書記還真當回事。”
能累死一頭牛的人
呼市的工作人員很快發現,新書記“活力十足,不怕累”。
牛玉儒在呼和浩特工作不足500天,除外出200天和生病住院3個月外,他的車在本市跑了5萬多公里。
一次,他帶了一個工作組外出招商引資。從呼和浩特到珠海,跑深圳赴銀川,5天跑了5個城市,每到一個地方不是考察就是洽談,日程安排得非常緊。
在返回呼市的火車上,大家都疲乏地癱在鋪位上。火車進入呼市,牛玉儒問工作組的幾個年輕人:“下了火車,我們是去辦公室,還是到哪里?”
“還要干活啊?”被問的幾個人面面相覷。牛書記看了他們一眼,笑了。然后說:“好,放你們半天假。”他自己下火車后,直接去了辦公室。
牛書記的拼命精神在呼市是出了名的,一位干部說,跟著牛書記跑,能累死一頭牛。
這點不僅牛書記的下屬有感受,外省的投資商也深有感觸。2004年元旦剛過,牛玉儒到浙江華門房地產集團公司考察,牛書記一行又是談又是看,從早上8點一直到晚上12點半,回到賓館后,負責接待的集團副總經理章佳堯又吃驚地聽牛書記說,還要乘第二天早上5點的班機返回呼市開會。“哪里有這么忙的市委書記?連個安穩覺都不睡?”
第二天凌晨4點,當服務生叫牛書記起床的時候,發現他已經去了機場。章佳堯他們感動不已,集團老總說:“牛玉儒這個人真是了不起,為了地方發展竟操勞成這樣!到老牛那里投資,我放心。”
短短幾百天里,一批帶動力強、發展前景好的大項目相繼在呼市落地。連續兩年,呼市的主要經濟指標增速位居全國27個省首府城市的前列。
當然,讓市民感受最深的是增加了工資。市財政兩年里拿出了1.4億元給干部職工增加工資,人均增資700元。
發火的書記
牛玉儒平日里是個隨和的人,不大批評人,但在他的秘書李理的記憶里,牛書記在呼市至少發過四次火。
第一次是牛書記視察呼市城建工程時,發現便道鋪裝的質量有問題,他左看右看,越看越氣,忍不住回頭罵相關負責人:“這可是老百姓的血汗錢哪!這樣的質量怎么向群眾交待?與其讓老百姓罵我們,不如我罵你們。”
另一次,是牛書記在散步的時候,發現盲道中間立著一根電線桿,他繞了一圈,就生了氣:“這盲道是怎么鋪的,這哪叫便民,是害人!”
再一次,正值一天中午下班,牛書記發現有段路堵車,他下車一看,是施工挖了馬路,當即電話批評有關責任部門:“這不是多大的工程,為什么不能晚上干?現在是下班時間,我們要多給百姓造福,少給添堵!”
第四次是2003年5月17日,《呼和浩特晚報》登了一條消息《這15戶居民啥時能喝上自來水》,反映15戶居民停水一年未得到解決的事情。牛書記讀了大怒,作出批示:“請市自來水公司的領導讀一讀這篇報道。群眾反映已一年多,是什么原因使這個并不復雜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我看,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一些同志頭腦中‘三個代表思想太淡薄!你們在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的同時,舉一反三,認真反思。請新聞媒體繼續監督。”
不到24小時,15戶居民跑了一年沒有著落的吃水難題就給解決了。
守法的領導
牛玉儒到呼市赴任時,很鄭重地對秘書說:“現在我到呼市當書記,權力會更集中,這樣可能找你的人就多了,所以你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凌駕于他人之上。”為此,牛玉儒對秘書“約法三章”:第一,要尊重其他領導同志和周圍群眾;第二,不能打著他的旗號辦私事,不能代收禮品和禮金,一律拒絕之后也不用告訴他;第三,多學習,少應酬。
呼市國土資源局局長李樹貴說自己“很有福氣”:“地方要發展,需要國土部門提供土地。一邊是法律,一邊是當地政策,土地部門往往受夾板氣。但牛書記不會給國土部門出難題。”
呼市招商引資最大的項目漢鼎光電有限公司,是牛玉儒三赴廣東引進的臺灣建鼎集團電子產業項目,初期投資2億美元。但是正是這個項目,投資方當初看中的1000多畝土地,一半以上屬于不允許動用的耕地,投資方和區政府就找牛書記要“特殊政策”。牛玉儒作出了立足長遠的決定:地方利益不能跨越法律。一個月后,投資方放棄了原來的用地方案,另選了符合規劃的土地。
2003年8月,一個涉嫌貪污罪的處級干部被拘留,他的親友托人跟呼市檢察院檢察長云布俊打招呼說:“我們可是找過牛書記說了好話的。”不久又來問:“牛書記跟你說過沒有?”云布俊答復說,沒有。一次向牛書記匯報工作時,云布俊順便問了一句:“這個案子涉及自治區機關的一個處級干部,他們跟我說找了您了,找過您沒有?”牛書記回答:“不管找誰,進入法律程序的就按法律程序辦,該咋辦咋辦。”
“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兒子”
在家鄉通遼,牛玉儒是犯了“眾怒”的,親戚們對他的一致評價是“不近人情”。讓親戚們“寒心”的例子比比皆是。牛玉儒在呼和浩特市任市委書記和在包頭市任市長期間,他想盡一切辦法解決了幾萬人的下崗再就業和“4050”困難群眾就業問題,可是他卻幾乎拒絕了所有兄妹、親戚、同學和朋友幫忙找工作的請求。
牛玉儒家兄妹6人,5個是普通百姓,還有下崗近10年沒有工作的妹夫。二叔從小將他撫養成人,可二叔家的孩子大多在農村務農,惟一的姑姑是廁所清掃員,姑父和大侄兒至今在通遼市蹬三輪車。牛玉儒的妹妹牛繼紅說:“多少年來,三哥為素不相識的老百姓辦過無數實事兒、好事兒,可親戚們卻認為他是個‘六親不認的官兒。”
牛玉儒三叔的兒子牛勇智在醫療器械管理站當了8年站長,希望得到提拔。2001年3月,牛玉儒作為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到通遼市考察工作,牛勇智特意到賓館看望堂兄,托他在市領導面前說句話。
牛玉儒回答說:“這話不能說,要靠實力去競爭,我相信你。”
一次去呼市出差時,牛勇智到牛玉儒的辦公室,聽到他在接電話,是牛玉儒一位親戚要結婚,托他找幾輛政府的轎車。牛玉儒問:“這樣吧,你需要幾輛車?”對方說5輛,牛玉儒說:“那行,我明天給你派5輛出租車迎親去,我出錢。”然后撂下電話。
2004年春節,牛玉儒回通遼時特意到農村看望對他有過養育之恩的二叔。牛玉儒6歲喪母,他在家里6個孩子中排行第三。牛玉儒的父親是國營五金公司副站長,經常出差,就把他和另外兩個孩子送到鄉下和二叔一起生活。看到二叔一家至今仍然住著幾十年前的土坯房,他心酸之余,留下3000元錢幫助二叔修新房。回到自己家,牛玉儒流淚了,對妻子說:“我是牛家最不孝的兒子。”
一個硬漢的最后90天
2004年4月22日,在一次例行的健康檢查中,牛玉儒被檢查出是“結腸癌肝轉移”。
可怕的消息首先擊倒了他的妻子謝莉。她和牛玉儒結婚24年來,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加起來不到10年。
知夫莫如妻。謝莉知道丈夫是個工作起來不要命的人。到呼和浩特工作后,牛玉儒更加忙碌了。一次,他出差回來很晚,謝莉等他到12點,就睡著了。早上醒來,發現他的東西在,人已不知去向。打電話才知,他已在去往鄂爾多斯的路上了,妻子哭了:“你這么干,到底還要不要命了?”他說:“我現在必須得這么干,等將來我退休了,一定好好在家陪陪你。”
可是,謝莉沒等到這一天。
4月26日在北京住院那天,牛玉儒懇求大夫盡量在“五一”長假期間把手術做完,爭取3天下地,7天拆線,10天后就能回去工作。
待體力稍有恢復,躺在病床上的他就開始辦公了。
有一次,女兒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故意給他講笑話,解除他的疲勞。他眼睛盯著女兒,看似在認真聽孩子講,可聽著聽著,忽然從他嘴里冒出一串工作電話號碼,要女兒馬上給他撥通。女兒再也笑不出來,抱著父親大哭。
在北京,每次化療結束,他就急著要回呼和浩特。住院3個月,他就回去過了3次。
牛玉儒最后一次回呼市,是參加7月份市委九屆六次全委會議。會前的一天,牛玉儒讓妻子準備參加會議的衣服。可謝莉傷心地發現,他的衣服大都不能穿了。原來2尺9寸的腰圍,現在都不到2尺3寸了。
牛玉儒沉默了一會,又開心起來,說:“就多穿幾件內衣吧,顯得胖些,別讓同志們為我擔心。”
看著他興致很高地在衣鏡前一件件往上套著衣服,眼淚模糊了妻子的視線,她極力克制著自己的感情,違心地安慰他說:“已經很合體了。”
第二天一早,牛玉儒穿著整齊、精神飽滿地出門開會。中午12點,他臉色慘白,被攙扶著回到家,無力地倒在床上,長時間地一動不動,妻子和女兒都被嚇壞了。后來才得知,他在大會上作了兩個多小時的即興講話……
8月10日,牛玉儒進入昏迷狀態。在又一次昏睡醒來后,他蠕動著雙唇,兩眼看著妻子,眼神是從未有過的溫和,很快,他的眼眶溢滿了淚花……
8月14日,牛玉儒與世長辭。這天,他在呼市工作剛剛493天。
8月20日8時不到,通往大青山殯儀館的的路上,長長的吊唁隊伍延伸了數公里之長,自發趕來送別的各族群眾越來越多……
此時,天空陰沉,如絲細雨綿綿而下,如泣如訴……
(華之、君華、張源、世明、寶珊、衛東、彥子、張波薦自《南方周末》 原標題為《一個市委書記最后的493天》 本刊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