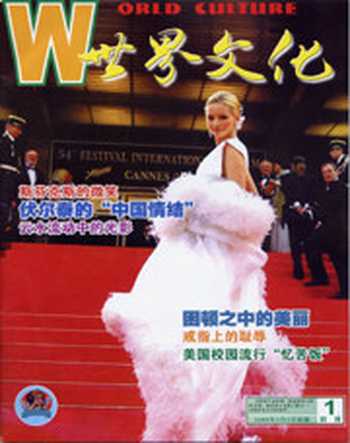陽光下的激情與渴望(上)
康 弘

19世紀西方美術的中心在法國,主宰法國畫壇的仍然是有勢力的官方學院派。19世紀后半葉,法國畫壇上一批有才華并且志趣相投的畫家聚集在一起,他們蔑視官方所推崇的矯飾、虛偽的學院繪畫法則,一反歐洲數百年來只在畫室中作畫的傳統習慣,摒棄了從18世紀以來畫面變化甚微的醬褐色調,走出畫室、奔向森林、鄉村、草地、海灘……。他們喜愛陽光和大氣,用畫筆表現出對自然的真實感受,追求稍縱即逝的直接印象,如醉如癡地沉浸在瞬息萬變的自然中,頑強地在烈日下苦苦地探索著光色的微妙變化。他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營造的絢麗多彩的畫面上,發掘著光與色的美。落選沙龍一年一度的巴黎沙龍的權威性足以使藝術家獲得或喪失榮譽,在沙龍中獲得成功的人物享受到的財富和威望是其他藝術家所無法比擬的。由于當權者所控制的評選委員會竭力支持那種媚俗的正統藝術,他們欣賞的是這樣的藝術:很強的故事性,精致完美的技巧和公式化的構圖。而這正是具有革新精神的藝術家所反對的。1863年,巴黎沙龍由于評審委員會的特別苛刻,使得3000名藝術家送來參展的5000余件作品的五分之三落選,這一事件引起美術界很大震動,稱這是場大屠殺,堆放遭拒作品的大廳簡直是座墳墓。藝術家憤怒的怨聲傳到了拿破侖三世的耳中。法國政府為了籠絡人心,平息落選者的不滿,拿破侖三世傳下旨意:“另辟一室展出被拒絕的作品,讓群眾評定藝術家的不滿是否有道理。”皇帝以寬容的姿態同意舉辦“落選者沙龍”,將所有于當年未被沙龍接受的作品單獨展出。落選者沙龍使學院派的權威性一落千丈。
裸體風波
在落選沙龍的大廳里,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引起人們的嘩然。官方沙龍曾通過拒絕這幅畫而警告他,一個令人起敬的展覽會是不能容忍寫實裸體畫和華麗而俗氣的色彩的。但“落選者沙龍”的出現,使這幅畫得以展出。畫上展現了幾個姿態悠閑而慵懶的巴黎上等社會青年在塞納河岸的一片樹蔭地休憩并午餐,一個手支下巴的裸女坐在中間,露出得意的神態,他們面前堆放著衣服和食物,遠處還有個浴女正從池塘邊走來。
當拿破倫三世蒞臨展覽會看到這幅畫時臉色驟變,氣憤之余大責其“不道德”、“有傷風化”。皇后也背過臉去不愿多看,皇帝一氣之下竟然宣布以后再也不搞落選者沙龍了。
觀眾也對這幅畫感到難以接受,畫中流露出了19世紀巴黎奢靡生活的浮華庸俗,而更加令巴黎人惱火的是,妓女成了作品的主角。“裸體風波”使馬奈成了巴黎人街頭巷尾的議論對象。與此同時,他又完成了另一幅作品《奧林匹亞》。他在這幅畫中立場鮮明地向宮廷沙龍發起攻擊,以蔑視沙龍的威嚴。
這幅《奧林匹亞》畫的是位橫陳床上的裸女,她雙眼毫無羞恥地直視著觀眾。古希臘圣殿奧林匹亞是傳說中眾神的聚居地,也是美神的所在地。馬奈把這個稱號賦予一個現代巴黎的下等妓女。馬奈借助藝術的神圣名義,在傳統的禮儀面前來炫耀這個紅頭發的裸體妓女,為的是宣泄社會對他的惡意和對道德家們表現出傲慢無禮。
這幅作品引起了巨大騷動,巴黎人發現,畫面上幾乎每一個細小的細節都在刻意侮辱著巴黎人的道德觀念和審美習慣。當人們想到馬奈在將黑人和黑貓描畫進畫面的時候,嘴角上一定流露出了輕蔑的微笑時,巴黎人憤怒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報紙和文藝評論都爭先恐后地對此畫進行嘲罵。巴黎人確信他的行為是蓄意地冒犯,這一題目和畫面是對藝術史發出的極其傲慢的挑戰。
正因為奧林匹亞刻畫的是一個下賤的妓女,所以它在藝術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為藝術家們贏得了兩項基本的自由:一個是它使藝術家在描繪女性裸體上不必再拘泥只刻畫那些令人敬畏的女神或仙女,而可以直接在畫中描寫人間凡女;另外它使藝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藝術家已經不再依賴于宮廷的庇護,而走向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奧林匹亞以一種鋒芒畢露的姿態深深地刺痛了那些平庸的畫家,這個形象的出現顯示出馬奈對表現對象的直率性。因此這幅畫展出后遭到學院派畫家的猛烈攻擊,有人將它說成是對道德和藝術的侮辱與挑戰。但年輕一代的畫家們都報以熱烈的掌聲。他們認為馬奈在他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種奇異的力量,藝術史上還從來沒有一件作品能產生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未來的印象派畫家們把馬奈看成他們的精神領袖。
蓋爾波瓦咖啡館
這次畫展后,巴黎有才華的年輕畫家走到一起,定期到蓋爾波瓦咖啡館聚會,交流思想、切磋技藝。謙遜、熱心、具有凝聚力的馬奈成了中心人物,莫奈和畢沙羅是這個集團的重要組織者,作家左拉是他們的喉舌和積極保衛者。盡管成員在性格和思想上有著巨大的分歧,但對官方藝術的鄙視和在常規之外尋求真理的決心使他們聯合在一起。
印象派的誕生
由于作品總是被沙龍拒之門外,莫奈提出搞個獨立展覽,跟沙龍對抗,得到了畢沙羅等畫家的大力支持。1874年3月25日,在著名作家、漫畫家和攝影師納達爾的工作室,29位畫家聯合舉辦了一次“無名畫家展覽會”。共展出165件作品。
這次聯合畫展,改寫西方藝術史。這群叛逆者的作品著色怪異,下筆粗放,以簡樸的日常生活為題材,而不隨時尚去繪畫端嚴人像和宏偉的歷史場面。那次畫展是對當時法國主流文化和主流藝術致命的雙重打擊。畫展上,莫奈一幅描繪河上日出的油畫《印象·日出》成為焦點。批評家路易·勒魯瓦借這幅《印象·日出》之名,以“印象”來挖苦他們,當時批評家形容一個畫家的作品像速寫似的、沒有畫完的性質時才用“印象”一詞。他對這個展覽進行了大肆地攻擊,不無嘲弄地把這個展覽稱作“印象派畫展”。西方藝術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畫派由此而得名。
飽受奚落
《無名畫家展覽會》是對陳舊的畫壇的一次宣戰,是一場悄然興起的繪畫革命。這次展覽所展出的作品代表了新一代藝術家的新追求,它打破了百年來傳統觀念的束縛。然而當時大多數觀眾和藝術批評家對這種藝術革新不能接受,且充滿敵視。
兩年后,莫奈等印象派畫家舉辦第二次畫展,這一次正式命名為印象派畫展。但展出并未贏得人們的認同,留給畫展的仍然只有嘲笑和譏諷。有人在《費加羅報》上撰文罵他們是:“五、六個瘋子,其中一個是女人。”
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印象派終于有權利在一間大廳里展出他們的作品。宣稱自己的職責是盡力阻撓印象派展出的讓·萊翁·杰羅姆,聽到印象派作品已被世博會審議委員會接受,氣急敗壞地大叫:“不,不要這些該死的印象派,不,不要那些破爛貨!”世博會開幕那天,當共和國總統洛佩走到印象派展廳前,他伸出雙臂擋在門口:“總統閣下,請留步,這里面是法蘭西的恥辱!”但是杰羅姆已經回天乏術。
從1874———1886年這樣的展覽共舉辦了8次,在前3次展覽中,這些印象派畫家們的展覽并未受到當時人們的歡迎,因為他們的繪畫觀念和在繪畫形式上的創新,破壞了人們長期以來的審美習慣,人們不能容忍這種破壞,拿出各種手段來打擊印象派畫家的狂妄和自大,以維護住舊有的審美習慣和觀念的平安。然而年輕的印象派畫家在人們對這種新的藝術手法與觀念的驚訝、恐懼與唾棄聲中,以一種全新的視角、以對光和色的獨特表現和對繪畫語言的大膽創造而令世人矚目,開了一代繪畫之先河。
有意義的貢獻
印象派第一次聯合畫展被認為在兩方面具有危險的激進傾向:他們的創作及其欣賞要求主觀的參與,他們認識到畫家不必為了尋找題材而鉆進文學的故紙堆,也不必在神秘的神話和傳說中苦苦搜尋。他們的主題貼近各種傳統和規范之外的生活,尤其是被學院派藝術傳統置之不顧的主題和表現,都進入了印象派畫家們的畫面之中。如:熙熙攘攘的街道,星期天的郊游,草地或游船上的午餐,花園或街角的舞會,行刑的場面,事務所辦公室的景象,舞女,樂隊,酒吧間等。過去的繪畫一直是為繪畫之外的目的而存在,像祭壇畫、裝飾畫、歷史畫、肖像畫。直到印象派,繪畫才擺脫了這些繪畫之外的意義,逐漸成為真正意義的獨立繪畫。
因為他們在方法和意識上都具有鮮明的民主傾向,他們不僅威脅著傳統藝術的權威,也對社會統治的權威形成了潛在的威脅。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印象派畫家的周圍,總是聚集著形形色色的反社會人格:從同情勞苦大眾、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左翼”作家左拉,到所謂“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波德萊爾,從反叛自身階層和家庭的紈绔子弟高更,到巴黎公社的熱情同情者和參與者湯基老爹等等。而這也就是為什么印象派第一次聯合畫展在法國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的根本原因。
色彩源于光
在繪畫中第一次將陽光作為那么重要的東西強調出來的是印象派畫家。所以印象派的名字是與光連在一起的。自然的光色閃爍在印象派的作品之中,而作品中那些強烈的光色又照亮了畫壇。
印象畫派跟隨巴比松畫派、海牙畫派和浪漫主義畫家等走向戶外,走進大自然、走向生活,用眼睛的觀察和直接感受作畫。產生印象派的時代,剛好是科學家對光和顏色的研究十分活躍的時代。科學家得出這樣的結論:肉眼之所以看到物體,是因為它反光。這給了印象派畫家一個啟示。他們將科學新發現作為為他們創作手法的根本,認為景物在不同的光照條件下有不同的顏色,所有的彩是由照射在他們之上的光線決定的,一切色彩都是光的表現形式。他們的使命便是忠實地刻畫在變動的光照條件下的景物的“真實”,這種瞬間的真實恰恰就是一種轉瞬即逝的“印象”。而印象派畫家把這種“瞬間”永恒地記錄在了畫布上。
印象主義尋求光線和色彩帶來的效果。他們發現戶外的陽光與以往的繪畫所表現出的光線完全不同。大自然中光線的神秘變化引起了他們的好奇,也增加了表現的苦惱。他們近乎狂熱地堅持,一幅畫作中所運用的所有色彩都應該處于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反應之中。印象派觀察事物,是感覺先于眼睛,不停留在它本身的形狀上,而以是感覺來表達光的現象。正因為如此,印象派成為學院派和當時主流藝術風格的對立面。對于后者而言,物體本來處于固定和孤立的狀態,而陰影只是物體表面凹凸的反映。印象派的藝術觀實際是在鼓勵創作過程中畫家身上各種主觀因素的參與和投射,而這正是以學院派為代表的藝術傳統所無法茍同的東西,他們所注重的只是對客觀物體維妙維肖的再現。
由于對光的執著追求,印象派畫家的一生都是在烈日炎炎和風雨交加中度過的。他們的足跡踏過了歐洲的山山水水。也是為了光,他們不得不早出晚歸,去戶外寫生,將太陽的痕跡在畫面上留住。
1867年,莫奈在戶外的陽光下寫生,為了在室外完成這幅巨作,他不得不在花園里挖一個與畫幅寬度一樣的條溝,以便畫上部的時候把畫降到溝里,他就可以從容地在畫面上縱橫揮灑。畫家庫爾貝來看他作畫時奇怪他為什么呆對著畫不動筆。莫奈說:“我在等太陽。”庫爾貝認為他可以先畫別的地方。他卻搖著頭說:“色彩關系不對。”
為了捕捉大自然的喜怒無常的各種表情,莫奈常常在最惡劣的天氣下寫生。為畫陽光下的水面,他模仿前輩畫家杜比尼也制造了一個“寫生船”,這樣,他就不必局限在岸邊或橋上畫水。而可以自由地深入到河水的腹地寫生畫畫,將陽光下的水光畫下來。
第一幅印象派繪畫的靈感便來源于莫奈從船上所獲得的對水的研究,他鼓勵雷諾阿在同樣的地點作畫,那里迷人的景色,就是陽光在水面上不停的移動,閃爍著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