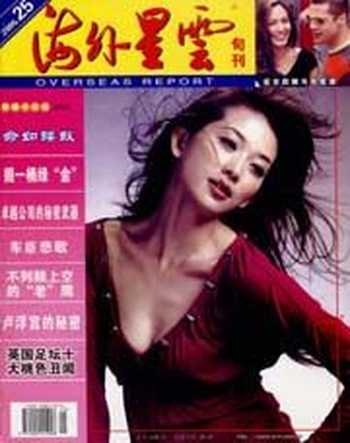車臣悲歌
10多年來,車臣戰事一直是場泛濫的大屠殺,在飽受戰火摧殘的這塊土地上,絕望籠罩著一切。好戰分子以車臣的名義而戰,但是真正的車臣人受夠了戰爭,渴望片刻的寧靜與和平。
這里被絕望籠罩
瑪莉卡是位育有兩個孩子的年輕車臣醫生,她在慘絕人寰的分裂戰爭中幾乎失去所有家人,家鄉也淪為但丁筆下的地獄。她母親在2001年被炸彈炸死,父親雖在爆炸中幸存,但因周遭恐怖慘狀對他的打擊太大了,很快就病倒。她的哥哥也被強行押走,在情況惡劣的臨時監獄中一關就是5個月,后來雖通過紅十字會救援脫困,不久卻因心臟病而過世。
最沉重的打擊發生在2002年的一個春天夜晚。凌晨1點鐘,幾個荷槍實彈、戴著面罩與頭盔的男子闖入瑪莉卡位于車臣首府格羅茲尼的公寓,擄走她的丈夫,至今生死不知。當地官員一點也幫不上忙。在格羅茲尼地檢署中有成千上萬份注明“失蹤”的檔案,瑪莉卡的丈夫只是其中之一。
瑪莉卡默默承受這份傷痛。10多年來,戰火一直在摧殘這塊孤獨領土,絕望有如一面棺罩般籠罩一切。2004年9月l日,以車臣人為首的32名恐怖分子攻占北奧塞梯共和國一所學校,劫持歷時52小時,寫下了恐怖新頁:約330人喪生,其中半數以上是兒童。當新聞主播困難地念著這個不熟悉的地名時,觀眾也抱著難以置信的心情觀看,無法理解人性怎么會沉淪至此。
渴望自由的車臣人
高加索山脈從黑海到里海綿延1200公里,車臣正是此區淌血的心臟。高加索從成吉思汗時代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戰士在深山尋求掩護、商人處心積慮利用這里的港口;到了最近,石油公司更紛紛涌向里海的油田。高加索的俄文名字“卡夫卡茲”就如同咒語般,召喚著法力高強的神靈。這里不只是動亂錯雜之地,也是充滿傳奇的國度:綁架新娘習俗與血腥家族世仇在這個危險地帶依然盛行,數世紀的主權之爭方興未艾。
前蘇聯解體后,山脈把俄羅斯與南邊的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等國隔開來。山地以北地區語言和種族龐雜,統稱北高加索。在眾多的古老民族當中,在錯綜復雜的種族與宗教傳統里,有一群人永遠顯得特立獨行,那就是車臣人。他們對于自由的渴望以及為自由而戰的斗性幾乎無人能及。從l722年首度與彼得大帝的騎兵正面交鋒時開始,車臣人就為了擺脫俄國統治而抗爭。
1858年,正當穆斯林山民對沙皇政權發動圣戰之時,旅經高加索山區的作家大仲馬就記載了車臣人的尚武精神:“所有的山中戰士都勇敢無比,他們所掙得的每一分錢都花在武器上面。一個車臣人就算衣衫襤褸,他的劍、匕首與槍也都是最精良的。”
戰爭摧毀了家園
前蘇聯末年,隨著獨立運動從波羅的海延燒到俄國遠東地區,車臣境內要求自由的呼聲點燃了叛變行動。就在1994年的最后一天,第一次車臣戰爭爆發。
整個車臣共和國的面積僅僅l.5萬平方公里,但是這場戰事在這么小的地區內,就已奪走10萬至30萬條人命,造成50萬以上的車臣人流離失所。格羅茲尼遭受的破壞,是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慘烈的。這次戰爭以沒有所謂勝負的方式結束。1996年8月,車臣叛軍大舉奪回格羅茲尼之后,雙方同意停火。
接下來的3年,這個共和國在缺乏有效法律與經濟基礎建設的情況下奄奄一息。伊斯蘭教律法興起,教法法庭與公開鞭刑充斥。而由于車臣與俄羅斯聯邦的其他成員斷絕了經濟往來,以至綁架與汽油走私等活動十分盛行。車臣人雖然贏得戰爭,但他們的家園卻淪為毫無法紀的孤島,吸引伊斯蘭教極端分子前來,成為北高加索中心的定時炸彈。
1999年夏天,戰火重燃,并持續悶燒至今。事件起于1200名車臣好戰分子帶著統一北高加索伊斯蘭教國家的荒誕意圖入侵鄰國達吉斯坦,此行動歷時甚短。接著莫斯科和另外兩座俄國城市,又發生一連串的公寓爆炸案。
俄羅斯的反應較第一次戰爭更為激烈。到1999年底時,格羅茲尼已是10年內第二度成為廢墟。數十萬車臣人民開始逃離家園,大部分人往西到達鄰國,也有許多人被迫向南走,穿越歐洲最高的山岳,在深雪中接連步行數日,不時面臨戰機的威脅。
在越過格魯吉亞邊界潘吉西峽谷入口的杜錫,我遇到一群車臣難民,他們擠在一間廢棄已久的醫院病房,光禿禿的水泥房間里沒有窗戶也沒有暖氣。“在第一次戰爭中,我們坐在地窖中數炸彈。但這一次的炸彈太多,我們根本來不及數。”一頭紅發的9歲小女孩蘿札說。
好戰分子不代表他們
當一切都消滅殆盡,強烈的報復心態取代了主權之夢,而其中最激烈的反抗標舉了新的名義——圣戰。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是教義最嚴格的伊斯蘭教教派,深深吸引了這一代的車臣青年,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除了戰爭與暴虐之外一無所有。
這里的叛亂長期吸引不少國外的伊斯蘭好戰分子前來,在他們眼里,獨立建國的車臣既是個值得支持的事業,也有望成為他們進行全球行動的中心。但許多車臣人民表示,不論瓦哈比教派還是其他外來的伊斯蘭教派,都與他們的傳統和真正認同背道而馳。
“我們正面臨年輕人被伊斯蘭好戰分子收編的危機。”車臣精神科醫生庫里·伊德里索夫說。5年來,他一直在為難民兒童服務,他也和大部分車臣人民一樣,絕望地看著一波波恐怖攻擊以他們的名義進行。
“這場戰爭已造成難以想象的傷亡。”利布科罕·巴札埃瓦說。他創立了一家服務中心,為車臣婦女提供法律與醫療協助。“極端的環境已令社會激進化,傾倒的不僅是我們的房子,連我們的民族精神也已成廢墟,我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加以重建。”
要的只是片刻的和平
今天的格羅茲尼,許多瓦礫已經清除,但整個城市己遠非戰前的模樣,那時全市有40萬居民,許多人在龐大的石化工廠里工作。即便如此,生活已略回復規律:燒烤小販又開始在路邊擺攤烤肉,果菜市場在市中心開張,如今僅剩的25萬市民偶爾還會遇到塞車;俄國軍隊仍駐扎在此,但許多檢查站已撤離,土兵也很少離開他們的要塞;在國立大學里,教師們也不必再在戶外爆發的槍炮聲中講課,但他們不抱幻想:“真正的重建工作少之又少,更別提恢復市民生活。”
車臣人不再提到他們在第一次戰爭中追求的主權。在格羅茲尼,人民的話題回歸到基本需求及個人與經濟安全。“他們受夠了俄國士兵劫掠他們的村莊。”來自圣彼得堡的俄裔教師卡佳·索金里安斯卡伊亞在談到她的學生時這么說,“他們也受夠了車臣戰士攻下同樣的村落。他們受夠了不法的官僚、貪污與混亂。他們也受夠了失蹤、暗夜槍戰跟不確定的未來。他們要的只是片刻的和平。”
(摘自《國家地理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