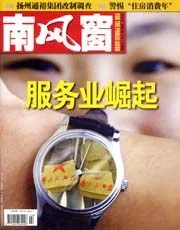亞洲四小龍的啟示
劉社建
近期有雜志撰文對亞洲四小龍自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的復蘇進行了研究。文中稱香港與新加坡的服務業所占比例較高,是它們成功地擺脫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2004年的情況來看,臺灣的經濟增長遜于香港與新加坡。2004年臺灣經濟增長5.7%,較韓國的4.6%為高,但卻低于香港的7.7%與新加坡的8.4%。臺灣工業生產增長雖達9.8%,但卻低于新加坡的13.6%;出口增長高達20.7%,但仍低于新加坡的24.6%。
而在2004年的人均GDP指標上,在四小龍中,臺灣退居龍尾。文章引用臺灣中央大學臺灣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朱云鵬的話說:“香港、新加坡已經以服務業沖高(帶動)國民所得(GDP),領先臺、韓,早已跟我們不在同一條跑道上。”
“龍尾”的答案未必是服務業
對于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大作用,當然必須予以足夠的重視。以服務業的發展狀況來解釋四小龍的復蘇,亦是一種有理的解釋。但是不宜對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予以過高估計,不能過分抬高服務業的作用,尤其是把服務業比重的高低作為解釋四小龍復蘇的原因更需謹慎。雖然可以肯定的是服務業在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復蘇中肯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未必是決定性的作用。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四小龍的服務業均已有了相當的比重。以近年來四小龍服務業的比重來看,臺灣、香港、新加坡服務業的比重并沒有質的區別。1998年時臺灣的服務業比重達63.1%,這個比重也比較高了,但是這樣的服務業比重包括香港更高的服務業比重均難抵擋東南亞金融危機。1995年時,臺灣的服務業產值比重就一度超過60%,這也是臺灣進入發達社會的標志之一。近年來臺灣的服務業持續上升,2004年臺灣服務業比重達到68.7,2005年上半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超過70%。雖然臺灣服務業比重不及香港2005年服務業87%的比重,但是超過新加坡2003年服務業占65%的比重。
臺灣、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服務業比重并不存在太大的差距,服務業的比重不足以成為是否促使其恢復的關鍵。
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發生的變化
此前不久的中國首次經濟普查,與隨之而來的GDP修正,進一步吸引了公眾對于產業結構變動尤其是服務業比重變動的關注。
以上海為例。最為突出的是上海第三產業比重的上升,按照普查以前的統計數據,上海近年來第三產業的比重有所下滑而且小于第二產業的比重,但是根據修正后的數據,2004年上海第三產業的比重為50.8%。
對于上海這樣的直轄市而言,服務業的比重自是衡量經濟發展階段與狀況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伴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產業結構的比重也遵循著國際產業結構一般趨勢的變化規律而不斷變動。目前中國整個經濟發展階段與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考察產業結構變動時,這種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必須引起足夠的關注。
這種變化的第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進入了重工業化與城市化加速階段,這種重工業化與城市化階段的疊加,使得高成本、高投入資源要素的約束性加大。這是由于重工業需要較多的資源要素,而城市化初期同樣也需要較多的資源要素。這樣重工業化與城市化加速并行的階段,就對資源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個突出的特點是體制改革深化,這種體制改革深化已由原來的經濟改革為主逐步走向社會改革與政府改革并重。而在此過程中,社會改革與政府改革對經濟改革的影響并非加速推進,而是如何使結構調整趨于平穩,并解決一些經濟社會領域的突出性的矛盾與問題。
第三個突出的特點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以及實踐科學發展觀將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已經和將要發生重大影響,目前業已顯現出來的是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動。
在上述三個突出特點構成的中國現實基礎之上,對于產業結構的變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是重點之一。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逐步上升是國際趨勢。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促進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這也是服務業比重的變動引起公眾關注的關鍵原因。
中國服務業發展可以大干快上嗎?
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服務業的比重持續上升,但是無論是制造業還是服務業仍存在著較多的問題。突出問題之一是產業結構仍是表層高度化,其內部結構表現出傳統產業競爭為主、以低附加值產業部門為主,其內含的技術程度與智力程度并不很高。
與此相應,產業組織基本上仍保持著傳統等級制的組織機構,以及傳統的以產業分立為基礎的市場結構。這種產業結構表層高度化容易出現比重關系的不穩定性,很可能導致經濟發展表現出后繼乏力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產業結構與組織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產業結構與組織的重點要轉向內含高度化。隨著一些地方土地成本、商務成本等的上升也促使產業部門更新換代,產業結構的發展將由合理化導向到高度化導向轉變。
同時,在此產業結構能級提升的過程中,大量新興產業部門將替代傳統產業部門,高端或高附加值產業部門替代低端或低附加值產業部門,高技術、高智力含量的產業部門替代低技術、低智力含量的產業部門。在此過程中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將加速發展,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經濟增長的未來狀況。
與傳統的產業各自發展模式不同,在產業結構內含高度化的過程中,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將呈現融合發展的趨勢。這是以知識經濟為基礎,借助于信息化手段,利用生產價值鏈進行合作,打破傳統產業邊界實現一體化發展的新型方式。
與這種產業結構內含高度化相適應,產業組織結構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動,要在產業自動化、智能化的基礎上實現組織結構柔性化,而且要求逐漸演變為原子式的組織結構,以適應靈活多變的市場組織形式。
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全局來說,要求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的融合發展,對于區域性地方而言也要求在促進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快速的發展過程中實現融合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先進制造業的強力支撐,尤其是對于一些省而言。省與直轄市不同,直轄市可以通過與周邊地區的緊密分工與合作,來獲取先進制造業的支撐與實現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而對于一般的省來說,由于省的區域范圍過大且受經濟發展階段所限,如果過分追求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而忽視了先進制造業的相應發展,將可能為經濟帶來不利的影響。
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平衡之道
對于中國未來的產業結構發展來說,無疑要充分發揮服務業的重要作用并促進服務業的持續發展,但是也不能忽視制造業的發展而導致產業空心化等不利傾向。
產業結構空心化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已有先例。對于作為一個國家中的若干地區,通過不同地區間的協作與合理分工,產業空洞化自可有效避免,但是作為決策者不可忽視產業空洞化的問題,尤其是對于省而言,四小龍中的臺灣即是前車之鑒。
由于臺灣近期制造業的衰退,服務業發展也相對滯后,雖然其服務業比重上升,但這更多的是制造業衰退而非服務業本身發展的結果。2005年臺灣經濟增長遠不如預期,各項指標均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況。
尤其是臺灣經濟的核心——制造業出現負增長,前四個月衰退0.77%。制造業占GDP的比例持續下降,2004年已降至29.5%,2005年一度曾降至25%以下,這是臺灣產業空心化的表現。正是由于制造業的相對衰退,使得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缺少了賴以發展的基礎。
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協同發展并非易事,而且這對不同的省與直轄市來說要求也不相同。對于上海這樣的直轄市而言,其發展制造業的方向是要努力發揮制造業管理中心的作用,而不是繼續保持生產中心的作用。上海制造業發展的關鍵是,能否把企業中的生產部門轉移出去,而把管理中心留下,要充分發揮制造業中管理部門的重大作用。生產部門向外的轉移并非產業的分工而是企業內部的分工,上海要通過制造業更高層次的發展,而為經濟發展與服務業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中國各省市處在全國統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在通過全國產業間的相互補充與合作,取得全國經濟一盤棋的統一發展。對于上海這樣的直轄市不但不需要顧慮制造業的比重有所下降,更關鍵的是與長三角等周邊地區合理分工,同時更加充分地發揮上海服務全國的重大作用,以使全國經濟發展獲得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些省也不必為服務業的比重高低而耿耿于懷,而必須在充分考量本地經濟發展階段的基礎上,在充分發揮農業的基礎性作用上,使得制造業與服務業協調發展,充分發揮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