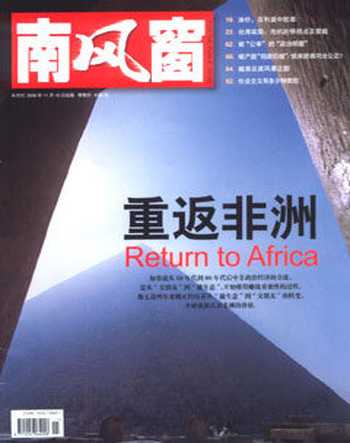勞力者與勞心者
高超群
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夫子也曾經斥思想學家、圃的樊遲,日:“小人哉,樊須也!”。在傳統中國,“勞心”的“君子”與“勞力”的“小人”是判然不同的兩個階級。不過,這兩個階級之間并非總是高度對立。因為在常態下,他們秉持著近乎雷同的榮辱觀念,“勞力者”也認可自己的卑下的地位。套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說:他們有一種“勞力者”的名譽觀、美德觀和正直觀,或者可以說,他們有一種身為“勞力者”而自覺光榮的心理。不用說,這是“勞力者”模仿“勞心者”的結果。在我們的史書和戲劇中,經常出現的“忠仆義主”的感人事跡就是一種證明。“勞力者”當中的有志之士也有希望通過狹窄的科舉通道來改變自己的身份地位,“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這種綱常倫理隨著現代社會的到來而土崩瓦解。從近代以來,“勞工神圣”便逐漸成為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準則,魯迅就曾經被人力車夫壓榨出“皮袍下的‘小”來。不過在民國年間對“勞力者”的重視還僅僅是“勞心者”自我反思的結果。直到共和國的建立,工農聯盟成為統治階級,“勞力者”的社會政治地位才真正有所改觀。但這種改變并不想人們想象的那么徹底。比如說,直到1985年,干部的最低級別,科級的工資是122元,技術工人的最高級別工資是113元,這當然不是偶然巧合。在其他待遇上,干部和工人之間的差別就更大了。更不用說沒有任何保障的農民了。在“文革”時期,在政治上遭到打擊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在下放農村的時候,和他們一起勞動的農民在內心里還非常羨慕這些吃皇糧的“公家人”。但終究“勞動光榮”的觀念還是確立了。“勞力者”不再愿意自認卑下,也不再以“仆人”的道德來要求自己,他們模模糊糊覺得自己應該是主人,但并不知道怎樣成為主人。
80年代開始的工資改革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最鮮明的是工資級別之間的差距開始拉大。這其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無論就結果還是原因來看,都不僅僅是刺激積極性、提高效率那么簡單。比如,改革前,同級的技術人員的工資,一般比行政人員要高。在“工資改革”后,同級的技術人員工資,比官員的工資低了。顯然這意味著對管理者偏重。
從宏觀的意義上來看,整個社會風氣的變化更為復雜,其意義也更為深遠。
在改革初期一段很短的時間里,勤勞是普通人獲得財富和地位的主要手段,因而在那個充滿朝氣的年代里,勤于勞動和善于勞動者受到人們的普遍贊揚。那時,工廠里的技術人員和掌握熟練技術的老工人,成為人們羨慕和學習的榜樣,年輕的技術員更是姑娘們愛慕的對象。在農村里,大量涌現的“萬元戶”也大都是節儉、勤勞得近乎自虐的人。“文革”中那些口中高唱平等、贊揚勞動,而實際上對工作和技術一竅不通、只善于投上級所好和利用政治運動整人的人一下子從“勞心者”的地位跌落。“勞力者”似乎看到了通過自己的勞動上升成為“勞心者”可能。在他們的心目中,改革就意味著順應這種變革的方向。
可惜好景不長。有人把國企工廠里的職工分成四類:“第一種是干工作好,關系也好。第二種是干活兒好,但不善于搞關系。第三種是干工作差,關系搞得好。第四種則是兩樣都搞不好。干工作大致分兩種,生產技術和生產管理。搞關系也分兩種,一是與領導的關系,一是與工友的關系,這里主要講的是與領導的關系。”隨著改革的發展變化,“早期第一種人走上領導崗位的多,后來不正之風越刮越猛,第三種人當官的數量增加得越來越快。其他人本來對第三種人反感,當第三種人當上官并漸漸成了主流后,倒行逆施,無疑會大大傷害生產積極性,企業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企業里的這種情形只不過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時至今日,勤勞致富似乎已經成為遙遠的童話,而“搞關系”卻成了“成功人士”的必備才能,越是接近生產的第一線,這種情形就愈加嚴重。由于缺乏生產積極性,“勞力者”們就再也不會任勞任怨,勤奮上進了。于是,在“勞心者”眼中,“勞力者”就變得越來越沒有敬業精神、不安本分;還時而貪婪奸狡,時而桀驁不馴。改革或許順遂了“勞心者”的利益,但并沒有造就他們所希望的新社會。
改革似乎在某些方面偏離了“勞力者”與“勞心者”對他們自身和他們之間關系的期望。那么這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或許下面這一段話可以讓我們有所啟發和警醒,這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表述由貴族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變革階段,主人和仆人之間的關系的,他說:“做主人的心懷敵意,但表面上和藹可親,做仆人的也持有敵意,但不隱瞞自己的反抗;一方企圖通過種種不公正的限制來推托其供養和付酬的義務,另一方則設法推托其服從的義務。管理家務的權柄在兩者之間漂浮,誰都想把它搶在自己手里。他們分不清權威和專橫、自由和任性、權利和本分的界線,誰都沒有正確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自己能夠做些什么,自己應當做些什么。這樣的狀態絕不是民主的狀態,而是革命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