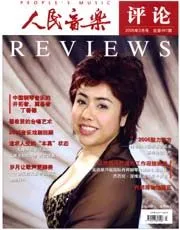開拓新領域 創作新音樂
從19世紀晚期吹響序曲、在20世紀初期拉開序幕的世界“新音樂”(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現代音樂”),是一種嶄新而帶有革命性質的“文化·社會”現象,也是世界專業音樂創作中一種新穎而帶有異軍突起性質的“語言風格”類型。這種新音樂從它出現的那天起,始終都以探索和創新的姿態頑強開拓,銳意進取,不斷壯大,勝利前進,迄今為止,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多元格局中一支風格獨具的勁旅。簡單地回顧一下世界新音樂的發展歷史就可以看到: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打破了傳統的時間律動體系;1923年,勛伯格的《鋼琴組曲》Op.25第一次摧毀了統治音樂千百年的調性體系并相應建立起無調性條件下的“音樂新律法”和“結構新秩序”;捷克的哈巴和意大利的“未來主義”者在與他們差不多的時間里,分別把微分音和噪音引入專業音樂領域,宣告十二平均律和樂音體系一統天下時代的結束;30年代,巴托克的創作使原本高度民族化的音樂語言獲得了能夠在世界范圍里傳播的國際化風格;40年代,約翰·凱奇的預配實驗第一次改變了鋼琴的音響本質;1946年在德國達姆施塔特開始的“現代音樂暑期訓練班”,則使這種新音樂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國際性培訓或教育機制;1948年,巴比特和梅西安等歐美作曲家創作的第一批整體序列音樂作品問世,中國的第一部無調性音樂作品、作曲家桑桐為小提琴和鋼琴而作的《夜景》也在同年問世;隨著“威伯恩十年”的開始,回避線條而強調發散的“點描音樂”、通過科技手段而人工合成的“電子音樂”、反對理性而強調偶然的“機遇音樂”或“不確定音樂”等先后出現;60年代,又出現了以新波蘭樂派為代表的弦樂新音響和樂隊新音響、以美國作曲家喬治·克拉姆為代表的室內樂新音響以及以意大利作曲家貝里奧為代表的“新人聲主義”和對常規樂器音響的新探索;70年代,一方面出現了以混成手法為特征的“新浪漫主義”和“復風格”音樂,同時又出現了以英國作曲家芬尼豪為代表的“新復雜主義”……,上述等等,不一而足。在20世紀出現的一次次事件、一次次創造和一次次突破,不僅形成了20世紀西方新音樂發生發展在作曲技術方面表現出來的主要脈絡和基本軌跡,也直接形成了70年代末期、在中國共產黨召開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大陸作曲家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迅速切入世界新音樂潮流的基本背景。
粗略算來,中國音樂家的新音樂創作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是同步的,迄今為止,也已走過了連續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不平凡歷程。總的來講,這種新音樂在面向世界的開放中國里發生和發展,既可謂事出必然,也可謂道路曲折。但從總的趨勢上看,二十多年來的中國新音樂創作不但以不屈不撓的姿態頑強生長而終于自成一支,而且以不可忽視的風格特性成為新時期中國音樂生活中一個有影響的部分,同時還以不可小看的實力成為能在國際新音樂舞臺上實現勝利競爭的有生力量。也就是說,通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實踐,中國新音樂創作不僅迅速跟進了國際新音樂發展的主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領著中國專業音樂創作的潮流。時至今日,中國新音樂有著一支老中青相結合的壯大的作曲家隊伍,他們創作出了既能與國際同行創作相對應、又具有獨特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大批量新音樂作品,這些音樂作品的創作不僅廣泛涉及國際新音樂同行創造發明的主要技術手法類型和品種樣式,又在中華民族和作曲家本人個性的基礎上實現了成功的移植和再造,產生了可識別的中國式創新。中國作曲家和他們的新音樂創作不僅豐富和提升了新時期的中國音樂生活水準,為國家和民族爭得了榮譽,為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還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出了大量有待解決的新課題。應當肯定地說:由于中國作曲家及時抓住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他們以敏感而勇敢的態度積極接受新事物、開拓新領域、使用新手法、創作新音樂,使中國音樂創作的專業化和國際化程度以空前快速的方式向前發展,以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寬廣得多的視野來觀察、思考和處理自己的專業音樂創作,這不僅是一種事實,更是一種變化、一種進步和一種價值之所在!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為此,我們應該向所有為中國新音樂發展做出貢獻的中國作曲家和中國音樂家們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面對這樣的事實,作為與音樂創作相應的音樂理論研究,究竟應當怎樣才能客觀、科學、全面、深入地看待新時期中國新音樂和它們的價值?在對新時期中國新音樂進行價值評判和理論研究時應該持有何種態度、使用什么方法、解決哪些問題?我們在繼續學習、借鑒、比較、研究西方新音樂同行創作成果的同時,又將如何及時實現在新音樂研究過程中的“自我關照”或有效實現在新音樂理論研究中的“本土化”轉移?對這些問題如何回答,將不僅影響著中國新音樂創作的現實存在和繼續發展,影響著中國新音樂在世界音樂舞臺上的應有地位和文化尊嚴,也將影響包括新音樂在內的中國音樂理論研究發展和后續人才培養。令人欣慰的是,那種在一度曾經把新時期中國新音樂探索及其階段性成果當作“新潮”、看作“怪胎”、稱作“沖擊波”、并且覺得它有“一石激起千層浪”之能效的那種“特殊反應期”已經基本過去;轉而覺得需要以平靜的心態、平等的眼光、寬容的姿態和寬廣的胸懷來對待中國新音樂的呼吁、認識或氛圍也正在逐步形成;圍繞著新時期中國新音樂而開展的歷史回顧、編年梳理、材料匯集、專題研究、比較對照、問題探討、個案分析、經驗總結、得失思考等工作,都能在比較正常而學術的情況下自然開展并不斷推出積極的成果;高等音樂院校的專業教學內容和重大專業賽事的曲目范圍,也較之過去而更多一些地涉及到了新音樂和中國新音樂。種種現象都能表明:人們的藝術評價習慣正在改變,人們的藝術審美角度正在調整,人們藝術需求的方面正在拓展,人們對新音樂了解的內在要求正在提高,人們對包括中國新音樂在內的藝術接受心理和能力也正在逐步成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如果能夠對新時期中國新音樂及其價值評判和理論研究采取更加平靜、更加平等和更加寬容的態度,這對新時期中國新音樂的創作、研究、傳播和推廣來說,才會形成更好一些的外在條件和客觀基礎,才會促成更加積極的各種成果,進而也才會獲得更加準確的價值評判。當然,我們并不要求也不可能無區別地盲目肯定新時期中國新音樂創作中出現的一切,就像我們既不主張也不可能全盤接受西方20世紀新音樂的一切一樣。至于那些在中國新音樂創作中難免存在的所謂“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或“良莠并存”等情況,則既不是今天才有的情況,也并不是惟獨中國新音樂才有的事情,相反卻是發展中、前進中和不斷完善中的事物大都可能碰到的一種現象。對此,人們應該允許并且充分相信:中國新音樂創作一定會通過自身的努力(包括必要的涅槃),按照事物發展的自身規律,勇敢地接受時間的考驗,接受實踐的考驗,接受批判的考驗;中國新音樂理論研究也一定會通過自身的努力(也包括必要的涅槃),按照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律,尊重音樂事實,面對音樂文本,客觀冷靜解析,在其過程中不斷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力求能夠從局部到整體、從現象到本質、從個性到共性,逐步實現中國現代音樂研究從必然到自由的全過程。
(本文為作者在2005年12月第一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開幕式上的致辭,本刊有所刪節。)
彭志敏武漢音樂學院副院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