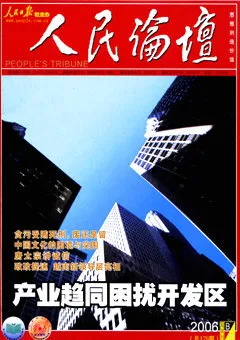貪污受賄死刑,廢還是留
據有關資料報道,近年來,攜巨款潛逃國外的在國內原身居要職的職務經濟犯罪分子已逾數千人,而緝捕回來接受國家法律制裁者卻寥寥無幾;追回的外逃資本更是不及數千億元之零頭。這樣一來,此類攜巨款外逃的貪官不但沒有回國受審,反在國外過上了安逸而舒適的“自由生活”,由此引發的負面效應,不僅僅是國家遭受巨額經濟損失,還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的良性運行與發展。
國內刑法學界不少學者因而提出我國宜盡快廢止經濟犯罪包括貪污罪、受賄罪的死刑設置,以方便引渡外逃貪官并減緩外逃之風。然而,此一死刑觀,卻不為國內多數(非刑事法)學者乃至整個社會公眾所普遍看好。
廢止論者的五大理由
實際上,對是否盡快廢止貪污、受賄等經濟犯罪死刑設置,國內存在廢止論與保留論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其中廢止論者的主要理由是:
死刑并非報應的必要手段。在現代社會,早期人類的同態復仇式的刑罰,已為實質意義的罪刑等價暨人道主義的刑罰所取代。而在現代人的理念之中,自由乃是人生最為寶貴的權利,故而,以終身監禁的辦法已足以達到相對報應的刑罰目的。
此外,無論從罪刑等價還是就單純的功利角度看,經濟犯罪分子既然造成了對國家經濟法律秩序乃至國家經濟建設的危害,就應較多地或者主要地以“經濟懲罰”的手段來“等價”懲罰之。事實上,刑罰只是“事后罰”,死刑更未必“萬能”。要大幅度地遏制貪官攜財外逃,應更多地依靠事前預防、事中堵塞、事后懲治的全方位的“廉政機制及其法律措施”的健全與暢行。
死刑具有不可分性。要做到刑罰的公正,必須令其刑罰具有可分性的特征。而生命權利卻不像財產權利、自由權利那樣具有可分性。從而,死刑就可能不同罪而等罰。例如,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在我國,從法律規定上講,貪污受賄10萬元人民幣、情節特別嚴重者就可判處死刑。在此制度設計下,貪污數千萬、數億萬元人民幣者,與貪污10萬、數十萬元人民幣者的社會危害性及其罪刑輕重顯然大不相同,而他們所面臨的刑罰卻可能都是死刑,這樣的刑罰顯然有失公允。
“死刑犯不引渡”帶來執法難題。目前,貪官們千方百計地攜贓款潛逃國外,我國卻難以引渡。因為世界通行“死刑犯不引渡”的政策。這樣,針對此類外逃貪官的我國國家刑罰權難以實現不說,貪官們“卷財而逃”的后果還會致使國家很難追回其犯罪贓款。此外,諸如此類的攜巨款外逃的貪官不能回國受審,也會給國內不少尚未發案的貪官提供十分惡劣的示范效應。
死刑不經濟。美國有人統計,迄今為止,死刑犯的最高平均花費已達500萬美元以上。在中國,執行一名死刑犯的花費雖然不可能如此之高,但是,隨著死刑二審必須庭審和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所有死刑案件復核程序工作的正式實施,要判決和執行一名死刑犯的花費必然會愈來愈高,因而動輒判處并執行死刑未必經濟。
死刑誤判難糾。任何時候、任何階段的定罪量刑工作,都難免存在錯誤,而死刑的不可糾正性,決定了此種“處罰”不宜于用作人類刑罰。
此外,從刑罰的正義性來看,國家也宜于逐步廢止貪污、受賄等經濟犯罪的死刑設置。人之生命價值永遠高于財產價值。無論貪官們給國家、社會、他人帶來多么巨大的經濟危害,由此危害所致的經濟損失之總和仍然不敵于“人的生命”之價值,因而經濟犯罪之害與死刑之害是“不等價”的。
保留論者的主要觀點
保留論者的主要理由是:
基于懲治和預防犯罪、維護國家政權的需要。認為廢止了經濟犯罪的死刑設置,會人為提高犯罪率,降低刑罰有關懲治與預防犯罪的功能;特別是會降低刑罰的震懾作用,從而既不利于國家政權的穩定,也不利于有效遏制貪污腐敗行為。
是全力發展生產力的需要。認為發展生產力需要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因而需要通過死刑來規則秩序、清理社會環境,從而推促經濟的穩步發展。
是確保國家、社會、民眾的財產權益不受犯罪侵害的需要。認為惟其死刑設置,才能以生命刑罰的威懾力來確保上述法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有利于刑罰報應功能的實現。認為經濟犯罪雖然不能直接導致他人死亡的法律后果,卻可間接地導致成千上萬戶貧困家庭成員失學、失業甚而饑寒交迫、病餓而亡。因而,從中國民眾目前普遍持有的刑罰報應觀而言,多數人仍主張惟有對這些事實上正在“謀財害命”的經濟犯罪分子判處死刑,才能滿足一般民眾的報應心理,從而穩定社會政治經濟秩序。
保留死刑更加經濟。因為關押犯罪分子需要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特別是如果沒有足夠的財力對各類犯罪分子實行分管分押,可能導致不同性質的罪犯相互濡染惡習或相互教習其犯罪技能,從而不利于預防犯罪。
廢止死刑未必會減少貪官外逃。即便廢止了經濟犯罪的死刑設置,貪官們在貪得大量錢財后也不會因為留戀故土而不逃往國外。因而廢止經濟犯罪的死刑設置,并不必然地會減少職務經濟犯罪分子外逃人數的總量。
廢止經濟犯罪死刑利大于弊
針對關于死刑或存或廢的爭論,筆者較為贊同廢止論。對此,除上述基本理由外,還存在關于廢止貪污、受賄等經濟犯罪死刑設置的國際法和國家憲法等“立法根據”。
首先,我國已經簽署《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既已簽署,按照國際慣例,我們起碼應當“自律”。按照《公約》的規定,“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何謂“最嚴重的罪行”。對此,《公約》的當然解釋機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基本立場為:最嚴重的罪行應當排除所有的非暴力犯罪。由此可見,經濟犯罪不屬于國家可予保留死刑的“最嚴重的罪行”。
其次,從學理角度看,國家設定經濟刑罰的前提性基準應是:以國內憲法所蘊涵的憲律、憲德、憲政為該原則取舍的法律準據、價值根基和政治法則。在此基礎上,惟有體現人本與自由,才是憲法的根本與核心。
上述憲法理念,目前看來固然有較多的應然成分,因為迄今為止,它尚未被明確規制于憲法某一具體法條之中,但筆者仍認為它應為貫穿于整個中國憲法思想精髓的憲法精義,作為憲法之“子法”的刑法——經濟刑罰,應當以其基本價值準則去設定各項法律及其法律活動。惟有將上述憲法價值法則推廣到經濟刑罰領域,人們考量問題的視點才是雙向的:既要保護被害人、社會和國家的經濟法律秩序;同時要關注到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特別是生命權利。
由此可見,無論從刑法的正義性、效益性、效能性還是其人權保障機能看,廢止經濟犯罪分子的死刑設置,都合乎法理、事理、情理且利大于弊,宜于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