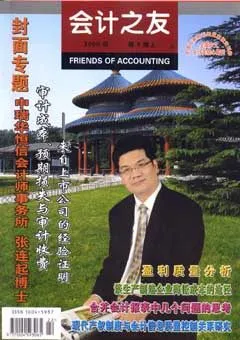對于2006年會計準則變化的思考
【摘要】2006年2月,財政部頒布了新會計準則,對于1992年及以后頒布的基本會計準則和具體會計準則作了較大的變化,這一變化有著重要意義,一方面我國會計準則正逐步與國際接軌,我國的會計準則制定體系也逐漸完善;另一方面可以預見到對上市公司的業績會產生重要影響。本文著重就新準則的主要變化談幾點思考。
一、基本會計準則中的主要變化
會計目標的變化。新準則第四條明確說明“財務會計報告的目標是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而1992年企業會計準則的目標主要是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新準則考慮到了所有相關者的利益,而不僅僅是國家的利益。
會計計量屬性中增加了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公允價值等計量屬性。由原來單一的計量屬性——歷史成本轉為多種計量屬性并存。
配比原則的變化。 在《1992會計準則——基本會計準則》第17條規定,體現了配比原則,即指營業收入和與其相對應的成本、費用應相互配合。“配比”原則經常成為上市公司推遲確認費用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雖然有謹慎性原則作補充,但這兩條原則在實際操作中以誰為優先并沒有相關指導說明。本次修訂的基本會計準則中,將這一條原則調整到“費用”要素下第35條“企業為生產產品、提供勞務等發生的可歸屬于產品成本、勞務成本等的費用,應當在確認產品銷售收入、勞務收入等時,將已銷售產品、已提供勞務的成本等計入當期損益。企業發生的支出不產生經濟利益的,或者即使能夠產生經濟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資產確認條件的,應當在發生時確認為費用,計入當期損益。”新準則中不再強調收入和費用在邏輯上的配比,更注重該項費用的支出是否能帶來經濟利益。
二、具體會計準則的變化
(一)形式的變化
具體會計準則的變化較大。首先是形式上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的慣例進行編號,新會計準則共38號。與原來的16項具體會計準則相比,增加了22項具體會計準則,如《具體會計準則第5號——生物資產》,《具體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和確認》。原來的《關聯方關系及交易的披露》變更為《關聯方披露》。
(二)內容的變化
內容上的主要變化在于非貨幣性交易與債務重組交易中恢復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債務重組中債權人豁免的債務可計入當期損益(原計入資本公積);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將不允許恢復;自行研制開發無形資產的支出不再全部計入當期損益,可以有條件地資本化;無形資產的攤銷不再僅僅局限于直線法,并且攤銷年限也不再固定;存貨的計價核算取消了“后進先出法”等重要變化。
三、對新會計準則變化的幾點思考
(一)新會計準則中對于“實質重于形式”原則體現得不足。比如《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不再把研發費用一刀切地計入管理費用,而是劃分為“研究階段”和“開發階段”,但這兩個階段區分得并不明顯,所以依然容易操縱。可以看出我國會計準則傾向于制定規則,這區別于其他一些證券發達國家或地區(如中國香港地區),與我國證券市場監管力度差及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相關。這樣以后會計準則還要不斷地修補漏洞。
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博弈總是處于不斷的運動當中,由此想到美國的安然事件對于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的影響。
安然事件之前美國的會計準則制定基礎是規則導向,美國的準則制定也以詳盡著稱,但是安然公司依然利用會計準則中對于特殊目的實體(SPE)的規定形式大于實質,進行表外融資以及關聯方交易。
美國FASB規定滿足以下條件的SPE可以不納入合并報表:
1.獨立于發起人或受益人的第三方業主對SPE擁有充足的權益性投資;
2.該獨立的第三方業主的投資是重大的(至少等于SPE資產總額的3%);
3.該獨立的第三方業主在SPE擁有控制性的財務利益(一般指持有SPE超過50%的表決權);
4.該獨立的第三方業主在SPE的投資具有重大風險和報酬(即該業主的投資及其潛在回報處于風險之中且不得由其他方作出任何形式的擔保)。
安然事件之后,美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備受指責,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決心修改相關準則,并改變規則導向的準則制定模式,現在自稱是以目標為導向。
可見,好的準則不在于其規定條款是否詳盡,而在于是否能有效地防止那些走灰色地帶和打擦邊球的行為。
(二)新準則中對于“重要性”原則規定得非常簡單,“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反映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項。”“重要性”原則是非常容易被濫用的原則,經常成為上市公司造假后而又以重要性為借口拒絕調整的幌子。美國前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阿瑟·利維特(Arthur Levitt)在他的一篇演講“數字游戲”(The Number Game)(黃世忠譯)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一些公司濫用了重大性概念。他們蓄意在規定界限內記錄一些錯誤,然后試圖通過辯解說這些錯誤對底行數字的影響微不足道來為其謊言尋找借口。如果確實如此,那么他們為何如此辛苦地創造這些錯誤?或許是因為這種影響事關重大,特別是如果他們彌補了共識性盈利預測所差的最后一分錢時,更顯得重要。當管理當局或外部審計師對這些明顯違反會計準則的做法提出質問時,他們總是羞澀地答到‘沒有關系,這是不重大的’。”從美國的一些經典的審計訴訟案例可以看出(如巴克雷斯建筑公司審計案例),法官在判斷“重大性”時是站在報表使用者的角度,“會誤導一般謹慎的投資者作出相關決策的”為依據。我們的準則中沒有對于相關方面的體現。
(三)資產減值損失雖不能恢復,但無法堵住上市公司調節利潤的缺口。以固定資產為例,某一年計提了巨額的減值準備后,固定資產的賬面價值減少,在攤銷年限不變的情況下,公司每年計提的折舊將減少很多,而且一次計提巨額減值只影響1年的凈利潤,而之后的折舊額卻可以影響若干個會計期間。比如,某公司有一固定資產計提減值準備之前的賬面價值為1000萬元,不考慮殘值,預計還可使用十年,則每年的折舊額為100萬元,假設該公司為此項固定資產計提減值準備300萬元,賬面價值還有700萬元,攤銷期限仍為10年,每年折舊額為70萬元,只此一項每年可增加利潤30萬元。
(四)易誤導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業績的判斷。這幾年,會計準則的某些變化較頻繁,如公允價值從沒有相關具體規定到禁止使用,現在又恢復使用。再如,新準則下資產減值將不允許恢復,因此可以預見2005年某些上市公司將轉回以前年度計提的巨額減值準備,某些公司無形資產的金額可能會增長較快等。廣大投資者并不明白會計核算的復雜性,不知道這其中充滿了對不確定性的估計與判斷,甚至不知道收入與費用的確認遵循的是權責發生制。大多數投資者看到的只是報表中列出的盈利數字,卻并不知道這些數字中蘊含的奧秘。新準則擴大了利潤的確認空間,近期內會給投資者以上市公司業績提升的假相。